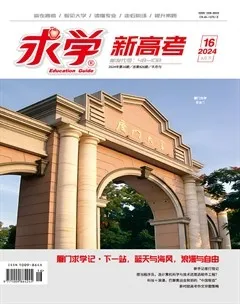一封郵件打開文學新天地
終于如愿以償考上了中文系,可我卻并沒有想象中那么快樂。
走進階梯教室,里面烏壓壓坐著彼此還不太熟悉的新生們。老師站在講臺上口若懸河地講授著專業知識,眼神時不時掃向講臺下的學生們,間或停頓片刻,示意學生們可以自由發言和討論。而我坐在教室的角落里一言不發,心里全是抵觸情緒。
我喜歡讀那些充滿詩意的句子,也喜歡動筆寫下心中的小情緒。我抱著“想成為一名作家”的心愿選擇了中文系,可等待我的卻是枯燥的文學史,那些鮮活的作品、有趣的靈魂,在這里都被壓縮成一個個書名號以及三五行概括性的話語。現當代文學課已經讓我大失所望,更何況還有文藝理論、訓詁學、音韻學等一堆如古董般生僻且過時的課程。
那段日子,被動接受知識的我就像射擊場上的靶子,全然沒有了快樂。直到一封郵件的到來,才打破了僵局。
那天,我像往常一樣登錄郵箱,意外看到教授現當代文學課的邱老師發來的一封課堂問卷調查。我知道這只是群發問卷而已,可以不用理會的。但那天我不知怎的,突然有了興致,不僅完成了問卷,而且還在問卷里噼里啪啦地表達了一通我對課程的不滿。
沒想到,下次再上邱老師的課時,他專門感謝了為數不多完成問卷的同學,然后鄭重地點出了我的名字,夸贊我的真性情,并希望我能和他當面交流。就這樣,課間時,我主動走到了他面前。邱老師并沒有批評我的想法,而是親切地問我最近在讀什么書。當我說到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紅》后,老師贊許地點了點頭。隨后,他向我推薦了當代歐洲最核心的文學家之一的安貝托·艾柯以及他的著作《悠游小說林》。
其實,聽到這個作者和書名的時候,我感到有些羞愧,因為這些對我來說很是陌生。我突然意識到,原來我是一個假的文藝青年,只是閱讀了幾本“流行讀物”就妄自尊大。后來,邱老師又根據我的喜好給我列了一份書單,上面的內容都讓我大開眼界。“這就是文學史的意義,像一個地圖,方便你按圖索驥。”沒想到,邱老師不動聲色地回答了我在問卷中提出的問題。
就這樣,我對文學史的抵觸情緒一掃而空。隨著閱讀的深入,我發現文學史的作用并不止于“按圖索驥”,它能讓我從更高層次來認識、評價這些文學著作。關鍵是,這些與寫作一點兒也不沖突,只有見識了更優秀的文學作品,我才能在敘事技巧以及語言駕馭上有更高的造詣與追求。
“根深才能葉茂,觸類才能旁通。”這是邱老師常掛在嘴邊的話。中國語言文學浩瀚博大,大學四年的學習也不過是觸及一些皮毛而已。認識到這一點后,我開始靜下心來把最基礎的知識學扎實。為了能更好地閱讀古代文學中的經典著作,我花了很長時間來研究《說文解字》。有了古代漢語這把鑰匙,那些著作中的文言字句一下子就通暢起來,古代文學就這樣被我“攻克”了。
有了學習方法,我的大學生活一下子變得忙碌起來:白天進行專業課的系統學習,晚上去圖書館品讀經典著作,偶有間隙,便進行寫作的練筆、投稿。比起開學時的無所事事,后來的日子里,我總覺得時間不夠用,那些暫時沒時間和精力閱讀的書籍,我只能無限期地往后排,常常會心生“滄海遺珠”的遺憾。
沒有想到,一封偶然的郵件,打開了我的心結。回望四年的學習,從抗拒到認同,再到漸入佳境,認知和態度尤為重要。只有敞開懷抱,腳踏實地,才能在浩瀚的學海中自由暢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