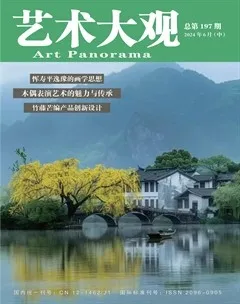自??然
“美”都是“神”的手所造的。假手于“神”而造美的,是藝術家。
這里的火車站旁邊有一個傴僂的老丐,天天在那里向行人求乞。我每次下了火車之后,迎面就看見一幅米葉(Millet)的木炭畫,充滿著哀怨之情。我每次給他幾個銅板——又買得一幅充滿著感謝之情的畫。
自然的美的姿態,在模特兒上臺的時候是不會有的;只有在其休息的時候,那女子在臺旁的絨氈上任意臥坐,自由活動的時候,方才可以見到美妙的姿態,這大概是世間一切美術學生所同感的情形吧。因為在休息的時候,不復受人為的拘束,可以任其自然的要求而活動。“任天而動”,就有“神”所造的美妙的姿態出現了。
人體的美的姿態,必是出于自然的。換言之,凡美的姿態,都是從物理的自然的要求而出的姿態,即舒服的時候的姿態。這一點屢次引起我非常的銘感。無論貧賤之人,丑陋之人,勞動者,黃包車夫,只要是順其自然的天性而動,都是美的姿態的所有者,都可以禮贊。甚至對于生活的幸福全然無分的,第四階級以下的乞丐,這一點也決不被剝奪,與富貴之人平等。不,乞丐所有的姿態的美,屢比富貴之人豐富得多。試入所謂上流的交際社會中,看那班所謂“紳士”,所謂“人物”的樣子,點頭,拱手,揖讓,進退等種種不自然的舉動,以及臉的外皮上硬裝出來的笑容,敷衍應酬的不由衷的言語,實在滑稽得可笑,我每覺得這種是演劇,不是人的生活。作這樣的生活,寧愿作乞丐。
被造物只要順天而動,即見其真相,亦即見其固有的美。我往往在人的不注意,不戒備的時候,瞥見其人的真而美的姿態。但倘對他熟視或聲明了,這人就注意,戒備起來,美的姿態也就杳然了。從前我習畫的時候,有一天發現一個朋友的pose(姿態)很好,要求他讓我畫一張Sketch(速寫),他限我明天。到了明天,他剃了頭,換了一套新衣,挺直了項頸危坐在椅子里,教我來畫……這等人都不足與言美。我只有和我的朋友老黃,能互相賞識其姿態,我們常常相對坐談到半夜。老黃是畫畫的人,他常常嫌模特兒的姿態不自然,與我所見相同。他走進我的室內的時候,我倘覺得自己的姿勢可觀,就不起來應酬,依舊保住我的原狀,讓他先鑒賞一下。他一相之后,就會批評我的手如何,腳如何,全體如何。然后我們吸煙煮茶,晤談別的事體。晤談之中,我忽然在他的動作中發現了一個好的pose,“不動!”他立刻石化,同畫室里的石膏模型一樣。我就欣賞或描寫他的姿態。
不但人體的姿態如此,物的布置也逃不出這自然之律。凡靜物的美的布置,必是出于自然的。換言之,即順當的、妥帖的、安定的,取最卑近的例來說:假如桌上有一把茶壺與一只茶杯。倘這茶壺的嘴不向著茶杯而反向他側,即茶杯放在茶壺的后面,猶之孩子躲在母親的背后,誰也覺得這是不順當的、不妥帖的、不安定的。同時把這畫成一幅靜物畫,其章法(即構圖)一定也不好。美學上所謂“多樣的統一”,就是說多樣的事物,合于自然之律而作成統一,是美的狀態。譬如講壇的桌子上要放一個花瓶。花瓶放在桌子的正中,太缺乏變化,即統一而不多樣。欲其多樣,宜稍偏于桌子的一端。但倘過偏而接近于桌子的邊上,看去也不順當、不妥帖、不安定。同時在美學上也就是多樣而不統一。大約放在桌子的三等分的界線左右,恰到好處,即得多樣而又統一的狀態。同時在實際上也是最自然而穩妥的位置。這時候花瓶左右所余的桌子的長短,大約是三與五至四與六的比例。這就是美學上所謂“黃金比例”。黃金比例在美學上是可貴的,同時在實際上也是得用的。所以物理學的“均衡”與美學的“均衡”頗有相一致的地方。右手攜重物時左手必須揚起,以保住身體的物理的均衡。這姿勢在繪畫上也是均衡的。兵隊中“稍息”的時候,身體的重量全部擱在左腿上,右腿不得不斜出一步,以保住物理的均衡。這姿勢在雕刻上也是均衡的。
故所謂“多樣的統一”“黃金律”“均衡”等美的法則,都不外乎“自然”之理,都不過是人們窺察神的意旨而得的定律。所以論文學的人說,“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論繪畫的人說,“天機勃露,獨得于筆情墨趣之外”。“美”都是“神”的手所造的,假手于“神”而造美的,是藝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