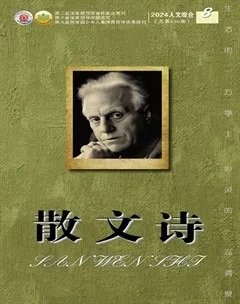未竟的母語
2024-09-22 00:00:00
散文詩(青年版) 2024年8期
一種通常被視作錯誤的翻譯原則是可行的嗎?也就是說,翻譯不是使外語母語化,而是使母語外語化!
本雅明在《翻譯的使命》一文中頗有意味地引用過魯道夫·潘維茲在《歐洲文化的危機》中說過的一句話:“翻譯家的原則性謬誤在于他始終想保持自己國家語言的偶然狀態,而不是讓自己國家的語言受到外國語的激烈撼動。翻譯家特別是在翻譯與自己的語言相距很遠的語言時,必須回到語言本身最終的要素上來,將語言、意象、聲音聯接為一體。翻譯家必須通過外語來拓寬深化自己國家的語言。”
無疑,本雅明將翻譯當作一項將語言從特定意義中解放出來的事業——他主張一種純粹由文本形式攜帶的、無法被還原成特定意義的“純語言”(die reine Sprache)。“謂純語言,自身不在意指或表達任何東西,但作為非表現性的創造性的語言,又以所有語言為意圖”;就其功能而言,與其說純語言是為了徹底消除意義,毋寧說,是為了破除語言的痂殼;也正是在此一意義上,書寫與翻譯的創造性才能獲得統一的合法性基礎。
只有在對創造性的追求中,我們才能意識到:真正的母語(無論它被追認為本雅明所謂的“純語言”,還是被當作它自身尚未綻開的潛能)恰好就囚禁在我們的母語之中,而書寫與翻譯的任務便是解放它。如此看來,那種錯誤的原則不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
猜你喜歡
新少年(2022年9期)2022-09-17 07:10:54
小天使·一年級語數英綜合(2020年6期)2020-12-16 02:56:41
文苑(2020年4期)2020-05-30 12:35:30
小天使·一年級語數英綜合(2018年6期)2018-06-22 10:25:54
小學生作文(中高年級適用)(2018年3期)2018-04-18 01:24:47
華人時刊(2017年23期)2017-04-18 11:56:38
華北電力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4期)2016-12-01 03:59:30
小學閱讀指南·低年級版(2016年1期)2016-09-10 07:22:44
少兒科學周刊·少年版(2015年4期)2015-07-07 21:11:17
北極光(2014年8期)2015-03-30 02:5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