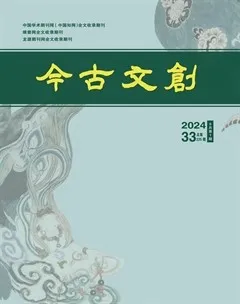《絲路古船》 : 現代海洋立場下的人物書寫
【摘要】《絲路古船》以雙線并行編排,明線摹寫打擊盜挖古船的偵察行動,暗線敘述船仔、老歐、池木鄉、練丹青、鄭天天等各人物的心境變化過程,交織構成了一部完整且精彩的打擊“盜挖古船”案件。《絲路古船》體現出作者濃烈的海洋情結與堅定的現代海洋立場,通過摹寫海洋與陸地之間的矛盾關系,呈現出強大的文學張力。本文聚焦現代海洋立場這一基點進行延伸,通過剖析作品如何通過對主要人物的書寫,揭示隱藏在背后的現代海洋立場,并分析小說如何使海洋這一意象跳脫傳統的單純背景,成為行文內在線索的創新性。
【關鍵詞】《絲路古船》;海洋立場;海洋文學;人物書寫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8264(2024)33-0013-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33.004
海洋,作為重要的文學背景,具有其獨特的魅力。現代海洋立場,即在新時代、新環境、新語境下,結合現代性思維,在認識與處理問題的過程中所呈現出傾向海洋一端的地位與態度。《絲路古船》正是這樣一部在現代海洋立場主導下應運而生的作品。小說以雙線并行的敘事方式,將敘事布景分割為陸地與海洋,實行了有效的延展。文中的人物也依照場景之異被分割:以陸地為主戰場的練丹青、鐘細兵等人;以海洋為主戰場的船仔、老歐、池木鄉、阿蘭等人;還有穿行于陸地與海洋兩個場域間的鄭天天。場域、人物、情節的交叉架構,使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可基于場域的分別,持不同的心態去閱讀,從而豐富并充實了閱讀體驗,也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閱讀期待。最為重要的是,這樣的鋪排,明顯展現出海陸之間纏繞斗爭、相依相克的關系。本文選取船仔、老歐、池木鄉這三位小說中著墨較多且具有共性與異性的人物,并將他們分為三類形象進行分析,從中剖析李師江所彰顯的現代海洋立場下人物書寫的創新性。
一、船仔:純凈的海洋之子
《絲路古船》中的船仔是最能體現出作者海洋情結與海洋立場的代表。與許多作品中聯結自然與人類二者的角色相似,如沈從文《邊城》中由天與地靈氣幻化孕育而生的“自然女兒”翠翠一樣,船仔可以被認為是在海洋哺育下所成長起來的海洋之子,其生命中所體現出的本然性與壯美性,是海洋內聚的體現。他是海洋純凈本質的化身,代表著海洋的本性,即未受污染、清澈純真、精美無瑕的本原海洋。
李師江在《絲路古船》的后記中,提到這一故事的藍本取材于他的一個島民朋友的真實經歷。李師江稱“寫小說的目的也非常單純,第一就是寫一個好看得不得了的海上故事,第二,就是塑造一個海島上自由而固執的靈魂。”[1]船仔正是“海島上自由而固執的靈魂”。小說開篇船仔的初次登場,本身就帶著一股子咸濕海風的氣息。首先,在海邊生活的人水性好,這是自然,但像船仔一樣具有天然如此好水性的人實屬罕見。船仔,似乎與晉代張華《博物志》中所記載的海洋族群“鮫人”[2]類似。這個氤氳著神話氣息的人物活靈活現地出現在讀者眼前,這是李師江的高明之處:他借助對人物的描寫,帶領身處陸地的讀者順著船仔的視野仿佛也置身于大海的世界當中,使讀者作為其中的參與者也進入了故事里,借船仔之眼,讀者看到了神奇的龍鰻,看到了玄幻的深海,這是李師江詮釋“在場性”這一概念的體現。
在中國古代海洋文學中,抒情者和敘述者始終與海洋保持著一定的距離。倪濃水據此指出:“‘遙望’而非‘在場’是中國古代海洋文學描述的基本視角。海洋是一種想象和寄托的附著對象,一種‘思想性和審美性的空間’。”[3]從古至今,人們對“進入海洋”做了不同的努力,如何打破“望洋興嘆”這樣的尷尬局面在中國的歷史發展中具有歷時性與共時性兩個層面,且具有一定的歷史傳承性。從這一角度上看,船仔這一人物的塑造,承續了這一歷史傳統。其次,船仔的性格也代表著海洋性格的一個剖面——自由、豁達、直接、純潔。在古湖島,男孩成年后,照慣例應該偷渡到美國去掙錢,這似乎是古湖島男人的一項成年禮,也是標志他們長大成人的“里程碑”。
前往美國這樣的行徑似乎是逐大波隨大流的無個性化表現,但事實上,這并非完全是為了塑造無個性者,相反,是通過世俗所為更加襯托出船仔身上所保有的純凈與空靈,加強了與世俗無個性者的對比度。船仔并不希望離開古湖島去美國端盤子,他實際上舍不得這里的海。潛入海底,被海擁抱,邂逅呆萌的魚群;偶爾遇到海底的龍鰻,能與它斗智斗勇,激戰一番,這是船仔覺得舒適的生活。當少林跟船仔討論挖掘到元青花瓷能賣出大價錢時,船仔覺得一萬與一千萬沒什么區別,表現出對金錢的漠不關心。接著面對少林問他分到錢了之后想干嗎時,船仔的回答仍然很是質樸:“我不分錢,我是來報恩的。”少林見他如此軸,索性直接問他,如果有一大筆錢最想干什么,船仔的回答是:“買條至少帶兩個發動機的大船”,“打魚不打魚無所謂,就是可以更自在,可以到鯨魚出沒的地方”。船仔以略帶童話色彩的回答表明了自己內心于海洋的深度眷戀。
與一般漁民的心態完全不同,一般漁民秉承的是靠海吃海的維系方針,對海雖持有感激之情,但深層根因仍是企圖依靠海滿足自身的生存需求,本質上仍然是基于自身獲利的人類本位心態;而船仔則與此相異,從他的回答中可以嗅出他身上的海洋氣息,是真正對這片大海愛得深沉,想要去探尋更加豐富的海洋魅力,以充盈自己的內心,體現出他對大海的關切,是真正的自然本位心態。
面對池木鄉逼迫船仔父子二人成為“水鬼”替其挖掘古船,尋找元青花瓷的要求,船仔表現出了強烈的抗拒,因為他認為這似乎是對海洋的冒犯,同時也是對生命的褻瀆。不同于父親老歐始終將自己置于低位,船仔并不害怕兇狠暴虐的池木鄉,且始終認為他與池木鄉之間是平等的地位,堅持他們只是幫池木鄉做事,自己與父親并不是奴隸的堅定態度。面對池木鄉的壓制,船仔的內心絲毫沒有動搖,沒有害怕,但為何選擇一味地忍讓,其癥結還是在自己的父親老歐。他不想因為自己的抗爭而讓父親選擇自己傷害自己,也不想讓父親因為自己而受到池木鄉的虐待,所以他只能選擇繼續忍讓池木鄉。這是船仔作為一個十八歲的青年所保有的“情”與“義”,同時也是船仔海洋性格的兩面涵蓋:溫柔雋永與剛烈無畏。
可見,小說從船仔的外貌、性格以及如何處理與周圍人的關系三個方面表現出其為純凈的海洋之子。他純凈,善良,不諳世事;向往自由,熱愛大海;骨子里纏繞著一股剛烈、頑強、正經的魂。在最后寫給鄭天天的信中,表露出了船仔對陸地的天生排斥與不信任,對“謊言”這種陸地產物的反感與逃避。倪濃水在提到“海洋”這一意象時,將海洋的描述分為:現實海洋與象征海洋,而后者顯示出了更加強勢的文化影響。“海洋的‘神圣-圣潔’寓意深刻地影響著后人,所以每逢‘亂世’,總有人會萌生‘下海’之念:或者希望移居‘海上’,或者借‘海洋空間’來映射、反襯‘現實陸地’”[3]。李師江借“海洋之子”船仔這一人物,與陸地形成鮮明的對照,發起了對陸地宣戰的先鋒號角。
二、老歐:悲哀的海洋受縛者
老歐,主人公船仔的父親。與海洋文學作品中普遍展現漁民不屈向上、奮發斗爭的硬漢性格不同,李師江筆下的老歐更顯出溫順純良的一面。他淳樸善良、關懷家人。面對自己遭遇海難而去世的妻子,老歐擔心她變成孤魂野鬼,紙錢燒得一年比一年多,還會嘟嘟囔囔地同妻子說話;為了船仔成年后能順利出國,他想盡方法要賺到更多的錢,為此不惜危險也要前往馬祖島一帶去捕撈梭子蟹。他恪守海事禮俗。作為有神論者,他對周圍所有的事物都充滿敬畏,特別是大海。雖然會受到船仔“整天伺候神鬼,就是不懂得伺候自己”的質疑,但老歐仍然默默恪守著“生活自有的一套法則”,始終堅定著對海神、媽祖的信仰,正因為此,他才有了面對大海的精神底氣。
“海洋既有人可以掌握而產生美感的一面,又有人不能掌握而產生悲恐的一面,可以說這也是科學局限的一面和人生充滿命運感的一面。”[4]人類的誕生雖然起源于海洋,但由于長期身處陸地,當置身海洋這一陌生場域時,往往會經歷從不安到恐懼的心理變化,敬畏、恐懼、認命等情緒在此過程中逐漸上揚,促使人們對自然信仰、神秘力量進行反思、依賴,最終起到維穩自己內心的作用。但對神明的敬畏之心,亦會造成兩面的影響。小說中,老歐堅信自己與船仔被池木鄉所救是媽祖的神思,做人要懂得知恩圖報,更要知道如何回饋神思。因此在面對自己不想做的“盜挖”工作時,老歐依然選擇聽從池木鄉的差遣,因為他認為,如果違抗他的意思,那就是與媽祖的神思作對,會遭遇不幸。老歐對池木鄉的言聽計從,表面上是為了保全兒子的性命,但究其思想根源,是深層次的信仰桎梏。
在染上“水鬼病”后,老歐的種種念想與行為,體現出他作為傳統海上討生者,在深層次信仰桎梏下所展現的強烈的海洋意識。他的首要愿望就是回家,因為他認為客死他鄉,魂魄不歸,這是比死本身更糟糕的事。他始終認為是因為挖到了海底的百年骷髏頭,被鬼魂的怨氣纏身才發病。他讓船仔替他去桃花塢上的墓念《地藏經》,祈求能夠得到鬼魂的原諒。就算自己的身體狀況已經惡化,他還不忘吩咐船仔要繼續聽從池木鄉的吩咐,繼續下海幫他做事。此時,老歐受到深層思維中海事信仰的束縛,大腦已經失去了正常的判斷能力。從客觀而言,老歐的發病是因為沒日沒夜替池木鄉賣命尋找古船所致,染上“水鬼病”只是邁向生命終結的導火索。老歐的一生,始于海,也終于海,一輩子被海洋與海事信仰所束縛,海洋受縛者終落得如此令人唏噓的下場。
老歐的人物形象與海洋息息相關。一方面,老歐可以看作海洋的一面化身,他有著海洋沉穩、堅守、包容、隱忍的性格,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如礁石一樣木訥、沉默、堅硬。面對外界對他的欺侮和脅迫,他總能在內心找到一片棲息地,轉變自己的思維,從而適應新的環境。而長期的海洋經驗,以及父親與丈夫雙重身份的加持,更凸顯出老歐身上的那股“海狼狠勁”。另一方面,老歐的身份是漁民,漁民對各種海事禮俗禁忌的敏感與恪守,是屬于這個身份的鮮明烙印。
不管是漁民的本職還是后來的“水鬼”身份,與海洋的羈絆聯系始終貫穿其中。老歐所從事的前后工作,經歷了從主動親近海洋到被動褻瀆海洋的轉變過程。在心態層面上,對海洋的褻瀆行徑不斷拷打著老歐的內心,因為不能違背神思而選擇繼續“盜挖”,但“盜挖”的同時又是對海洋的褻瀆,原本對信仰的無上尊敬轉變為了對信仰的持續冒犯,這使老歐的內心備受煎熬,影響了他的思維與身體狀況,一步一步邁向死亡。
李師江此前的海洋文學作品《黃金海岸》,精髓之處“在于人與海洋之間的情感聯結,以及圍繞海洋所形成的風俗習慣、民間信仰,在小說中獲得了濃墨重彩的書寫。”[5]如果說在《黃金海岸》中,海事習俗與海洋信仰起到了正向的助推作用,那在《絲路古船》中則轉變為了反向的束縛。崇敬海洋的心態造成了褻瀆海洋的結果,這無疑加重了文本表達的諷刺性。這一正一反所產生的張力與擴容,彰顯了李師江對海事禮俗的辯證眼光。
透過老歐這一人物,展示了當原本站在海洋立場上的角色邁向另一極端時,所經受的靈魂拷打以及命運的最終沉淪。老歐與船仔這對父子,雖與海洋同脈,卻走向了不一樣的結局,于更深層面顯示了以船仔為代表的新一代漁民和與老歐為代表的老一代漁民在對待海洋的態度、對陸地的抗性等方面的差異,彰顯了李師江所立足的現代話語關照下的海洋立場,也啟發讀者進行思考:關于海洋與傳統海事信仰,堅守的尺度應如何把握?
三、池木鄉:海陸屬性撕扯下的異化者
池木鄉作為盜挖古船活動的二把手,是小說著墨較多的主要人物之一。筆者認為,李師江是有意將池木鄉與船仔放置于兩個極端進行書寫。池木鄉與船仔,都可視為海洋的化身,但各種原因的交叉,二者卻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兩條道路。
為何說池木鄉同樣也是海洋的化身?第一,從池木鄉的原始身份出發,池木鄉出身海島,同樣也是漁民。受經濟狀況不佳所迫,再加上其本身心高氣傲,覺得自己將來定能干出一番大事業,但因為沒有合理的渠道來實現自己所謂的“抱負”,才走上了非法走私這條“一時來錢快”的道路。走私,屬于陸地習氣侵蝕海洋的典型行徑。池木鄉在走私過程中被陸地所帶來的污濁習氣侵蝕,成為“海洋的叛徒”。第二,池木鄉的性格暴戾,做事手段直接,常以蠻橫兇惡的態度示人,也只有在面對自己的女人阿蘭時,才會展現其寵溺的一面,當然這也是建立在阿蘭沒有影響到他利益謀取的前提下。小說中提到“女人上船,晦氣一年”的航船忌諱,池木鄉因為阿蘭跑到船上,竟然大罵自己心愛的女人晦氣,并讓她趕緊從船上滾下來。種種行徑都可窺見,池木鄉身上屬于海洋性格的另一剖面:海洋獸性。他為了聚攏團隊,保證盜挖計劃得以順利進行,先后將少林、老歐殺死,將鄭天天囚禁于荒島,甚至一度想要置其于死地,在這種種事件中,池木鄉毫無人性悲憫之心可言。
但另一方面,池木鄉在面對阿蘭與阿蘭的女兒之時,又不免讓人意識到本質上他仍然是溫熱的人類,還尚存一絲人性的柔軟地。池木鄉的角色定位可視為“被陸地所污染的海洋之子”。阿米蒂奇指出,因為人們長期生活在陸地上,因而對陸地的依戀情緒比對海洋要深。這種心態被稱為“陸地中心主義”。“長期以來,‘陸地中心主義’在人的大腦中根深蒂固,海洋被看成是與陸地對立的、險象叢生的、充滿敵意的場所。”[6]但在小說中,相較于海洋,陸地更是險象環生、風險迭出的不潔危險之地。他刻著海洋獸性的烙印,在主動與被動間與陸地產生了千絲萬縷的聯系,他的靈魂在陸地與海洋的矛盾場域中不斷被撕扯摩擦,最終淪為了如此畸形的異化形態。
李師江立足于反向角度,通過對池木鄉的書寫,詮釋了他堅定的海洋立場。通過陸地對人的異化,將陸地與海洋的矛盾聚焦于池木鄉這一主體進行展開。池木鄉的人格發展過程,象征著“陸地習性”與“海洋本性”從互相制衡階段逐漸過渡到二者失衡的階段。“陸地習性”指追求世俗欲望、必須堅持弱肉強食方針才能存活下來的心流體現;“海洋本性”則是自由無拘束、純潔、不諳世事變遷的本原人格。“陸地習性”在此過程中占據上風,“海洋習性”逐漸被消磨殆盡,最終平衡完全被打破,池木鄉也在此時完成了“異化”的全過程。
根據西方“萬物鏈”的觀念,每個生靈都有自己在固定的位置,不能隨意更改,如果其中一環發生了異化,那整個宇宙的秩序就會紊亂,世界將會崩塌。在這條“萬物鏈”中,人類因為具有部分的理性,與在其上位的天使有所類似,但因為人有各種各樣的欲望,更是與“萬物鏈”之下的獸類相似。人如果努力踐行諸如忠誠、希望、節儉等美德,則會趨向天使;而如果過分放縱自己的欲望,附著貪婪、嫉妒、暴怒等負面屬性,就會使自己異化為野獸。為了陸地上美好的繾綣,任由自己無節制的“陸地欲望”不斷膨脹而選擇冒犯海洋,池木鄉的“異化”已有端倪。在海陸屬性相互撕扯的過程中,池木鄉以詭異的形態進入海洋,背離了海洋的情感基點,最終邁向終結的深淵。在“萬物鏈”中,他們對自己的定位模糊,連作為人類所帶有的部分理性也完全拋棄,徹底淪為了野獸,最終毫無節制地墮落下去。
四、現代海洋書寫:回歸生命本源的寫作
“時代的認知裝置和文化精神決定了文學中海洋書寫的不同形態。”[7]在新時代、新環境、新語境下,李師江是如何結合現代創新思維,在人物書寫這一環節來彰示現代海洋立場,創作出具有現代海洋立場的海洋作品呢?
李師江筆下的海洋已經被賦上了“泛浪漫主義與現代化”的意蘊象征。海洋,作為精神原鄉,呼喚著愛與自由的回歸。“大海之子”船仔愛海愛得深沉,由于海洋立場的強烈統攝、對自由的向往與遠離復雜的淳樸心態,使他最終拒絕了鄭天天對他的“補償” ——讓船仔在學校繼續學習,之后投考體育專業的安排,同時也毅然決然終止了與鄭天天青澀的無果邂逅。鄭天天作為小說中穿行于陸地和海洋兩個場域的人物,身上更多沾染的是陸地的氣息。李師江非常巧妙地通過一種“離岸”行徑,通過二者的交往,將帶有陸地元素的鄭天天與充溢著海洋元素的船仔融合起來,顯示出一種重組還原的力量。而同時,海與岸也構成了一組指涉關系,并且依靠理性達成和諧,海的純凈最終收服了岸的繁雜。從海-岸關系的融合與對弈,上升到了生命復歸本源的層面。安排具有海洋純真品質的船仔帶領鄭天天回歸大海,讓幼時喪母的鄭天天尋找到了回歸子宮的感覺,從而體會到了海洋對她的療愈效果。如小說寫道:
鄭天天好像回到子宮,被羊水包圍著,溫暖著,重力的消失,使得人極為放松,但是因為在水底下,思緒完全集中到眼前,心中萬事消散,內心瞬間是前所未有的放松。是的,自己覺得那顆滿是傷疤的心,此刻像海綿球,柔軟死了。她猛然感覺到,自己被治愈了。沒有潛過水的人,不曉得海底的妙處:那是在另一個平行世界,也許是自己剛剛出生的那一天。
在這一層交往中,蘊含著兩層復歸的含義:一是人作為獨立個體對生命母體的復歸,二是人作為自然生靈對生命根源的復歸。作為人類生命本能的對應物,海洋與母體在此刻聯結在了一起,共同代表著生命孕育的場所。而在這段敘述中,人類也拋棄了智慧生物的高等身份,參與進了一眾生靈之中,成為自然的一部分。李師江巧妙運用人物經歷與人物性格的雙重聚焦,不露聲色地將海洋立場糅合至人物的內核之中,現代海洋立場下人物書寫的創新之處可見一斑。
在陸地上的經歷讓安于純凈大海已久的船仔需要反復去消化這段驚心動魄的心路歷程。與鄭天天的無果邂逅,船仔淺嘗到了短暫的歡愉,但更多的還是體會到了人世的險惡,最終在陸地與海洋的兩端選擇了背向陸地,重歸大海。這是李師江為船仔鋪設的最美結局,也是人類歸于海洋這一最終結局的藝術想象延伸。小說最后安排了時隔多年后,船仔短暫重歸陸地與鐘細兵相遇。已近中年的船仔仍然是孤身一人,而且總覺得人們會欺騙他,對人產生了嚴重的不信任感,選擇不相信任何人,強行遺忘過去、強行抽離記憶的籠罩,以至于“說話”這件事情對船仔來說都十分困難。經過“絲路古船盜挖事件”后的船仔,被“失語”與“失憶”雙重捆綁,其當時的狀態就像在魚缸中的金魚一般,寬廣的海洋實際上是船仔身處小小“魚缸”的放大投影。
誠然,在現代話語體系下的海洋文學、海洋書寫等基于海洋為理論背景的創作與研究逐漸被納入學科交叉視野,并產出了豐富的成果。在此過程中,各路作家也逐漸形成了文學創作的內核立場。海洋立場作為現今全球化視野下尚可繼續深入挖掘的文化心態,具有一定的歷史傳承度與拓展輻射性。“海洋既是一個充滿現代性魅力的理想他者,亦是現代中國自我體認和自我想象的未來形象。”[8]在中國當代文學,像《絲路古船》這樣通過人物書寫來進行具象化詮釋海洋立場的寫作依然可以作為繼續延展的優質創作領域,對于構建現代化海洋意識依然具有重要的意義與影響,值得我們繼續探索下去。
參考文獻:
[1]李師江.絲路古船[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3.
[2](晉)張華撰,范寧校證.博物志校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4.
[3]倪濃水.中國海洋文學十六講(修訂版)[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7.
[4]張法.怎樣建構中國型海洋美學[J].求是學刊,2014,41(03):115-123.
[5]周榮.海洋風景與地方傳統的審美書寫——以南北方地域經驗為視角[J].海峽文藝評論,2023,(03):18-22.
[6]王松林.“藍色詩學”:跨學科視域中的海洋文學研究[J].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23,46(03):35-43.
[7]周榮.海洋風景與地方傳統的審美書寫——以南北方地域經驗為視角[J].海峽文藝評論,2023,(03):19.
[8]彭松.論1980年代中國文學中的海洋熱[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1,(09):124-133.
作者簡介:
李昌達,男,漢族,廣東汕頭人,福建師范大學在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