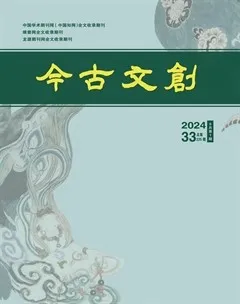柏拉圖《理想國(guó)》中蘊(yùn)含的正義思想研究
【摘要】《理想國(guó)》是柏拉圖的代表性著作,描繪了柏拉圖心中的烏托邦國(guó)家,其中所蘊(yùn)含的正義思想也是不容忽視的。柏拉圖將城邦的正義與個(gè)人的正義進(jìn)行類比,城邦的正義就是城邦里的三種群體按照各自的天性各司其職,個(gè)人的正義則是靈魂的三要素和諧統(tǒng)一,論證了個(gè)人把自己奉獻(xiàn)給城邦是有利的,力圖實(shí)現(xiàn)整體的善,最終證明正義的人是最幸福的,個(gè)人要追求靈魂的正義。
【關(guān)鍵詞】柏拉圖;《理想國(guó)》;城邦正義;個(gè)人正義;靈魂;幸福
【中圖分類號(hào)】B50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2096-8264(2024)33-0053-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33.017
《理想國(guó)》作為柏拉圖的經(jīng)典代表作和學(xué)界最具影響力的著作之一,描繪了一幅理想的國(guó)家藍(lán)圖,對(duì)后世學(xué)界產(chǎn)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其內(nèi)容涉及多個(gè)學(xué)科領(lǐng)域,但核心問(wèn)題只有一個(gè),即個(gè)人與城邦是正義好還是不正義好以及正義到底是什么。《理想國(guó)》中對(duì)正義思想的討論是人類歷史上關(guān)于正義問(wèn)題最早的系統(tǒng)論述。
一、柏拉圖正義思想的背景
任何哲人思想都不可能憑空產(chǎn)生,都與他的個(gè)人經(jīng)歷和社會(huì)現(xiàn)狀相關(guān)。柏拉圖也不例外,他在《理想國(guó)》中提出的正義觀及對(duì)理想社會(huì)的描述也都與他當(dāng)時(shí)所處的社會(huì)環(huán)境緊密相關(guān)。雅典在與伯奔尼撒之間的戰(zhàn)爭(zhēng)中慘遭戰(zhàn)敗,從此之后雅典社會(huì)危機(jī)四伏,戰(zhàn)亂時(shí)常發(fā)生,整個(gè)希臘的城邦制度開(kāi)始走向衰敗。面對(duì)這樣的現(xiàn)狀,身為名門之后的柏拉圖心系百姓,對(duì)墮落為寡頭政治的雅典貴族政治產(chǎn)生不滿。柏拉圖早期跟隨蘇格拉底學(xué)習(xí)直至蘇格拉底被處死,隨后與蘇格拉底的其他弟子一同周游各地,他的思想受到了蘇格拉底的極大影響。在柏拉圖看來(lái),過(guò)分的民主制度造成了精英制的寡頭政治,因此,只有真正的正義才能夠改變現(xiàn)狀、拯救社會(huì)。柏拉圖的正義觀中表現(xiàn)出對(duì)平息戰(zhàn)亂和穩(wěn)定社會(huì)的理想,對(duì)城邦和個(gè)人的設(shè)定也在事實(shí)上反映了渴望奴隸主貴族統(tǒng)治回歸的愿景。
《理想國(guó)》原名是“republic”(共和國(guó)),這本身并未包含“理想”之意,但書(shū)中卻描述了一個(gè)正義、和諧、美好的理想社會(huì),這個(gè)理想社會(huì)與戰(zhàn)亂動(dòng)蕩、世風(fēng)日下的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形成了鮮明對(duì)比。《理想國(guó)》所描繪的藍(lán)圖是正義的公民在正義的城邦中從事正義之事、過(guò)著幸福的生活。因此,對(duì)“正義”的探求便成為貫穿本書(shū)的主線,柏拉圖也因此可以被認(rèn)為是系統(tǒng)探討正義問(wèn)題的鼻祖。
二、柏拉圖的正義思想
(一)在《理想國(guó)》中尋找正義
根據(jù)對(duì)正義的不同方面的探討,可以將《理想國(guó)》劃分為五個(gè)部分,第一卷是第一部分,是整部作品的引入部分和預(yù)備階段,討論了正義的本質(zhì)與作用。第二卷至第四卷是第二部分,討論的主題是何為正義以及正義的人是否比不正義的人更幸福。第五卷至第七卷為第三部分,談?wù)摰氖巧频睦砟顔?wèn)題,并認(rèn)為正義本身來(lái)自善。第八卷至第九卷是第四部分,圍繞四種墮落體制進(jìn)行了討論,并提出三套完整的“推論”,最后得出正義者更快樂(lè)的結(jié)論。第十卷則為第五部分,通過(guò)靈魂輪回論證靈魂不死,說(shuō)明正義者生前死后都比不正義者更幸福。
在《理想國(guó)》的首卷中,柏拉圖通過(guò)蘇格拉底與好友的辯論引出了對(duì)正義的不同看法。克法洛斯的正義觀代表了老年人的觀點(diǎn),認(rèn)為正義就是不欠債;柏拉圖以武器不能還給變成瘋子的朋友為例來(lái)反駁他。玻勒馬霍斯的正義觀則代表了中年人,認(rèn)為正義就是每個(gè)人被給予恰如其分的報(bào)答。色拉敘馬霍斯發(fā)表了自己的觀點(diǎn),認(rèn)為正義就是強(qiáng)者的利益,“我說(shuō)正義不是別的,就是強(qiáng)者的利益。”[1]338柏拉圖反對(duì)這種說(shuō)法,認(rèn)為強(qiáng)者犯錯(cuò)時(shí),反倒有利于弱者。之后進(jìn)入第二回合,討論正義者是否有益。柏拉圖做出四個(gè)反駁:第一,將技藝與掙錢之術(shù)分離;第二,正義者不愿意與不正義者爭(zhēng)強(qiáng)好勝,由此證明正義的人又好又聰明,而不正義的人則又壞又笨;第三,不正義者會(huì)為了保全自己利益殘害敵人,但不至于自相殘害,原因是他們之間存在正義;第四,所謂正義是指心靈的德性,而不正義則是心靈邪惡。
在第二卷至第四卷中,柏拉圖借蘇格拉底之口對(duì)正義的定義進(jìn)行了討論。在這里,柏拉圖將城邦的正義與個(gè)人的正義進(jìn)行了區(qū)分。柏拉圖認(rèn)為,正義的城邦需要不同人各司其職,各自充當(dāng)自己的職責(zé)并發(fā)揮作用。城邦中的三個(gè)階層分別是統(tǒng)治者、護(hù)衛(wèi)者和生產(chǎn)者,統(tǒng)治者擁有智慧的美德,護(hù)衛(wèi)者擁有勇敢的美德,生產(chǎn)者則擁有節(jié)制的美德。他們分別發(fā)揮各自的美德,在哲學(xué)王的統(tǒng)治之下各司其職、各盡其能,在這種狀態(tài)下的城邦可被看作正義的。而關(guān)于個(gè)人的正義方面,蘇格拉底認(rèn)為靈魂的三要素是理智、激情和欲望,這三方能分別與智慧、勇敢和節(jié)制相對(duì)應(yīng)。理智是聰明智慧的,可以代表靈魂進(jìn)行謀劃;激情是勇敢沖動(dòng)的,需要服從和協(xié)助理智;欲望則是代表貪婪,需要用理智和激情來(lái)管理并節(jié)制欲望。當(dāng)一個(gè)人的理智起主導(dǎo)作用,引領(lǐng)激情、控制欲望,即理智、激情和欲望三者處于和諧有序的狀態(tài)時(shí),個(gè)人的正義就獲得了實(shí)現(xiàn)。
隨后在第五卷至第七卷中,柏拉圖指出“善的理念是最大的知識(shí)問(wèn)題,關(guān)于正義等等的知識(shí)只有從它演繹出來(lái)的才是有用的和有益的”[1]505,他認(rèn)為善是最高的知識(shí),正義本身也來(lái)自善。那些知識(shí)匱乏、脫離善、憑借運(yùn)氣生活的人是不正義的、渾渾噩噩的,因?yàn)樗麄儾涣私馍啤⒅R(shí)和正義。一個(gè)真正有知識(shí)的人會(huì)竭力尋求實(shí)在的善、正義和美。在人類的認(rèn)識(shí)活動(dòng)中,“善”發(fā)揮了中介作用,一方面賦予人類理性認(rèn)識(shí)的能力,另一方面賦予可認(rèn)識(shí)事物的本質(zhì)。換言之,人類理性借助“善”的理念從真正意義上認(rèn)識(shí)事物的本質(zhì)。
第八卷至第九卷討論的中心話題是正義者是否有益,即做一個(gè)滿口仁義的偽君子,還是一個(gè)正義的人。柏拉圖借蘇格拉底之口談?wù)摿怂姆N墮落的政制:榮譽(yù)政制、寡頭政制、民主政制、僭主政制。這四種政制在缺陷程度上是層層遞增的,榮譽(yù)政制則是由美好的王政國(guó)家退化而來(lái)。這五種政制對(duì)應(yīng)產(chǎn)生了五種人物,首先是最完美的王者型人物,其次是分別存在缺陷且缺陷層層遞增的貪圖名譽(yù)型人物、寡頭型人物、民主型人物和僭主型人物。這五種人物中,王者型人物具有王者氣質(zhì),最能自制,因此他是最善者和最幸福的人;而僭主型人物是最不正義者和最不幸的人,因?yàn)樗幱诏偪竦挠?qū)使之下,他的心靈充滿大量的奴役和不自由,這不僅使自己成為極端悲慘的人,也使得周圍人成為悲慘的人。由此證明了正義者更為快樂(lè)。至善者和正義的人是最幸福的人。
在第十卷中,通過(guò)肉體的疾病導(dǎo)致死亡,引申到靈魂的惡對(duì)靈魂的傷害,說(shuō)明惡不能毀滅靈魂,“既然任何惡都不能毀滅它,可見(jiàn),它必定是永恒存在的。既然是永恒存在的,就必定是不朽的。”[1]416柏拉圖論證了靈魂是不朽不滅的,而正義本身就是最有益于靈魂自身的,通過(guò)靈魂輪回的觀點(diǎn),柏拉圖想說(shuō)明正義者無(wú)論在生前還是死后都能得到榮譽(yù)和報(bào)償,正義者無(wú)論生前還是死后都比不正義者幸福。柏拉圖提出的這種懲惡揚(yáng)善的正義,似乎是一種靈魂的正義的回歸,也是整篇對(duì)話的完美結(jié)束。
(二)城邦正義與個(gè)人正義
在柏拉圖之前的哲學(xué)家大都認(rèn)為正義是某種外在的東西,而柏拉圖則持有不同的觀點(diǎn),他追求個(gè)人靈魂深處的和諧。他從城邦正義切入,再與個(gè)人靈魂的正義進(jìn)行對(duì)比和類推,認(rèn)為這個(gè)思路會(huì)更清晰的表達(dá)正義的內(nèi)涵。
“我們建立這個(gè)國(guó)家的目標(biāo)并不是為了某個(gè)階級(jí)的單獨(dú)突出的幸福,而是為了全體公民的最大幸福;因?yàn)椋覀冋J(rèn)為在一個(gè)這樣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正義。”[1]420一個(gè)完整的城邦由三類人構(gòu)成,分別是:統(tǒng)治者、護(hù)衛(wèi)者、生產(chǎn)者。三個(gè)階層的人由于天性具有差異和不同,因而從事不同的工作,但不同的工作不是任意分配的,而是根據(jù)他們不同的天性分配到最適合他們的不同崗位。在柏拉圖看來(lái),這種不同人根據(jù)自己美德各司其職的城邦是正義的,“當(dāng)生意人、輔助者和護(hù)國(guó)者這三種人在國(guó)家里各做各的事而不相互干擾時(shí),便有了正義,從而也就使國(guó)家成為正義的國(guó)家了。”[1]158另一方面,盡管三個(gè)階層的不同人各司其職,但并不是相互割裂,而是相輔相成,才能共同建立一個(gè)正義的城邦。統(tǒng)治者擁有智慧和理智,統(tǒng)領(lǐng)城邦的發(fā)展;護(hù)衛(wèi)者擁有勇敢和激情,聽(tīng)從統(tǒng)治者智慧的安排以保護(hù)城邦安全;生產(chǎn)者智力低下且擁有欲望,因此需要有節(jié)制的美德,同時(shí)聽(tīng)從智慧的統(tǒng)治者與勇敢的護(hù)衛(wèi)者的指揮安排。不同的人各司其職又互相合作建立了一個(gè)正義的城邦,這個(gè)正義的城邦是善的,同時(shí)擁有智慧、勇敢、節(jié)制三種不同的美德。當(dāng)有人違反自己的天性與美德,從事其他行業(yè)的職位,例如,一個(gè)擁有醫(yī)學(xué)天賦的人去從事苦力做最下層工人,一個(gè)魯莽無(wú)知的人成為統(tǒng)治者,這些都會(huì)給城邦帶來(lái)?yè)p失甚至災(zāi)難,從而墮落為一個(gè)不正義的國(guó)家。換言之,任何與美德相違背的行為都會(huì)給城邦帶來(lái)災(zāi)難。
城邦的正義是三個(gè)階層按照各自的天性各司其職,將城邦與個(gè)人類比,還需考察個(gè)人的正義。柏拉圖指出,靈魂的三要素是理智、激情和欲望。理智與智慧相對(duì)應(yīng),激情與勇敢相對(duì)應(yīng),欲望與節(jié)制相對(duì)應(yīng),只有靈魂中的每一個(gè)要素都只從事自己相對(duì)應(yīng)的事物才是正義的、“善”的靈魂,“我們每個(gè)人如果自身內(nèi)的各種品質(zhì)在自身內(nèi)各起各的作用,那他就也是正義的,即也是做他本分的事情的。”[1]171當(dāng)一個(gè)人違背了天性,靈魂的要素與美德進(jìn)行了錯(cuò)誤搭配,就會(huì)對(duì)靈魂造成傷害。例如,一個(gè)靈魂中帶有欲望的人同時(shí)擁有智慧的美德,那么他可能通過(guò)他的智慧去實(shí)現(xiàn)無(wú)盡的欲望,這個(gè)人的靈魂就是不正義的,并且會(huì)對(duì)他人、對(duì)城邦造成傷害。另一方面,只有一個(gè)人的靈魂中同時(shí)擁有智慧、勇敢、節(jié)制的美德,這個(gè)人才是正義的、是“善”的,缺少任何一種美德,這個(gè)人都不是正義的人、都會(huì)對(duì)靈魂造成傷害。值得注意的是,柏拉圖的“靈魂分析不單是通過(guò)類比來(lái)解釋社會(huì)——無(wú)論是美好社會(huì)還是墮落社會(huì)。它已預(yù)設(shè)并豐富了人類作為政治動(dòng)物的概念,人的動(dòng)機(jī)必然具有社會(huì)性的維度”[2]210,因此,他得出正義的個(gè)人與正義的城邦是一致的,因?yàn)樗鼈兌甲裱粋€(gè)原則,即每個(gè)部分都只做符合自己天性的工作而不相互干涉,并且在善的指導(dǎo)下成就了各自的美德。
(三)善主導(dǎo)下的正義
整個(gè)《理想國(guó)》對(duì)正義的考察從未離開(kāi)過(guò)“善”。格勞孔將善分為三種,第一種善是“我們樂(lè)意要它,只是要它本身,而不是要它的結(jié)果”[1]44;第二種善是“我們之所以愛(ài)它既為了它本身,又為了它的后果”[1]44;第三種善是“我們愛(ài)它們并不是為了它們本身,而是為了報(bào)酬和其他種種隨之而來(lái)的利益”[1]44。面對(duì)格勞孔的提問(wèn),蘇格拉底認(rèn)為第二種“善”是正義的“善”,也是最好的“善”。換言之,在可知的世界中,正義是最高的“善”,同時(shí)正義的過(guò)程會(huì)帶來(lái)“善”的結(jié)果,人們可以在這種“善”的正義過(guò)程和正義結(jié)果中獲得幸福。
然而,要證明正義本身是一種善無(wú)疑是困難的,這首先要知道什么是善,因?yàn)椤皼](méi)有一個(gè)人在知道善之前能足夠地知道正義和美”[3]110,人們對(duì)善的理念知之甚少,只有對(duì)善的理念進(jìn)行深刻解讀才能對(duì)正義的理念進(jìn)行理解。柏拉圖在這里借用蘇格拉底之口提出了“洞穴喻”,如果將“洞穴”比喻為人們生活的世界,生活在洞穴中的我們認(rèn)知能力有限以及受到傳統(tǒng)觀念的影響,而無(wú)法窺見(jiàn)正義。雖然蘇格拉底聲稱他無(wú)法對(duì)善進(jìn)行直接的定義,但為了能夠進(jìn)一步解釋“善”的概念,他引入了一個(gè)新的概念,即“善的兒子,就是那個(gè)看上去很像善的東西”[1]266。蘇格拉底指出,人要完成“看”這個(gè)活動(dòng),需要三個(gè)要素,看的能力——眼睛,看的對(duì)象——客觀物體,以及中間介質(zhì)—— “光”。“光”將看的能力與看的對(duì)象相連接,使得“看”這個(gè)過(guò)程順利完成,而光的真正來(lái)源則是太陽(yáng),換言之就是太陽(yáng)具有如此特殊的性質(zhì)使得“看”這個(gè)過(guò)程能夠完成,因此,太陽(yáng)就是在可見(jiàn)世界中“善的兒子”。
根據(jù)上述的“太陽(yáng)喻”,我們可以推測(cè)認(rèn)為,正義就是可知世界中“善的兒子”。當(dāng)正義表現(xiàn)在城邦方面時(shí),正義就是每個(gè)人各司其職;當(dāng)正義表現(xiàn)在個(gè)人方面時(shí),正義就是靈魂要素與美德相互匹配。由此可以推論,正義代表著某種理性秩序,這個(gè)秩序類似于太陽(yáng)以自身光亮照亮世間萬(wàn)物。同樣,在可知世界中,正義的理念規(guī)范城邦以及個(gè)人處于理性秩序之中,從而擁有了善,不同的美德在“善”的統(tǒng)領(lǐng)下各司其職,城邦與個(gè)人獲得自身存在的意義,這樣的城邦和個(gè)人都是正義的。換言之,正義的理念統(tǒng)治著可知世界,就如同太陽(yáng)統(tǒng)治著可見(jiàn)世界一樣。因此可以說(shuō),在可知世界中,正義就是“善的兒子”。
(四)正義與幸福
在《理想國(guó)》這本著作中,有關(guān)正義的人更幸福還是不正義的人更幸福的證明是貫穿在整部作品中的主線。在這里柏拉圖所說(shuō)的幸福不是指感官上的滿足,他所說(shuō)的幸福是人們對(duì)正義的主觀感覺(jué),即對(duì)靈魂三部分的內(nèi)在和諧而產(chǎn)生的感覺(jué)。人的感官的滿足可以帶來(lái)快樂(lè),但是快樂(lè)并不必然地達(dá)到幸福。柏拉圖認(rèn)為,要想獲得幸福的必要條件就是正義地生活,幸福是依附于正義的。在柏拉圖看來(lái),正義是一種美德,并且正義的人是最幸福的人,不正義的人是最不幸福的人。為此,柏拉圖進(jìn)行了兩次論證。
第一次論證是在對(duì)色拉敘馬霍斯提出的“不正義的人比正義的人幸福”的觀點(diǎn)進(jìn)行反駁時(shí)。首先,柏拉圖提出了相對(duì)復(fù)雜的方法去反駁色拉敘馬霍斯的觀點(diǎn)。第一,正義的人只想得到自己應(yīng)得的東西,不想比其他正義的人拿得多,相反,不正義的人就沒(méi)有正義的人的覺(jué)悟和高度,他們想勝過(guò)同類和不同類;第二,真正有知識(shí)的人從來(lái)不想和他同類的人去爭(zhēng)上下,而無(wú)知的人不僅僅是想勝過(guò)與他不同類的人,甚至于想要?jiǎng)龠^(guò)任何人;第三,有知識(shí)的人是好人,沒(méi)有知識(shí)的人是壞人。綜上所述,正義的人必然接近于好人,而不正義的人則接近于壞人,色拉敘馬霍斯的觀點(diǎn)被以上論證完全顛倒了。其次,柏拉圖用政治后果來(lái)論證。正義能夠帶來(lái)和諧,而不公正只能引起仇恨和廝殺等,并且實(shí)施不公正的人的內(nèi)心會(huì)非常掙扎。最后,柏拉圖用其提出的功能理論駁斥了色拉敘馬霍斯所說(shuō)的“不正義的生活是更幸福的生活”。第一,每一事物都有自己的功能,這種功能是指對(duì)于每個(gè)事物來(lái)說(shuō),只能由其來(lái)做的工作或者只有它才能做得好的工作;第二,如果一物的功能發(fā)揮得非常好,那么它就獲得了美德;第三,人的靈魂也有功能,而靈魂的美德就是正義;第四,靈魂一旦獲得正義,那他就會(huì)幸福。所以,正義的人是幸福的。此處反駁只是引入一些概念,并未完全展開(kāi),因此未能使人感到完全信服。
第二次論證是在利用語(yǔ)言和想象構(gòu)造完“理想國(guó)”后,又描述了四種墮落的制度和這四種制度中的不同品性的人。最好的制度是賢人制,以德性為善,公民是正義的人;賢人制墮落的第一步是變成榮譽(yù)制,以榮譽(yù)為善,公民是愛(ài)好榮譽(yù)的人;榮譽(yù)制墮落變成寡頭制,以財(cái)富為善,公民是愛(ài)好錢財(cái)?shù)娜耍粯s譽(yù)制墮落變成公民制,以自由為善,公民是愛(ài)好自由的人;公民制墮落變成以專制為善,即最壞的僭主制,公民是專制的人。此四種制度和公民的描寫,其目的是為了證明賢人制中的人,即堅(jiān)守正義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僭主制中的人是最不幸的人,從而重扣整個(gè)討論的主題——正義的人是最幸福的人。
三、《理想國(guó)》中的正義觀評(píng)析
(一)古典的正義觀
柏拉圖所理解的正義概念和我們現(xiàn)代意義上的正義概念是不同的。或許以現(xiàn)代的目光來(lái)考察它,是無(wú)法看清它的面目的。在《理想國(guó)》中,正義是囊括其他所有德性于其中的德性。《理想國(guó)》中的正義觀是古典的正義觀。在繼承了畢達(dá)哥拉斯思想的基礎(chǔ)上,柏拉圖把德性設(shè)想為和諧,“正義則是靈魂的內(nèi)在和諧”,這一觀點(diǎn)是一種道德式的說(shuō)明。在與玻勒馬霍斯的討論中,討論的錯(cuò)誤在于使正義成為許多技藝中的一種。正義探尋整體的好,蘇格拉底認(rèn)為知識(shí)是最高的好,而玻勒馬霍斯認(rèn)為財(cái)產(chǎn)是最高的好,正義只不過(guò)是獲得財(cái)產(chǎn)的手段而已。色拉敘馬霍斯認(rèn)為,個(gè)人利益和統(tǒng)治者的利益是矛盾對(duì)立的。“哲學(xué)恢復(fù)一個(gè)人的生活的統(tǒng)一性。正如要求于各種技藝的,哲學(xué)要求對(duì)其對(duì)象的完全獻(xiàn)身,同時(shí)它給予其從事者豐厚的獎(jiǎng)賞,因?yàn)樗撬奶煨缘耐昝阑⑹顾械阶畲蟮臐M足。只有在哲學(xué)中,對(duì)技藝之適當(dāng)運(yùn)用的關(guān)心和對(duì)一個(gè)人自己利益的關(guān)心才達(dá)成一致。”[4]56只有共同體的利益和個(gè)人利益保持平衡,個(gè)人才會(huì)履行正義。
(二)靈魂的正義觀
柏拉圖將城邦的正義與靈魂的正義進(jìn)行類比,柏拉圖的正義觀指向人的內(nèi)在靈魂。只有在理性的指導(dǎo)下,才能實(shí)現(xiàn)正義。靈魂的正義是討論的主題,柏拉圖在《理想國(guó)》中表述過(guò)城邦無(wú)法實(shí)現(xiàn),那關(guān)于城邦正義的討論的意義何在?“一開(kāi)始在城邦中尋找正義的決定,以及城邦中的正義和個(gè)人身上的正義之間的最終區(qū)別,始終把如下問(wèn)題置于我們面前:使一個(gè)城邦健康的正義是否與使一個(gè)人健康的正義相同?這一問(wèn)題的答案決定著另一問(wèn)題的答案:一個(gè)人把自己奉獻(xiàn)給城邦是否有利?”[4]69柏拉圖假定城邦的正義和個(gè)人的正義是相同的,個(gè)人把自己奉獻(xiàn)給城邦是有利的。柏拉圖的正義觀力圖實(shí)現(xiàn)整體的善,只有實(shí)現(xiàn)靈魂正義,并證明正義的人更幸福,那人們都會(huì)踐行正義了。這是一種靈魂的正義觀。
(三)柏拉圖正義觀與羅爾斯正義觀的比較
在整個(gè)人類社會(huì)發(fā)展歷史上,羅爾斯的正義觀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柏拉圖的正義觀以社會(huì)秩序?yàn)橹行模_爾斯的正義觀以人的自由權(quán)利為中心,下面將兩者的正義觀進(jìn)行簡(jiǎn)要對(duì)比。
柏拉圖的正義原則是社會(huì)中三個(gè)不同等級(jí)的人們,即統(tǒng)治者、護(hù)衛(wèi)者和生產(chǎn)者,各自做好自己分內(nèi)的工作,做與自己性格相適應(yīng)的工作,各司其職、各盡其責(zé),不能妄圖其他等級(jí)的人的工作和位置。柏拉圖的正義論認(rèn)識(shí)到了社會(huì)分工的必要性,但柏拉圖認(rèn)為這種等級(jí)劃分是永久的、無(wú)法改變的,這表現(xiàn)出其思想受到奴隸制較大的影響。他的目的是依靠把人劃分為不同的類別、各司其職看作一種永恒的正義,來(lái)實(shí)現(xiàn)一個(gè)既能維持貴族特權(quán)、又可為貧苦階級(jí)接受的社會(huì)。因此,柏拉圖的正義論是服務(wù)于貴族統(tǒng)治的穩(wěn)定,代表著沒(méi)落的貴族的利益。柏拉圖的正義論觀點(diǎn)盡管有著局限性,但對(duì)于柏拉圖所處的時(shí)代的特點(diǎn)以及其理論中所蘊(yùn)含的思想方法而言,依舊是一種值得認(rèn)識(shí)和研究的理論,如公民對(duì)待法律態(tài)度觀念上要求守法、統(tǒng)治者要有良好的德行、提倡人們追求心靈的智慧等。
羅爾斯則是在開(kāi)篇提出“正義是社會(huì)制度的首要價(jià)值”,為了論證他的正義原則,羅爾斯進(jìn)行了“原初狀態(tài)”和“無(wú)知之幕”的設(shè)定。在無(wú)知之幕后的人們,個(gè)人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地位、天賦等信息,只能進(jìn)行一般考慮。羅爾斯認(rèn)為在這種狀態(tài)下的人們選擇的原則才是最符合社會(huì)、最正義的原則,即平等的自由原則,公平的機(jī)會(huì)平等原則和差別原則。最少受益者的最大利益是羅爾斯所最為強(qiáng)調(diào)的,要保證給所有人提供真正意義上平等的機(jī)會(huì),對(duì)于那類天賦較低或社會(huì)地位相對(duì)不利的人們,社會(huì)需要給予更多的關(guān)注,將更多的資源花費(fèi)在他們身上。與柏拉圖所不同的是,羅爾斯認(rèn)為個(gè)人天賦同樣屬于社會(huì)的共同資產(chǎn),由于偶然的分配,每個(gè)人擁有的天賦也會(huì)不同,正因如此,更需要從經(jīng)濟(jì)利益或社會(huì)層面上對(duì)天賦較低的人群給予補(bǔ)償,最大可能地縮小他們與天賦較高者的差距,從而擴(kuò)大社會(huì)福利平等。
總體來(lái)說(shuō),通過(guò)對(duì)比分析柏拉圖和羅爾斯的正義原則發(fā)現(xiàn),他們?cè)诟髯圆煌臍v史背景下提出不同的正義觀,現(xiàn)代性的擴(kuò)張和自由主義的發(fā)展一定程度上破壞了傳統(tǒng)道德的作用機(jī)制,制度約束機(jī)制規(guī)則成為實(shí)現(xiàn)現(xiàn)代社會(huì)正義的必然選擇。
參考文獻(xiàn):
[1]柏拉圖.理想國(guó)[M].郭斌和,張竹明譯.北京:商務(wù)印書(shū)館,2017.
[2]馬爾科姆·斯科菲爾德.柏拉圖:政治哲學(xué)[M].柳孟盛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7.
[3]色諾芬.回憶蘇格拉底[M].鄭偉威譯.北京:臺(tái)海出版社,2016.
[4]布魯姆.人應(yīng)該如何生活[M].劉晨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9.
[5]劉飛.論柏拉圖《理想國(guó)》中城邦正義與個(gè)人正義的一致性[J].哲學(xué)動(dòng)態(tài),2014,(6).
[6]羅躍軍.柏拉圖《理想國(guó)》中的正義觀辨析[J].哲學(xué)研究,2012,(8).
[7]黃頌杰.正義王國(guó)的理想——柏拉圖政治哲學(xué)評(píng)析[J].現(xiàn)代哲學(xué),2005,(3).
[8]楊佳.柏拉圖的正義觀解析[J].人民論壇,2010,(08).
[9]王萬(wàn)松.柏拉圖《理想國(guó)》正義論研究[D].貴州大學(xué),2019.
[10]陶一桃,張超.柏拉圖經(jīng)濟(jì)正義思想研究[J].吉林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21,4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