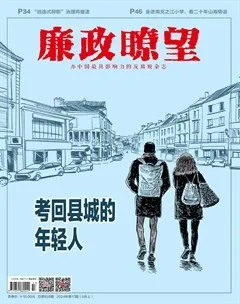“縣城編制”成為他們的新選擇

“如果只是為了追求穩定的普通生活,回到縣城其實是一個‘有性價比’的選擇。”來自安徽的周妃莎這樣評價自己的擇業決定。
經過近一年的備考,周妃莎成功“上岸”,即將入職家鄉縣城文旅局的非遺辦公室。周妃莎畢業于北京一所985院校,與許多畢業留京的同學不同,她拒絕了北京幾家公司的入職機會,轉頭選擇了家鄉的“縣城編制”。這一選擇在十年前可能還不被人理解,但隨著就業重心逐漸下沉,越來越多的人不再把立足一線城市作為自己的人生目標,轉而進入到地級城市以下地方,而縣城體制內工作頗受這部分人的青睞。除了像周妃莎這樣的應屆生,還有不少“京漂”“滬漂”以及“深漂”們趕著在35歲之前上岸“縣城編制”。
“縣城編制”緣何吸引一線青年?
對于父母和老家的親戚來說,周妃莎回縣城考公的選擇并不是那么好理解。
“我姑媽認為回來是一種‘浪費’。但這是我經過深思熟慮才決定的。為此我甚至把畢業時的幾種工作選擇做成對比表格發到網上,我發現,不少已經畢業的學姐學長都支持‘縣城編制’。”周妃莎說。
周妃莎在北京讀書7年,在家里人心中,這個從小優秀的孩子就像是未來的新北京人。“又不是找不到工作,為什么不留在北京打拼呢,再不濟,在合肥或者南京找個工作也好呀,為什么要回縣里來呢?”如今,談及女兒畢業這一年來的選擇,周妃莎的母親王燕仍然感到不解。
王燕對記者說,如今女兒即將入職,她雖尊重孩子的選擇,但對于盼望著孩子“飛出小城”的家長來說,還是覺得有些遺憾。“感覺打開的那扇門又關上了。”
為什么要回縣城?這是周妃莎做出選擇后被問到最多的問題。周妃莎坦言,在做出最終的決定前,她也糾結了很久。驅使小鎮青年們回到縣城的動機可能五花八門,但周妃莎認為,許多動機最終都指向當下青年人對工作與生活平衡的思考。
“回老家考公”這幾個字對于在大城市漂泊不定的小鎮青年們,似乎有著別樣的誘惑。“穩定、不再有職業年齡焦慮、沒有996,縣城編制好像代表著大城市艱難生活的反面。”王浩杰回憶自己回家前的心態如是說。
王浩杰表示,回鄉,不僅出于對穩定生活的渴望,更因為縣城公務員崗位的多樣性與機會。武漢大學社會學院的楊華教授指出,縣城作為一個“熟人社會”,公務員在資源分配中扮演重要角色。對于缺乏背景的青年而言,能夠在縣城成功競聘公務員職位,確實是一種成就,家庭和朋友的支持、認同往往也隨之而來。
與“縣城編制”形成強烈對比的是他們眼中一線城市工作環境“殘酷”。“普通的私企中,加班文化、末位淘汰、裁員等等都是司空見慣的事。”盡管是一名應屆生,但研究生時在大廠實習的見聞,讓周妃莎對大廠“祛魅”了。周妃莎稱,選擇回鄉考公的動機就是想避免這樣疲憊的生活。
為什么都是考老家縣城的編制?周妃莎與王浩杰有著類似考慮——一步到位。
國家公務員局數據顯示,今年國考通過資格審查的人數已達303.3萬,較五年前足足增加了133%。隨著考公熱潮的興起,“編制”也呈現僧多粥少的現象,不少青年選擇將目光投向競爭稍弱的縣域公務員崗位,“縣城編制”成為越來越受歡迎的新賽道,競爭日漸凸顯。
比起主動選擇,對于一些人來說,“縣城編制”只是一種退而求其次的考慮。“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在經濟發達的地區站穩腳跟。”在一些選擇回到縣城的人看來,在大城市打拼過后,“縣城編制”就像是留給年輕人一個拼搏失敗的“后路”。
“我當時是多手準備,哪里能去去哪里。”來自四川仁壽縣的女孩辜丹云稱,自己之所以畢業一年后才入職,是因為畢業時選調、省考結果不理想,盡管在上海讀書,但由于專業問題,找的工作收入都不高,左挑右選之間,精力花去了大半,最后匆匆報考了離家不遠的某縣城的事業編,以應付家里對于她畢業一年還不工作的施壓。“可以理解為在大城市卷不贏,也可以理解為回縣城是最優解。”
在辜丹云看來,自己比較能代表一部分人的畫像,出身縣城,家庭條件一般,大學畢業之前,對于未來的職業幾乎沒有規劃,人生的每一步都是被大潮推著走,而自己的父母也難以提供建設性的意見。“我們這樣的小鎮青年,一方面無法在大城市站穩腳跟,一方面家鄉附近沒有強二線城市可以容納自己,同時又有留在父母身邊的需求,最后就只能選擇回老家。至于進入體制,并沒有太多別的想法,主要是回縣城好像只有體制內這一條路可以走。”
回與不回,那些做出選擇的瞬間
今年33歲的劉浩杰曾是他人口中的“上進模板”。盡管出身縣城的他高考并不如意,只進入了江蘇一所大專院校,但經過努力,王浩杰一路升本,讀研,畢業后順利進入上海一家貿易公司。“以前總覺得只要努力就能有所收獲,但在上海這樣的城市,我的收獲還遠遠不夠讓我站穩腳跟。”雖然一直意識到這一點,但真正下定決心,還是因為朋友的愛情敗給現實這一故事就發生在眼前。
王浩杰說:“那是一個在上海結識的老鄉因為在上海買不起房剛剛和女朋友分手,見面時他勸我早點認清現實。如果在上海呆不住,不如趁自己能靜下心學習,早點回老家考公。”
王浩杰形容,自己聽到“回老家考公”時猶如雷擊,對于許多漂泊在一線城市的小鎮青年來說,這就像是在大海中憑借孤舟冒險的人遇到了一艘巨輪,“巨輪代表著安全、舒適,但登上它也代表著冒險生活的終結。”
從一線城市回到縣城,這種逆向選擇背后,人們動念的起因各有不同。
29歲的楊宇春此前在深圳工作,因離家太遠,他很早就有了回家的念頭。在家鄉得到一份穩定的“有編制”的工作是他當時立下的目標。他的選擇相對主動,準備也比較早。但在考公群里,他卻看到有人被動選擇的無奈。他還記得有一個群友說,自己因懷孕被公司辭退,打官司讓她筋疲力盡,而丈夫也因為行業不景氣收入驟降,兩個人眼看要支撐不住在深圳的花銷,因此才選擇回老家。但是兩個人的行業在偏遠地區的老家找不到崗位,最后丈夫在省會找了個與之前行業相關的下游產業工作,而她則出于穩定的考慮,選擇報考離省會不遠的一個縣級市的編制。
選擇回到縣城,對于大多數人意味著選定了今后發展的方向和生活的環境,這背后,親情起到了催化作用。
回到甘肅老家天水某縣城的馬鳴遠,在剛剛畢業時進入了上海一家有國資背景的數科公司。據馬鳴遠的描述,他收入不低,盡管遠遠達不到在上海置業安家的條件,但對于一個剛畢業的碩士生來說,這份工資收入讓他在上海這樣的城市實現了從未有過的物質滿足。“那時幾乎只會去貴價超市,我也報了很多興趣班,雖然工作很累,但上海好像有無數‘新鮮事物’等著我去發掘。”
不過,馬鳴遠卻對這樣的生活有著一絲“負罪感”,特別是老家父母對馬鳴遠情感狀態的關心,讓他覺得自己這個獨生子沒有按照父母的期待生活。“大城市的生活好似一種真空,讓我與傳統的家庭價值隔絕了。”馬鳴遠稱,許多在一線城市漂泊的小鎮青年,其家庭都有類似的畫像:家庭條件在縣城中處于中上,但父母思想較為保守,最大的期望就是孩子能守在身邊,找一個穩定的工作,結婚生子,在小地方過得體面、舒適,有一個順順當當的人生。“我好像始終被家中的一根線牽著,在大城市與小縣城之間左右搖擺。”
于是,在又一次被家里人催婚后,馬鳴遠選擇了回家,“回去找份工作,相親,結婚,生子……”這是馬鳴遠回到家鄉縣城前給自己規劃的未來。
與馬鳴遠的家庭類似,楊濤在老家縣林業局家屬院長大,父親在縣財政局工作,母親是中學老師。當初畢業時,他和父母都覺得可以先在外面闖一闖,在上海工作一段時間,看看情況再說。經過一段時間的體會,楊濤清醒地意識到扎根上海的難度,產生了回去的打算,而父母對于他想要回到老家考公的選擇都表示支持。
“我是獨生子,他們還是希望我能夠回來,一方面求個穩定,另一方面也希望我能夠離他們近一些。”促使他回家的一大原因是他的母親原本身體就欠佳,有一些呼吸系統的問題,新冠疫情后,病情有所加重。楊濤想回家減少父母的擔憂,也更方便照顧他們。
回縣城也要制定“戰術”
從英國畢業歸國的曹輝將縣城體制內崗位視為當代緊繃社會環境下的避難所。曹輝的家庭就業結構是浙江富裕縣城中的一個典型,家中有廠,有2個以上的小孩,一個人接手家族生意,一個人則進入體制內。對于曹輝的家長來說,孩子進入哪里的體制內并不重要,但比起離家較遠的大城市,自家所在的縣城是上上選。對此曹輝表示,自己回國前也收到過上海不少公司的offer,但在倫敦生活多年的曹輝只想“回家”。“考公算是‘回家’最暢通的渠道,因為縣里能找到的我感興趣的工作不多。”曹輝說。
除了直接考公回到縣城,一些人也采用了“迂回戰術”。去年,王浩杰在父母的“慫恿”下,將簡歷投遞給老家縣城的兩家國企,并成功被其中一家單位錄取。回到家鄉縣城后,王浩杰感覺收入雖然不高,但好像一下子沒了壓力,連閑暇時備考公務員都顯得輕松很多。談到自己備考公務員時,王浩杰笑稱,“好像每個從大城市回來的小鎮青年都是沖著體制內去的。一些人直接辭職回家備考,還有一些人就像我一樣,先在縣城找個比較清閑的工作,一邊上班一邊備考。”
“縣城體制并不是那么好進,首先專業限制就排除了一大部分人,其次縣城能提供的體制內崗位也有限。”楊宇春說,考公考編并適用于每個人。能直接通過考公考編回到縣城的也是“幸運的少數”。
去年,名校碩博生扎堆到浙江遂昌、江蘇阜寧、廣東和平等縣城體制內單位就業的現象引人關注。其中不少縣城基礎工作崗位的入圍人員均來自著名大學,且絕大多數為碩士、博士。對于一些有名校背景的人,想進入縣城體制內還有一個較為“方便”的渠道:人才引進。“我很早就想離開深圳,正好前幾年老家有人才引進政策,我的專業、學歷都符合,并且服務期也不長,就想著先回家工作再觀望。”在準備回家的第二年,楊宇春碰到了自己眼中的“機遇”。
“對于大城市的人才政策門檻來說,縣城更呈現‘求賢若渴’的姿態,雖然像前些年那樣優厚的人才引進政策在收縮,但在工作待遇本身還可以的情況下,認真工作幾年,最后多多少少也能拿到一些很實惠的人才優惠。對于很多想回家的人來說,這很有吸引力。”楊宇春介紹,由于各地人才政策優惠力度不一,人們會瞄準自己的“需求”去報名。“有些本身就計劃回縣城安頓的,往往會選擇有住房優惠政策的地區,而有些人只將回縣城體制內作為一個跳板,之后還是想回到省會或二線城市,這種往往會直接選擇有資金補貼政策的縣城。”
“雖然越來越多的人回縣城考公,但如果可以有更好的選擇,相信小縣城的公務員崗位并不會如此吃香。”據楊宇春觀察,之前所在的考公群中,有人對回到縣城后的生活期待頗高,也有人仿佛失去了生活目標才選擇回到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