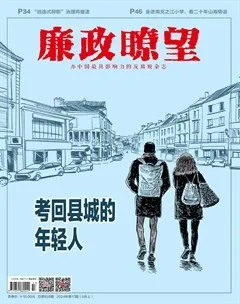金繕與鋦瓷:在裂縫里“種花”

兩方翠綠陶瓷獅子擺件昂首挺胸,細看之下才發現母獅上有“金絲”流淌而過,色澤與獅子金黃的發髻、身上的佛珠相得益彰。走進尹記鋦瓷堂,廉政瞭望·官察室記者便一眼望見這對向往來客人展示著自己“新生”的陶瓷獅子。
母獅擺件原本碎成了多片,是四川三臺縣非遺項目尹氏金繕技藝的傳承人尹啟榮用金繕技藝修復的。所謂金繕,“金”為黃金,“繕”為修復,是一種用天然大漆作為黏合劑和塑形劑修繕破損的器物,最后再“以金為衣”,用黃金裝飾破損處的傳統技藝,金繕的過程也是修繕師二次創作的過程。
而除了金繕,尹啟榮還擅長鋦瓷,這也是修復陶瓷的一種方式。尹啟榮的這門手藝來自爺爺,他的爺爺是一名鋦匠,鋦匠亦稱“錮爐匠”“鋦瓷匠”。
對于修繕師而言,他們當然也可以進行無痕修復,但金繕和鋦瓷的意義就在于“有痕”,修繕師擁抱殘缺,突出并重塑器物傷痕,這種二次創作模糊了破碎與圓滿的邊界,讓殘缺變成了另一種完美Q+66j0OGi60hoOv+Rq7nDMVLcAsku9k2BHL90bx3MZo=。
從補貴器到補成貴器
“國內的金繕近幾年才發展得愈加蓬勃。”梅琳玉是江西景德鎮藝術職業大學的一名老師,在景德鎮建立了自己的工作室,“我開始學金繕后發現,中國有關這方面的前輩、資料都相對較少。”他最初基本靠自學,但因為從小就接觸這方面的文化,上手很快,作品也日益精致。
尹啟榮在了解金繕歷史時發現,其實陶瓷修復手藝或許可以追溯到8000多年前,那時古人已經開始用大漆修復陶器了。“慢慢地,更多的修復方式出現。瓷器傳統裝飾手法‘描金’便與金繕相似。”
鋦瓷則是無可非議的中國非遺,在《清明上河圖》里,就有錮爐匠在街邊鋦瓷的場景,“沒有金剛鉆,別攬瓷器活”的俗語也源自鋦瓷手藝。“鋦瓷就是把打碎的瓷器用鋦釘(也稱鋦子)修復好。以前沒有電動工具,打孔鉆眼都需要用金剛鉆慢慢磨。有的瓷片特別薄,只能鉆三分之二。”尹啟榮告訴記者,每顆鋦釘都是手工制作,看起來或許大小一致,但其實每顆都略有不同,有的鋦釘還得雕刻花樣,用以搭配瓷器的樣式或圖案。

以前,瓷器相對珍貴,瓷器修補的需求較大,錮爐匠們便挑著錮爐挑子走街串巷,尹啟榮便是聽著爺爺吆喝“鋦盆、鋦碗、鋦大缸”長大的。“除了實用性的需求,一些顯貴、名士還會特意在完好的瓷器里裝上黃豆,倒入水撐裂,然后讓錮爐匠鋦出特別的模樣。”尹啟榮的朋友便曾將一個紫砂壺特地撐裂開又鋦好,上面以數顆鋦釘固定,再點綴上花釘、銅錢釘各一顆。
“現在的瓷器沒那么金貴,修繕費用卻遠大于器物價格,到我父親那一輩鋦瓷便有些落寞了。”尹啟榮不希望傳承的技藝消失,“所以我四處拜師,學習了多種修繕技藝,例如金繕,以融會貫通。”經過他的努力,今年7月,尹氏金繕技藝被列入三臺縣第十批縣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金繕和鋦瓷這兩種修復方式可以互相搭配,但不能互相替代。前者的優勢在于它的可逆性,后者在某些情況下會更加牢固。”
尹啟榮現在修復的多是極具情感價值的器物,他會更注重美感與實用性的兼具。他向記者展示了一個以前鋦的碗,上面的鋦釘較大,僅是順著紋路將殘缺部分補好,而后面修繕的一個杯子,鋦釘更小粒,排列更加細密整齊。
“俗話說‘瓷爛如泥’,我們所做的便是通過修復,賦予‘爛瓷’第二次生命。”尹啟榮說,一些器物經過修繕師修復后身價倍增。
好“事”多“磨”
學習金繕、鋦瓷并非一件易事,是否對大漆過敏、能否忍受這種過敏是進入這個行當的第一道門檻。
“生漆(大漆)是非常珍貴的,俗話說‘百里、千刀、一斤漆’。”尹啟榮介紹道,漆文化本身也是一種光輝燦爛的文化。生漆在干燥固化后綠色環保,無毒無副作用,且具有耐水、耐熱、耐酸、耐堿、耐磨等特點,是理想的天然涂料,但其中卻含有一種會導致過敏的特殊物質——漆酶。大漆導致的過敏,也被稱作“中漆毒”。
梅琳玉最初接觸大漆時并未出現過敏反應。誰知漆毒會潛伏,半個月過去,他的胳膊上突然冒出密密麻麻的皰疹。“我還算好的,有的人只要一聞到大漆的味道就會過敏,我身邊一些想學金繕的人因此被‘勸退’。”
但一些自學的修繕師初學時并不知道漆酶的存在,沒有做防護,因此過敏癥狀往往會更加嚴重。例如接觸大漆之后,臉、手、腳都起了疹子,骨頭縫里都癢,往往需要長達半個月恢復時間,且身上仍會留下一些痕跡。
有的修繕師還會在修復中突然“中招”,漆毒導致他們全身潰爛,甚至無法下地走路。而且由于漆毒不會因經歷一次之后就免疫,修繕師仍會時常出現過敏的情況,只是相對沒有最初那么嚴重。但隨著修復的器物增加,修繕師逐漸習慣了忍受過敏,甚至主動摘下手套,因為他們認為裸手修繕更有觸感,還能用指紋進行拋光。
而在經歷了漆毒的磋磨后,修繕師還需要一遍又一遍地打磨瓷器,以及日復一日地“打磨”自己的眼光。
“金繕這門技藝入門不算困難,但修復水平的高下之分,要看修繕師的審美。”梅琳玉認為,對于修繕師來說,每一件瓷器都是獨一無二的,破碎之處更是完全不一樣,每一次的修復都是一個新挑戰。因此,在真正開始修復前,他會先觀察那些器物,了解器物本身的材質、顏色、花紋,它是怎么破碎的,是需要補缺還是只需要粘合……“修復不能脫離器物本身,它不是從0到1的過程,而是從1開始,所以要‘因勢利導’,根據器物本身的情況選擇是金繕還是鋦瓷,如何設計、操作才能與原物契合。”
對于修繕師而言,他們經常需要到各地去參觀展覽,“養一養自己的眼睛”,不斷提高審美。因為金繕需要師古而不泥古,要站在年輕人的角度不斷創新,做出更年輕、更新穎有趣的設計。“在修復過程中,和物主進行交流、思考如何設計往往是耗時最久的一個步驟。”梅琳玉說。

開始修復之后,修繕師需要層層上漆,每上一層都要等待大漆自然陰干,如果天氣不好,等待時間也會變長。大漆凝結后,就要開始打磨。打磨對力道的要求很高,力度太大會破壞裂痕中間的漆面,力度太小又沒有作用。上漆、陰干、打磨,每修復一件器物,這些程序至少要重復十幾遍,耗時數月,之后再用金粉、金箔等進行最后的修飾,然后又是一輪打磨。梅琳玉介紹完后笑道,“好‘事’多‘磨’嘛。”這,說的是磨物件,也是修繕師經歷的身心磋磨。
修復的是物,也是情
最初入行時,許多修繕師常會認為他們修復的會是名貴的古董、文物,可實際上,他們修復了許多年輕人的“奇怪”器物,vjxhch2zejRZsntJMpvJWw==比如陶瓷bjd(Ball-jointedDoll,即球型關節人偶)、香爐、甲蟲擺件……梅琳玉也修復過許多“奇怪”的東西,他還幫一個朋友上門修復過瓷桌。
修繕師們發現,金繕和鋦瓷惜物之心的背后是思人之情,許多人支付的修復費用時常大于器物本身價值,他們舍不得的往往是器物背后所代表的情感紐帶。梅琳玉曾經幫一位任期已滿,即將離華的駐華大使修復過一個咖啡杯。“由于職業的特殊性,他們時常需要搬家,他一直帶著的這個咖啡杯并不算名貴,但因為是祖母留下的,他格外珍視。”
一名正在學習中的修繕師跟記者分享,他曾經修復過一個茶杯,茶杯原價不過幾十元,要修復的話費用卻上千。這個茶杯是物主的母親留下的。母親去世前時常和他一起坐在院子里煮茶,這個茶杯在那時就出現了一個缺口,但母親偏偏就喜歡用它喝茶。母親去世后他在一次拿取時不小心將杯子摔碎了,他找到修繕師修復,卻要求保留原來的缺口。修繕師感嘆,這保留的是缺口,也是回憶。
尹啟榮經常淘一些破碎的瓷器進行修復,這些瓷器本身或許并不珍貴,甚至已經被“淘汰”,但經過一番修復,它們往往會煥發新生。他還曾幫成都某老年學院鋦過一個豆青釉青花堆白大瓶,用作該校教學鋦瓷技藝的一個參考教具。
對于修繕師而言,在修復過程中,他們聽見過太多故事,修補好了無數條“紐帶”。他們還在不斷探索,尹啟榮在研究金繕、鋦瓷等有痕修復的同時,還在研究讓器物聲音不受影響的無痕修復;梅琳玉只接熟悉的物主的修復訂單,想要將更多精力放在設計上……
金繕與鋦瓷中融有修繕師的心力,當器物漸漸“圓滿”,看到物主們的欣慰,他們“在裂縫里種出的花”便擁有了特別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