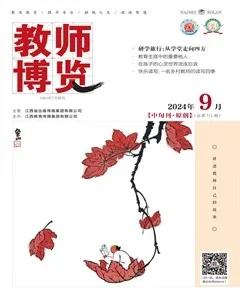重看《十六歲的花季》偶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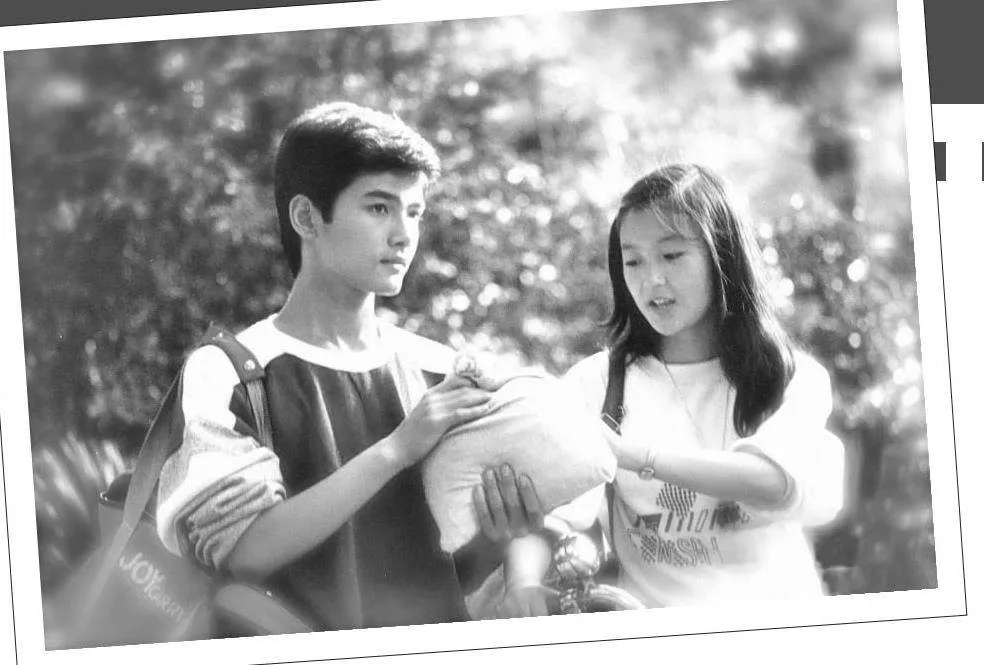
前段時間,我在網上重看了12集電視劇《十六歲的花季》。1990年,此劇一經播出就風靡一時,長期“霸屏”,更號稱國內第一部青春偶像劇。在很多“70后”乃至“80后”心目中,這部《十六歲的花季》是一代人青春期的難忘記憶。我也不例外,當年初看此劇,我還是一個初中生,年齡不到16歲,卻與電視熒幕上的這群“16歲”有著深深的共鳴。30多年后的這次偶然重看,我卻又似乎收獲了些許新的感觸。
一、關于上海
《十六歲的花季》講述的是一所上海市重點中學的師生故事,也可以說,這部劇為我們展示了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上海生活。劇中的上海已然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卻又處在轟轟烈烈的浦東開發(fā)開放之前,商品經濟(市場經濟)意識顯然已經深深影響著這座本就是中國最富有商業(yè)氣息的大都市。然而,又誠如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所言,在高歌猛進的經濟特區(qū)建設大潮里,我們卻曾經一度遺忘了上海。我想,從某種意義上說,《十六歲的花季》當年講述的恰恰就是這樣一個被遺忘的上海。
在這個被遺忘的上海,無論是高級知識分子如歐陽嚴嚴的爸爸,還是手上有點副食品審批權力的國企干部如韓小樂的爸爸,或是充滿藝術創(chuàng)新精神的設計大師如白雪的爸爸,都還是繼續(xù)在石庫門的大雜院里“螺螄殼里做道場”,在充滿市井與傳統(tǒng)氣息的住房環(huán)境里上演著每一幕生活與工作的“日常”。同樣,一所市級重點中學的校長還是需要為辦學經費尤其是教職工的福利待遇犯難發(fā)愁。高一(2)班班主任童老師的男友陳老師積極為學校創(chuàng)收,也還是得不到大家的理解,甚至連自己的女友也多有埋怨。而“16歲”的他們還是能夠在周末回家的時候,騎上各自的自行車自由愜意地穿行在上海的大街小巷,沒有太多機動車的打擾,可以在騎行的途中盡情釋放自己的快樂與秘密。
當然,暫時被遺忘的上海畢竟還是上海。白雪家的鄰居阿寶哥正與他的朋友“八國聯(lián)軍”忙活著出國,歐陽嚴嚴的媽媽縱然在逼仄狹小的家里也要漫不經心地喝上一杯咖啡,白雪與歐陽嚴嚴在騎車回家的途中時常互請一瓶在當時尚屬稀罕的可口可樂或雪碧,而白雪的父親也能與自己的碩士研究生兼同事羅蘭在交響樂劇場里或者充滿小資情調的餐廳里互訴著成年人的心事,陳非兒與袁野兩個人能否順利考取上海的大學而成為真正的上海人依舊是他倆曾經的上海人父母“支邊新疆”最掛懷的心愿。
于是,《十六歲的花季》所講述的上海讓我們再次看到了市場經濟之前的上海——一個蠢蠢欲動的上海,一個萌生著新的生活熱望的上海,一個在昔日輝煌的傳統(tǒng)與展望可以觸摸的未來之間搖擺過渡的上海。這似乎也是處在改革開放青春期的上海,這座成長中的城市,在回望過去的復雜心情里注入了未來必然迎接無限可能的澎湃激情。每當我行走在上海那些永不拓寬的馬路上時,不知為何,我有時總會想起“16歲”的他們曾經灑下的一路歡笑。
二、關于家長
初看《十六歲的花季》時,作為初中生的我完全被代入了白雪、歐陽嚴嚴、韓小樂、彭瑜、何大門等中學生的世界里。說真的,那個時候這些“16歲”們的家長所說的話、所做的事,我基本上都不大搞得懂。而30多年后的重看,卻很有意思,因為我發(fā)現(xiàn)我再也無法把自己代入到“16歲”的世界里,反而對那些家長們的所思所言所行清晰無比地產生了極大的共鳴。從這個意義上說,《十六歲的花季》不僅是青春片,它耐看,也經得起看。
家長的幸福總是相似的,無非是自己的孩子成績好。家長們各有各的對孩子們的期望,而對成績的期待是高度一致的。2012193f3750e02daf993cf0a11bc68430年來,這一點似乎也從未有真正的改變。當初的我不理解也不認同這種高度一致的期待,而現(xiàn)在作為家長的我,盡管不完全認同但更多了分理解與接受。家長總會把自己的期望當作孩子的全部義務與責任,這當然會造成青春期的煩躁與壓力。但是在一個機會本就少得驚人的社會環(huán)境里,孩子的壓力也總歸是家長的壓力。
《十六歲的花季》其實已經處理得很好了,比之于如今某些“高考劇”和“家庭劇”里的高昂代價與雞飛狗跳,當年的“16歲”們也算得上是從容淡定、多姿多彩。那些充斥著家長的欲望與期望的教培補習、金牌機構、成龍成鳳以及永遠不輸在起跑線的“教育風景”尚未完全上演。家長們還能夠少問少介入,還能有幾分屬于自己和孩子共有的自由與寬容。從某種意義上說,《十六歲的花季》不僅描繪的是“16歲”們的精神世界,也探詢到了家長們的內心世界。孩子在成長,家長其實也在成長;孩子有孩子的困惑,家長有家長的困擾。重看此劇,我深感懵懂與明理、成熟與幼稚、堅強與挫折不獨屬于“16歲”們,也屬于他們的爸爸媽媽們。面對復雜世事,面對無窮誘惑,面對大千世界,眼睛里的憧憬會因為誘惑而變得狡黠,昔日的理想會因為太多的不確定而變得像輕浮的絨毛隨風飄揚。回頭看一看,不過只是希望在自己的心靈世界里,建立一個感情的棲息地,不必在乎別人的眼神,也不需要在意別人的評頭論足。“16歲”們如是,家長們亦如是。
三、關于16歲
“十六歲的花,只開一季。”當年這句席慕蓉的詩,經由《十六歲的花季》反復傳播,成為一代人最為深沉、略有傷感的青春期金句。今日重看此劇,當年這些“16歲”們說出的很多金句有些已經明顯過時,有些依舊頗有分量。縱然是那些有幾分過時的臺詞,也足以代表那時那刻那一代人青春的自由與獨立。這很可能就是30多年前此劇能夠迅速捕獲人心的力量所在。
每一代人都經歷過16歲。誰人沒有過青春,誰人又有過青春?關于“16歲”,我想問的是,今天為什么幾乎再也沒有關于現(xiàn)在的“16歲”的《十六歲的花季》呢?不能說完全沒有關于“16歲”的故事,但確實沒有那么純粹的“16歲”的故事。當下的“16歲”們的故事,也一次次掀起過青春敘事的活力張揚,有時尚,也有傳統(tǒng);有叛逆,也有皈依;有傷害,也有反思;有自我,也有承擔。青春只有提問,沒有答案。必須承認,這些“16歲”們的故事在故事手法和視聽包裝上新銳時尚,其中也不乏這個時代的“16歲”們身上所迸發(fā)的令人艷羨的對于自由和個性的珍視與揮灑。但是,稍對當下的中國社會與時代現(xiàn)狀有所敏感的人,都不能不對電視劇所渲染的“北京三環(huán)內”或“上海南京路”的青春話語,感到切膚的隔膜和恍如隔世般的虛空感。這種奮斗、這種青春實在有點奢侈,實在有點輕飄,實在有點脫離典型環(huán)境中的典型人物。這種過于理想化的戲劇張力,實在也擔不起所謂“青春的奮斗”與“奮斗的青春”。這就是我說的不夠純粹。
我甚至想,可不可以講述一個簡單而溫暖的新時代的“花季故事”。它可能缺少個性,卻很真誠翔實,讓記憶重回到充滿著成長幸福與煩惱的中學時光,能夠讓我們又記起那些一道走過青春的同學以及許多只能重現(xiàn)于個體記憶之中的故事化的往事。這樣的少年詩篇,也許能夠讓當下的“16歲”們在另一個30年后,不經意地重新找回“我的失敗”與“我的成功”,給之以鼓舞,給之以回味。
(作者單位:南昌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