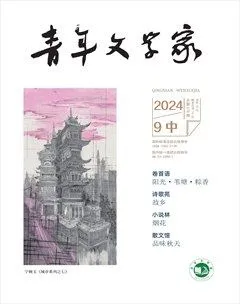生 逝
花開花落,我們來到這里,或離開這里。這里沒有我們的永恒,面對蒼穹,它們的永恒顯得我們的生命是如此短暫。此生,唯一可以驕傲的,只有無盡的思考。
祖父的突然離世,讓我們始料未及。我既沒有勇氣接受,也沒有資格面對。祖父是在醫院里去世的,也許一切本應該平凡地過著,祖父的病情并不嚴重,他卻選擇從樓上躍下。我不知道祖父在生命的最后想到了什么,又如何理解了這生與死的真諦。生離死別,我卻連祖父的最后一面也未見得,十五歲少年的我,只能在懺悔中熬過。祖父去世前的那個暑假,我每日每夜坐在電腦旁,玩著不知所謂的游戲,一局又一局,一盤又一盤,以致去醫院看望祖父都沒有做到。在祖父生命的終點,我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我憎恨自己,不愿去坦蕩地面對這些發生的事情。我一直覺得自己是個罪人,祖父的去世是因為我的漠不關心,縱然親人說祖父在走之前的日子常常說胃痛、肚子痛,但我還是自責地認為祖父真正想說的是對我的心痛。
一個明明還應健在的生命卻如此簡單地逝去,簡單到只是從樓上到樓下絕望地一躍。葬禮前,親人們哭著;葬禮時,面對那明明存在卻沒有反應的身體他們再次失聲痛哭。這最后一面,讓父親、讓姑姑哭得那么無力,明明他們那么努力補救,卻還是無法挽回。我不敢出聲,唯有讓眼淚悄悄滑落,隨后自私地封存了這些記憶,又自私地封閉了自己的情感。葬禮后,雖然悲傷未退,但我們仍要投入新的生活,因為我們還活著,因為我們還要奮斗,因為我們還不能對生活說永別。世間便是這般無情,不管少了誰它都一樣轉過。后來,總是憶起祖父對我說大道理講故事的那些時刻,當初滿心抵觸,如今卻覺那時珍重無比,而祖父的那句“百善孝為先”深深地鞭撻著我的靈魂,我沒有為祖父帶來太多的笑容,我的善又在哪里?一切本應在時間的作用下銹蝕沉底,卻總會有些強耐腐蝕的不堪大行其道,游于時間長河;又總會有些新的存在從支流匯入,這一刻加入我的命運,下一刻離開我的命運。
老家的鄰居,我不知道他們具體的名字,只記得一直稱呼明哥、明嫂。明哥應是六十多歲了,聽說從小就喜歡玩樂,現在也經常打牌,即便這般平凡、這般碌碌無為,卻也這么生活了幾十年,嘗遍生活的酸甜苦辣。雖平凡,卻不意味著無禍。明嫂患了大病,經過治療,聽說后來在家中調養。我也有很長一段時間未曾見過明嫂。直至一兩年后,才見到明嫂再次出現,卻是坐在輪椅上,就那樣在門口靜靜地坐著,明哥守在旁邊。每次從家里出去,常常可以看到他們,每次我簡單地微笑示意,明嫂卻沒有表情、沒有言語,印象中她再也沒有動過,也許,是她不想動吧。我莫名感到一種悲傷,一種對生命的悲傷。對明嫂而言,這種生活的幸福和意義又存在于哪里?我不知道,如果我變成這個樣子,我能用什么理由來接受,又有誰會記得我、陪伴我?
后來一次在家附近滑滑板時,明哥也推著明嫂來到這條小道上,明哥停了下來為明嫂調整輪椅,我卻慶幸自己還健康地活著,可以玩所有感興趣的玩具,做所有能做的運動,又對明嫂感到一種悲哀,哀嘆她生命的坎坷。無形中,我的內心翻涌起一種恐慌的感覺,慌張地拿起滑板在明嫂呆滯的目光下向家里跑去,我不知道我為什么會慌張,直至此時,我也無法理解那一刻復雜的情緒。
漸漸地,明哥明嫂他們的生活日復一日,我的生活也日復一日,就像兩條射線,在一個點上交叉后,卻再不相交。這世上又有多少人與我一般,與明哥明嫂一般,與我的祖父一般,或接受或拒絕著生活,我們都在奮斗著什么?又為什么而奮斗?也許只是簡單地活下去,也許只是想要幸福,也許又是為那名垂青史。
聽說人們臨死時可能有一段回光返照的時間,在那時可看破生命的意義,因而放下一切,獲得最終的幸福,不知祖父是否完成了他的人生?如今,要走的人平靜地走了,擺脫了這個喧嘩的世界;而未走的人們仍在忙碌著,送別離開的,迎接新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