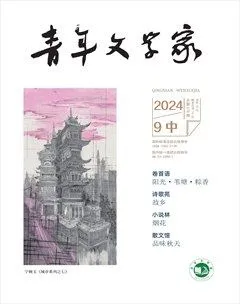黃連樹下彈琴
“黃連樹下彈琴,苦中取樂”,小時候,母親時常這樣教育我。苦生苦長,樂觀堅強,已成為深刻記憶,成為溫馨回憶!
尋覓野菜
盼望著,盼望著,春天來了!我們這些缺衣少食的山孩子,終于可以不用縮手縮腳,身子蜷成樹疙瘩,手腫成小饅頭,臉皴成樺樹皮,終于可以像南來的燕子,漫山遍野地翻飛,尋覓各種野菜,幫襯父母度過青黃不接的日子。
聽,“三月三兒,抽毛芽兒,結繩繩兒,卷餅餅兒,給你嫂子當枕頭兒”,山間小道上到處飛揚著我們這幫無邪兒童的歡聲笑語,盡管我們臉上滿是饑餓的菜色!
看,薺菜、灰灰菜、野韭菜、野小蒜……這些隱沒在雜草叢中的各種山野菜都是發光體,引得一群群叔侄、姨甥們一陣哄搶,它們都是各家能夠填飽干癟胃囊的稀罕物啊!
高小畢業的母親,要比周圍的親友們機智,好吃的熟悉的野菜太少,難填飽肚皮,她就教我順著山澗溝渠尋覓飯蒿和桑葉。
怕我誤采飯蒿,食后中毒,她就教我學會一看二聞。
她說,飯蒿的背面是乳白色的,其他野蒿的背面是青黑色的;飯蒿有一股清香味,野蒿是水草味的。桑葉好辨認,盡量采嫩葉就行。
飯蒿采回來后,用開水一焯,再用涼水漂洗幾遍,切碎加鹽攪一點兒玉米面,煮成稀糊糊,味道不比薺菜糊差。
桑葉洗凈、焯水、切碎,放進開水鍋,倒入一點兒石磨生黃豆漿,煮熟,做成懶豆腐,吃了很耐餓。現在大餐館里有時也有懶豆腐,用精美蔬菜做成,可我再也吃不出童年的清香味道了。
長大后,不免感嘆:“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畫,心里初戀的童年……”
助力搶夏
夏天,天高云也長。
“豌豆算割,豌豆算割……”“麥黃快割,麥黃快割……”房前房后布谷鳥清脆的催叫聲,催醒我們準備幫大人“搶夏”了。
父母天不亮就下地了,我和弟弟趕緊起來,招呼妹妹們起床做事。掃地、放雞、喂豬、做飯、送飯,這些必修課,必須趕在上午八點上學前完成;中午父母不歇晌,我們姊妹五個陸續從學校趕回家,燒茶、做飯,還要給父母送到地頭,還要喂豬喂雞;下午放學后,時間長,活路更多。第二天的口糧要是沒有了,來不及背糧到小磨坊加工,我們還得自己用小石磨推“麥辣子”(小麥磨碎,不去皮、不去麩),還得削好一大盆子的洋芋(細糧少,全靠摻洋芋充饑),還得上山打豬草,還得洗父母滿是汗漬的臟衣服……
我們家人多活兒多,忙不過來怎么辦?抱團呀!我常常邀請堂弟堂妹們把削洋芋皮之類的活兒都拿到我家來做。我們先幫她們,她們再幫我們,比著干,賽著做,效率自然高多了。說實話,還是占了堂弟堂妹不少便宜,畢竟他們家務活兒的總量少些。
“婦姑荷簞食,童稚攜壺漿,相隨餉田去,丁壯在南岡。”當我讀到白居易的《觀刈麥》時,情不自禁地改為:“童稚荷簞食、攜壺漿,相隨餉田去,父母在搶夏!”
爬樹采藥
別看我們年紀小,卻多是上樹的高手。深秋了,落盡了葉子的樹梢上還有幾個誘人的烘柿子。機靈的三妹不用竹竿,而是脫掉鞋子,往雙手掌上吐些唾沫,身子一縱,噌噌幾下就爬到樹頂上,任憑樹枝像秋千一樣蕩來蕩去,她用雙腳緊緊勾住樹枝,雙手輕盈地摘下柿子放在背上的小背簍里,刺溜刺溜地溜下地來。我們驚叫著,歡呼著,如一群嘻嘻哈哈的小畫眉。
我們還是采藥的“犟人”。父母為養家糊口,“面朝黃土背朝天”地在貧瘠的山地上耕種。想上學,只能自己掙學費!我們每個周末都會在各個山梁上采藥。即使一天只能采到一點點柴胡、連翹、五味子,能挖到一兩斤黃姜,我們也不會放棄,我們相信愚公移山,我們相信人定勝天。
上山騎牛
隆冬時節,我們一邊上學,一邊放牛,一邊割牛草,一邊撿牛糞。牛兒是我們最好的玩伴,到了平曠一些的山頂,吃飽了的它們便高興地弓下前腿,讓我們依次爬上牛背,它們甩開尾巴馱著我們來來回回在山頂游走。郭老曾在《天上的街市》中暢想:“那隔著河的牛郎織女,定能夠騎著牛兒來往。”敢情是受了這一啟發?
四季更迭,時節如流,我們就這樣度過了有憂有慮、苦樂相伴的童年。奇怪,再回首窮困童年散落在樹林草叢間的那些小碎片,不覺辛酸,不覺愁苦。原來“愁”是“離人心上秋”!那時的我們,祖輩健在,父母年輕,姊妹無邪,雖物質貧困,但親情豐厚,關愛富足!最最關鍵的是,母親教會我們:即使坐在黃連樹下,也要堅持彈琴唱歌,苦中取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