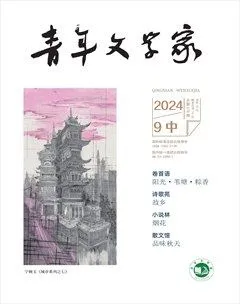從文學到圖像:《黑駿馬》跨媒介改編探析

文學到圖像的轉換是研究經典文學的重要議題。基于不同媒介特性和傳播效果,文學改編作品之間也存在互動的情況。本文將分析《黑駿馬》的連環畫和電影改編,旨在探討跨媒介下圖像化對文學性的影響及文本間互動。
一、從文學到圖像
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中,跨媒介改編普遍存在,我們應關注文學、廣播、戲劇、連環畫、電影等媒介間的相互關系。武新軍的《中國當代文學跨媒介傳播史料整理問題》強調了影響文學作品的外部因素包括政治、文藝政策、經濟、產業和技術條件。跨媒介傳播的文本史料、不同創作主體的跨界互動,以及傳播效果與范圍的史料也需考慮。研究《黑駿馬》跨媒介改編時,本文以連環畫和電影改編為例,探討文字到圖像的轉化中文本互滲問題。改編者理解各異,表達多樣,媒介間的“合力”影響文學地位。文學作品圖像化是媒介時代趨勢,當代文學媒介轉換現象值得研究。
二、小說《黑駿馬》的跨媒介改編文本
趙憲章的《文學圖像論》認為,文學與世界圖像關系在于“語象”展示世界,而非概念說明。同時,預想文本通過視覺圖像外化,如文字造型、詩意畫、插圖、連環畫和影像改編等均為其延宕結果。《黑駿馬》自出版以來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文學文本陸續被改編為連環畫、話劇、電影等。這種跨媒介改編文本之間相互作用,形成不同的傳播效應。
(一)1984年連環畫改編
連環畫起源于20世紀初葉的上海,它是根據文學作品改編的,有簡明文字腳本和生動畫幅。自“五四運動”以來,許多經典作品被改編成連環畫,這與現代中國市場環境緊密相關。連環畫更大眾化、通俗易懂,適應市場并在底層群眾中廣泛流傳。文學作品被改編成連環畫,體現了從文字到圖像的轉換特征。《黑駿馬》是1984年刊載于《連環畫報》的連環畫,獲1986年全國第三屆連環畫評獎繪畫創作二等獎,由魏小明繪制,小晴改編。改編后的連環畫賦予小說新活力,畫家技巧精湛地塑造小說中的人物,使人物形象更加飽滿,更生動地傳達了作者的情感和思想。在《黑駿馬》的啟發下,張承志描繪了草原文化的蒼涼與沉郁,通過白音寶力格的成長,講述了其與索米婭的愛情悲劇。索米婭是這部小說的核心人物,其復雜性和多面性源于草原文明的束縛與現實世界的妥協。連環畫通過細膩描繪人物神態,展現了索米婭在不同時期的復雜情感和處境。索米婭的內心壓抑與真實情感,雖未能直接表達,卻通過其言行流露出來,無論是童年的純真、對愛情的依戀,還是成年后對家庭的責任,都生動地呈現在讀者面前。
童年時期的索米婭毫無保留地展現出她純真活潑的天性和生命最真實的狀態,她和孩童白音寶力格一起生活玩耍,親切地喊他“巴帕”,她“閃著黑黑的眼睛盯著我”。畫者對索米婭的神態進行的特寫可以看出這時的索米婭還保留著最原始、最真實的內心,還沒有受到草原的道德與精神枷鎖的束縛。索米婭期待的眼神與黑駿馬鋼嘎·哈拉同框,體現了畫家對兩者關系的精妙處理,呼應了原作中索米婭對白音寶力格的深情。成年后,白音寶力格與索米婭發現彼此的變化,但羞澀使他們保持距離。直到送白音寶力格去學習的夜晚,索米婭在顛簸中緊緊依偎在白音寶力格懷里,淚水濕透了他的衣服。那個夜晚,索米婭不再克制,展現出最真摯的依戀。成年的索米婭面容清秀,秀發飄逸,嘴角含笑,與白音寶力格緊緊相擁,神情中流露出深深的眷戀。畫家在圖像化過程中突出了索米婭的情感,塑造了一個純真未泯的少女形象。
索米婭經歷風雨后,與白發額吉一樣堅韌善良,胸懷如草原般寬廣。她承載著草原文化,珍視并平等對待生命。面對生活苦難,索米婭為保護孩子,對白音寶力格尖叫,甚至咬了他一口。此時她失去愛意,眉頭緊鎖,眼中充滿恐懼與乞求,左手護胸,這一細微動作象征性地割斷了她與白音寶力格的情緣。畫者未給她戴上頭巾,展現了成熟女性的形象。面對苦難,她倔強沉默,無怨承受。此時的索米婭也是一位“額吉”,“被額吉高尚的道德和她所遵循的‘草原的習性和它的自然法律’所規范與監視”(沈鳳蛟《〈黑駿馬〉中索米婭形象新論》)。白音寶力格與索米婭重逢,歷經磨難的索米婭已是四個孩子的母親,草原文明的精神世界被喚醒。她所接受的草原文明是“如同草原一般廣闊的、博大的、無限包容、無限珍視生命的一種草原母性精神”(蒲華睿《對〈黑駿馬〉中索米婭的身體解讀》)。這里索米婭被草原環抱,象征著她靈魂深處融入的草原文明。她與白音寶力格不同,她始終堅守著傳統。最后的索米婭真摯柔和,在白音寶力格離別時喊出“巴帕”,并愿意留在草原撫養孩子。魏小明筆下的她,散發母性光輝,泛紅的臉頰、麻花辮與寬大衣袍,完美詮釋了地道的草原女性形象。
作家張承志以他獨特的草原書寫刻畫人物內心,將人物不同時期的成長與變化一一剖析在讀者面前,但文學作品只能通過文字來描摹人物形象,這些藝術形象需要讀者去想象建構,圖像化的文學形象不是唯一的,因此畫者的繪畫有一定的自由度。魏小明的畫幅同樣注重人物精神世界的變化對于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性,因此連環畫中所體現的對人物神態動作細膩的刻畫補充了讀者的想象空間,使讀者對文學文本的想象更加具體化。
(二)1995年電影改編
電影作為視聽媒介,通過鏡頭和蒙太奇手法展現了現實世界。中國電影早期以古代文學為靈感,發展后將文學融入電影制作,用鏡頭語言替代文字,連接視聽與文字。1995年,謝飛導演將《黑駿馬》改編為電影,由張承志編劇,騰格爾等出演,促進了文藝傳播。影片獲得多個獎項。文學與藝術互融,使電影與原著小說相得益彰,形成跨媒介傳播力。《黑駿馬》篇幅適中,適合電影改編。張承志在擔任編劇后保留了小說的思想性,并通過電影形式表達了小說背后所蘊含的情感。電影改編除了關注視覺藝術,還需重視聲音這一獨立聽覺藝術形式。
電影相對原著小說,情節進行了改動,視角也發生了變化。首先,電影對《黑駿馬》的敘事結構進行了調整。原小說風格散漫,以第一人稱敘述回憶;影片采用逆時間線敘事,簡化情節為兩段式結構,同時強化了象征和隱喻。原小說中的惡棍希拉在電影中變得健壯風趣,深受草原女子喜愛,與索米婭有著情感糾葛,并導致索米婭懷孕。電影減少了戲劇性,更深入地探討了人類生存本性的主題。其次,電影文本在保留第一人稱自述的同時,增加了女性視角敘述,特別是通過強化額吉形象。白音寶力格的名字由額吉所起,象征草原哺育與生命重生,體現母性情結。他重返草原,發現索米婭已經成為四個孩子的母親,形象與額吉重疊,隱喻了草原女性的命運和精神。敘事視角的轉變使騎手與妹妹成為敘事主體。
謝飛導演在《黑駿馬》中運用詩意鏡頭語言,繼承并轉化了小說的詩化敘事。電影結合聲音、剪輯與影像,具象化了草原之美,強化了自然生態的氣息。導演用空鏡頭展現草原風光,起抒情作用,控制敘事節奏,烘托情感表達。在白音寶力格離開草原的那個夜晚,暗夜里,白音寶力格漸行漸遠的空鏡,烘托深沉夜色,凸顯其沉重的心情,渲染了離別之情,增添了悲劇色彩。謝飛導演運用空鏡抒情表意,使鏡頭語言更加詩意化,深化了蒙古族的文化主題。
從語言藝術到視聽藝術。電影跨媒介改編需注重聽覺藝術效果,區別于其他圖像媒介。在《黑駿馬》中,聲音藝術主導敘事節奏和審美范式,古歌《鋼嘎·哈拉》貫穿全片,隱喻人物命運的悲劇性。白音寶力格重返草原尋找往日愛人索米婭,卻得知她已“嫁到了山外—那遙遠的地方”,正如額吉歌謠里唱的那樣,索米婭的命運似乎在冥冥之中被這古歌指引著。索米婭遠嫁后的生活境遇正如歌謠里所唱,在白音寶力格離開后她默默承受了命運帶給她的所有苦難。影片中的聽覺藝術并不是一個獨立的存在,更多地推動故事情節的發展,是使故事更加完整的重要元素。電影對《鋼嘎·哈拉》的配樂處理精巧,聲線變化象征主人公的情感轉變,引領觀眾的情感起伏。小說雖提及該歌,但電影以聲音媒介直觀呈現,使觀眾直觀感受其魅力。
三、小說-連環畫-電影的互動關系
從跨媒介的視野來看,以“小說-連環畫-電影”為核心形成的文本鏈建構了當代小說經典化的路徑。這種跨媒介文化生產機制遍布整個中國文學史,當一部小說獲得社會的強烈反響后,連環畫作為當時最為活躍的大眾媒介,迅速引發同名連環畫的改編,然后隨著影像技術的發展,再將其改編為電影。這種橫跨文學、美術和電影三大藝術領域的文本鏈在生產和傳播的過程中存在著互動關系。
(一)對作品文學性的轉化與延續
跨媒介改編以文學作品為基礎,影響連環畫腳本和電影主題。在圖像文本依賴文學改編時,小說的文學性可能消解、轉化或延續。文學性的界定分為狹義和廣義。狹義的“文學性”是指一種文學現象,廣義的“文學性”是指“滲透在社會生活方方面面并在根本上支配著后現代社會生活運轉的話語機制”(姚文放《“文學性”問題與文學本質再認識—以兩種“文學性”為例》)。隨著文學作品的跨媒介傳播,經典小說被改編為連環畫、電影、戲劇、影視劇等多種藝術形式,文學的存在方式和傳播途徑不斷革新,文字不再是其唯一的生產和傳播方式,在文字到圖像的發展過程中,傳統文學作品的文學性是否逐漸被消解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圖文結合的連環畫作為中國20世紀以來最受大眾喜聞樂見的傳播媒介,自問世以來便飽受爭議,魯迅、茅盾等多位學者先后對連環畫現象發表自己的觀點。文學的圖像化雖然更容易迎合受眾市場,擴大傳播范圍,但應警惕在連環畫改編過程中,為迎合部分受眾的娛樂性需求而對作品文學性的消解。“五四運動”時期,《連環畫報》等平臺積極推動了連環畫的發展,它們以傳統文學為素材來源,共同促進了市場的繁榮。革命小說如《青春之歌》被改編為連環畫,為原小說注入了新的活力,是文學性的轉化與延續。
自電影誕生之時,有關文學與電影的激烈討論就從未停止,“娛樂至死”等觀點的提出體現了電子時代大眾傳播媒介對人的消極影響,以圖像和聲音為媒介手段的電影無疑是對以文字為媒介的傳統文學的替代,文學逐漸被“邊緣化”。但是,正如童慶炳在《文學獨特審美場域與文學人口—與文學終結論者對話》中所說,“文學是人類情感的表現形式,那么只要人類的情感還需要表現、舒泄,那么文學這種藝術形式就仍然能夠生存下去”。文學與電影共生互融,改編需保留并傳承文學性,要求編劇深入理解作品內核并注入個人見解。改編并非簡單地照搬,而是導演將編劇的情感共鳴創造性地轉換為電影語言,從而使文學性得以在電影中得到生動的表達。
(二)參與文學作品經典化的過程
從圖像媒介的傳播特點來看,傳播范圍廣泛、傳播內容豐富、傳播途徑多樣,多種藝術形式擴大了傳播格局,因此文學的跨媒介傳播能夠激發其經典化路徑新的活力。20世紀80年代以來,“尋根”思潮在文學領域逐漸盛行,少數民族作家張承志以草原題材為主的“文化尋根”掀起一番文學熱潮,自《騎手為什么歌唱母親》出版發行以來,張承志的不少作品都是圍繞草原、生態以及兩種文明沖突為主要題材,受到文學界的廣泛關注。1982年,他在雜志《十月》上刊載了中篇小說《黑駿馬》,并榮獲第二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及第二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榮譽獎。小說《黑駿馬》因其超高的藝術價值而成為經典文學作品,在其經典化的過程中,跨媒介傳播作為外部因素起到了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
關于“經典”的概念,還要追溯到《文心雕龍·宗經》中,“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鄭玄在《周禮注》中將“典”定義為“典,常也,經也,法也”。因此,“經典”可以理解為具有指導意義的,長期內可以作為規范性標準的作品。“經典化”則可以理解為,在一定時期內,“經典”的形成過程和機制。童慶炳的《文學經典建構諸因素及其關系》指出建構“經典”的六要素:文學作品的藝術價值、文學作品的可闡釋空間、意識形態和文化權利變動、文學理論和批評的價值取向、特定時期讀者的期待視野、發現人。由此,其他藝術形式的改編和“二次創作”正是說明了《黑駿馬》作為經典文學作品有著可闡釋的空間。
跨媒介文本的多樣化在滿足不同受眾群體的同時,還穩固了《黑駿馬》的經典地位。除了連環畫和電影,1983年的廣播劇和1986年的話劇版也廣受歡迎。廣播劇、話劇演出后,《黑駿馬》聲名大噪,其愛情悲劇深入人心。《黑駿馬》不同的藝術形式均獲得贊譽:連環畫獲多項大獎并被永久收藏,話劇在多地演出后備受關注,電影版及其導演也獲多個獎項。跨媒介改編融合多種文藝理念,拓寬了文學作品的傳播渠道,增強了傳播力,促進了文學作品的經典化進程。這種互動不僅體現在改編上,更推動了文學作品的深化和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