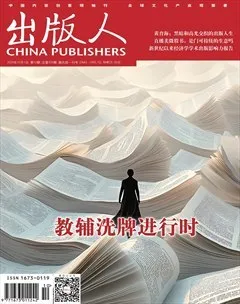絲絲編織古典情韻,密密敘寫生活之美
兒童文學理論家劉緒源先生曾感慨于童書市場充斥著太多過分“熱鬧”的作品,兒童文學的靜美、斯文、深邃、悠遠卻逐漸遠去。近期,二十一世紀出版社的“故鄉·童年”原創兒童文學書系推出吳新星的新作《珍珠塔》,于喧嘩中安放一份沉靜。該作以經典彈詞曲目《珍珠塔》命名,講述了民國時期少年萇玉離家學習彈詞的經歷。小說將兒童成長、文化傳承等“大”議題,細密地編織進瑣碎日常,近看只見針腳綿綿、微不足道,遠觀則如劉緒源所說的“故事的骨骼”得以顯現。在纖毫畢現的生活敘寫中,《珍珠塔》細無聲地傳遞著中國古典美學的深邃和情韻。
作為童書領域的“姐妹花”,吳新星和吳洲星兩姐妹的文字都保留著中國古典文學的韻味,不過,姐姐吳新星更專注于古典題材的敘寫。語言是故事的筋骨,吳新星在《珍珠塔》中延續了前作《玉簟寒》《采菱曲》《蘇三不要哭》等作品的古韻,以匠人之心錘煉文字、打磨語言。書中,“餳澀”“涇”“訇然一笑”等現代漢語不常用的詞匯偶現于行文間,“脅下生雙翼”“雙靨似桃花”之類的化用,以及“日照虹霓似,天清風雨聞”“清明時節春意濃,鶯啼柳浪燕舞空”等詩詞歌賦的引用,更是信手拈來、俯拾即是。從吳新星的文字中,能讀出近至張愛玲遠至《紅樓夢》的文學遺產。作者并不為了“俯就”兒童而使語言流于粗淺,而是以“量”的控制和人物的適度闡釋,保持了行文的曉暢通達。這種嚴肅慎重的書寫姿態,何嘗不是對孩子尊重的體現?
《珍珠塔》流溢的古典情韻,不僅融化于字詞間,還被編綴于本真的生活場景、人物生命中,并不因其“古”而與“今”拉開距離。嬉笑打趣,柴米油鹽,故事起始,尋常瑣事間夾雜少年人的淡淡惆悵,“苦度光陰長”。萇玉決心輟學求藝,“父母在,不遠游”是祈愿,但“游必有方”更是生活的無奈。辭家遠行,萇玉咀嚼人情冷暖,“分離十六春,天涯無處沒娘親”,《玉蜻蜓》的唱詞唱進了萇玉心里。日夜苦練,學有所長,萇玉獲得了獨自演出的機會,他講《珍珠塔》,唱方卿“受盡風霜吃盡虧”后“他將我另眼相看待”的人生,自己也重走了一趟那酸楚又歡欣的歲月光陰。詩詞不再是課本上的方塊黑字,而是萇玉自心底生發的感喟;彈詞也不再是遙不可及的古雅藝術,而是與萇玉的人生血肉交織的成長之見證。傳統文化在《珍珠塔》中不是外附于故事的皮,而是內化在故事里的血與骨。
進一步而言,《珍珠塔》亦將屬于個體的情感,編織進歷史洪流。大國的危難和小家的傷痛,透過趙先生等人的只言片語,在平緩流淌的敘事里若隱若現,這在時間維度賦予了故事厚度,但《珍珠塔》并沒有將宏大敘事放置臺前,而是選擇將歷史隱沒在故事背后,將故事隱沒在生活背后。傳統文化,事關歷史傳承和大國氣韻,但也和至親離別的思念、遠行從藝的辛酸與少年逐步成熟的人生有關。成長,關乎離別和傷痛,但也和蘿卜絲、玫瑰腐乳與小餛飩有關。連接歷史與當下、書內與書外的,不一定是豐功偉績、大忠大義,更可能是家長里短、一日三餐,因為這才是我們每個人都身處的本真生活。
從《藍門》到《碗燈》《鐘鼓樓下》,再到《珍珠塔》,“故鄉·童年”原創兒童文學書系中的作品均著力保留日常生活滋味,還原日常生活質感,回應了劉緒源對“純文學”真髓的期待。眾多文化產品“快餐化”的時代,我們需要更多的生活流敘事,需要“故鄉·童年”原創兒童文學書系及更多的作品,為我們在喧鬧的當下守住深邃和靜美。像《珍珠塔》這樣的故事,不一定為市場大聲簇擁,但有必要為其保留一片空間,讓其自在流淌,正如萇玉對自己的期待,經過時間的淘洗,等待這些故事的,會是一片“更豐美、更浩渺的水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