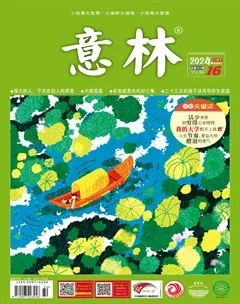隨心而動,讓愛情更像愛情
真愛不該有套路,更不該被財富與權力掩埋,而要打破成見,隨心所動。
真摯的愛情往往起于無心
《傲慢與偏見》第三卷第十八章,伊麗莎白與達西互訴衷情,她要達西先生講一講他當初是怎么愛上她的。
達西喃喃說:“我也說不準究竟是在什么時間,在什么地點,看見了你什么樣的神情,聽到了你什么樣的談吐,便開始愛上了你。那是在好久以前的事,等我發覺我自己開始愛上你的時候,我已是走了一半路了。”
好美的“一半路”,世上多少人并不擁有。
很多人冷靜而理性。有的人的“相愛”一開始就充滿“話術”,在動腦不動心的“技巧”中制造“愛情”。
真摯的愛情往往起于無心,甚至像《傲慢與偏見》中的達西與伊麗莎白,一個“傲慢”,一個“偏見”,都亮出自己的本色和鋒芒,似乎勢不兩立。但正是在這樣的真實中,他們互相沖突,互相感受著真性情。他們不會為了對方的“歡心”,故意展現自己“美好”的一面。而這恰恰抵達了愛情根本的要義:愛必須是兩個真實的人的互相看見,是生命蓬勃的原生態。

伊麗莎白十分明白這一點,她聽了達西的傾訴無比欣喜,對達西說:“有些女人從說話到神態到思想,總想博得你的歡心,你厭惡這種女人。我引起了你的注意,打動了你的心,因為我跟她們截然不同。”
“截然不同”——多么鮮明,多么清澈!
打破成見,讓愛情更像愛情
為什么簡·奧斯丁1796年能創作出這部長篇小說?寫出初稿的時候,她不過21歲。也許是因為當時的她正在經歷一場傷感的戀愛。
這一年,她遇到了學習法律的年輕男人勒弗羅伊,兩人相互傾慕。然而,奧斯丁的父母并不贊同這場戀情,因為勒弗羅伊沒錢,還要養一大家人。奧斯丁不得不放棄了心中所愛,她給姐姐卡桑德拉寫了一封憂傷的信:“終于,這一天還是到來了,我將與湯姆·勒弗羅伊告別。而當你收到這封信時,一切都已結束。一想到這些,我不禁淚流。”
如何讓愛情簡單一些?如何走出種種壓制在愛情之上的習見?《傲慢與偏見》寫出了一種幾乎不可能實現的情感:打破階層差距,打破環境壓力,打破心中的成見,讓愛情更像愛情。這就是簡·奧斯丁的“截然不同”,她在現實中喪失的愛情,要在小說中盡情地實現。
從更廣的歷史視野看,簡·奧斯丁的愛情理念也來自她比較純凈的生活經歷。她并沒有經歷完整的學校教育:“我可以坦誠地說,世上敢于當女作家的人中間,我是最沒有學問、最無知識的一個。”她的小說題材限定于自己的直接經驗:“我要描寫的不過是鄉村中的三四戶人家。”
然而,正是在這樣的小日常中,奧斯丁沒有喪失關于生命的常識,她是以女性的自然之心創造自己的小說天地,以文學的眼光“重構”一個有愛的世界。在那樣驚悚的時代,奧斯丁以細柔的筆觸描繪出心中理想的愛情,那是一片多么溫暖的期待,是女性以自己的“小世界”對冰涼時代的抵抗。
“逆流而上”的情感力度
有意思的是,《傲慢與偏見》中寫出了兩種面對愛情的代際關系。
小說第十七章,得知女兒要嫁給達西,父親班納特先生有些擔心:“我還是勸你重新考慮一下。我了解你的脾氣,莉齊。我知道,除非你真正敬重你的丈夫,除非你認為他值得仰慕,否則,你就不會覺得幸福,也不會覺得體面。你是那樣活潑聰慧,要是嫁個不般配的丈夫,那是極其危險的。你很難逃脫丟臉和悲慘的下場。孩子,別讓我傷心地看著你瞧不起你的終身伴侶。你可不要稀里糊涂的。”
這位年收入兩千英鎊的鄉紳并沒有看重達西那年收入一萬英鎊的財富,而是讓女兒堅持精神上的門當戶對。當他確認女兒愛上的是達西的人,而不是他的錢,班納特先生終于送上了祝福:“好孩子,我沒有意見了。如果真是這樣,他倒配得上你。莉齊,我可不愿意讓你嫁給一個與你不相配的人。”
父親的一番話讓伊麗莎白“心里那塊大石頭這才算放了下來”,感嘆“所有歡樂愉快的事情都來得太突然”。
而母親則大為不同,一聽到女兒要嫁給達西,她頓時感覺要暈過去,因為她瞬間看到了金錢滾滾的奇景:“我的心肝莉齊!你就要大富大貴了!你會有多少零用錢,多少珠寶,多少馬車啊!哦,親愛的莉齊!我以前那么討厭他,請代我向他賠罪,但愿他不計較。親愛的莉齊!城里有座住宅!家里琳瑯滿目!三個女兒出嫁啦!每年有一萬英鎊的收入!哦,天哪!我會怎么樣啊,我要發狂了。”
這話讓伊麗莎白面紅耳赤,“慶幸的是,母親這些信口開河的話,只有她一個人聽見”。
代際關系總是有這些哭笑不得的場景,父親母親的態度表達的是兩種不同的價值觀。《傲慢與偏見》用這樣的描寫,釋放出“逆流而上”的情感力度:在當時的英國等級社會,在愛情中追逐金錢與地位,是絕對多數的選擇。
愛情的嶄新定義
即使是在奧斯丁去世后的年代,依舊有無數的真愛被財富與權力掩埋。
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嘯山莊》中,凱瑟琳深愛希斯克利夫,但她“清醒”地嫁給了“門當戶對”的埃德加。在她答應埃德加的求婚后,對女管家耐莉說,嫁給埃德加,是因為“他長得英俊,跟他在一起很開心”“他年輕,滿面春風”“他將來會有很多錢,我會成為這一帶最尊貴的女人”。
耐莉的回答特別干脆:“這都很糟!”她質問凱瑟琳:“可是,天下有錢的美少年還有著呢,也許比他更有錢、更英俊,那么,你怎么不去愛他們呢?”
凱瑟琳不得不說:“我清楚地知道我是做錯了……埃德加與我,像月光和閃電、冰霜和火焰那樣截然不同。我生命中最大的思念就是希斯克利夫。即使其他一切都毀滅了,獨有他留下來,我依然還是我。假使其他一切都留下來,獨有他毀滅了,那整個宇宙就變成了一個巨大的陌生人,我再不像是它的一部分了。”
凱瑟琳如此清楚地知道自己與埃德加“截然不同”,但她還是嫁給了他。
知與行之間是那么遙遠。也許,世上的事就是這樣乖戾,“截然不同”的實現需要很多很多代的努力。簡·奧斯丁的貢獻是,她在200年前就寫出了“截然不同”的幸福,對愛情做了嶄新的定義。
這讓我想起比奧斯丁晚生41年的夏洛蒂·勃朗特,她曾經批評奧斯丁:“她全然不知激情為何物。”這恐怕是嚴重的誤解,有時候,默默地拒絕一種主流的慣性生活,比仰天呼號更為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