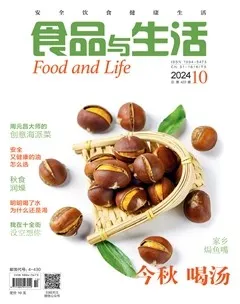《食神》 誰解其中味
時隔28年,喜劇電影《食神》再次登上了國內大銀幕。盡管此次票房表現平平,但1996年該片在香港上映時,它以高達4000萬的票房成為當年我國香港地區的票房亞軍。世事總是這樣難以預料,當年票房、口碑雙失利的《大話西游》系列,在2014年的重映時竟斬獲1.85億的票房,戰績驕人。想來影片大概也遵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道理,此一時彼一時。如果不看票房,那么這部藏在遙遠記憶里的《食神》,因為重映被激活,似乎分外適合本專欄。
貼切的菜品
作為一部以美食為主題的影視作品,食物自然是重中之重。開場的食神點評戲就非常吸睛,我們也能從中窺得何謂優秀粵菜。
開場四道菜中,皇帝炒飯和金縷佛衣的問題都出在了食材上,一個是用錯食材,一個是用了壞的食材,這些在菜品制作時都是大忌。而錦繡多味魚和乾坤燒鵝的問題則出在“色”上。
然而,粵菜對優秀菜品的要求是全方位的。在烹調上以炒、爆為主,講究清而不淡,鮮而不俗,嫩而不生,油而不膩,要求“五滋”(香、松、軟、肥、濃)“六味”(酸、甜、苦、辣、咸、鮮)俱佳,同時要求火候和油溫的掌握恰到好處,此外還講究菜的氣勢、檔次。
而結尾的食神大戰,則是福建名菜佛跳墻與市井之食叉燒飯的對決。這固然有戲劇結構上的必須,也體現了我國傳統文化的陰陽相生,大道至簡。正如遍嘗天下美食的洪七公對黃蓉的燒白菜贊不絕口一般,能抵御鮑、參攻擊的,正是那碗鮮甜的叉燒與香糯的米飯。
如果說開篇和結尾的菜品是主人公與外部關系構建的重要道具,那么人物自身轉變更離不開三個重要的食物道具。想起自己最初對《食神》的印象,莫過于當時還被譯為“撒尿牛丸”的“爆漿瀨尿牛丸”和“黯然銷魂飯”,后者如今在一些港式茶餐廳中已經是非常普遍的存在。如果說最初對于這兩個菜品印象深刻,是因為后者與金庸先生的“黯然銷魂掌”張冠李戴而覺得滑稽,那么前者可能還帶著一些惡趣味。
時過境遷,當我走進影院觀看時,突然想清楚了一個問題:為什么是瀨尿牛丸?它固然是著名的街頭小吃,但香港街頭小吃那么多,燒鵝、云吞面、菠蘿包……何以是它?讓男主人公跌入谷底的車仔面,又名“雜碎面”,象征人生進入雜碎階段。讓男主人公感到溫暖的叉燒飯,又名“黯然銷魂飯”。而讓男主人公絕處逢生的秘訣是選擇了爆漿瀨尿牛丸,原因無他,唯四字耳:觸底反彈。這既是香港撒尿牛丸的物理特性,彈力勁道,又是主人公人物曲線的具象,令人擊節稱妙!
正因為是美食電影,食物的選擇往往更具匠心。雖然對于《食神》的解讀早已遍布網絡,然而,如果我們再仔細深入地推敲一下,還是能從嚴謹的創作中讀出許多主創的巧思。
神秘的“食神”
“食神”一詞簡單直白,如果不多做解釋,大眾自然能意會為“食物之神”。這固然不錯,卻忽略了影片中主人公前后階段不同的能力:第一次食神大賽時,男主角在四道頂級美食面前,點評準確犀利,可以看出是味覺靈敏美食家,但他被下屬打敗,走下神壇,則是因為當時的他不善烹飪。
那么,“食神”究竟是指“美食家”,還是“頂級大廚”?在我的理解里,影片《食神》顯然將“食神”描述為:既是美食家,又是頂級大廚的狀態,這種疊加即便在日常生活里,也不是必然:“美食家”未必擅廚,畢竟“食神帶祿則為天廚”——后期的男主角通過進入佛門進修,學習了一手好活兒。不過,即便有一條敏銳的舌頭,一手精湛的廚藝,卻還都不是影片所想表示的“食神”的全部。
影片結尾的比賽中,通過評委夸張地闡釋,如專注、好刀功、好炒功這些條件被一一添加上去,而尤其重要的一點,則是通過男主角自己提到的“忠誠”(品德)。在對于人才的傳統評定中,無論哪個門類都有自己的“圣”,而這種“圣”尤其表現在道德上的自律。從這個角度來說,被踢館前的男主角和踢館成功的男配雖然都暫時得到過“食神”的榮譽,但他們的失利是必然的。
非常有趣的是,影片里“食神”獎牌下繞了一圈“FranceCuisineClub
(法國廚藝俱樂部)”的文字。男主在踢館前,穿著浮夸的中式大廚服裝,而包藏禍心的徒弟,則穿著西式廚師的服裝;踢館成功后,西式廚師服也換了更
加深黑的顏色。這種構思寓意不免令人感嘆創作者的大膽犀利,他既批判了以資本驅動行為的西化模式,對于假借傳統故弄玄虛的“銀樣镴槍頭”們,也是毫不客氣地趕下了神壇。我想,他所贊美的真正食神,不僅具備世俗意義上的技術,更是心中有眾生,并能放下我執的存在——興許這樣的存在要求太過苛刻,因此主創用了“人人都是食神”,并將男主收編入天庭,來表現這樣一種虛幻——“食神”是一種可以無限接近,卻無法到達的狀態。
在我看來,重映電影票房的多寡實則與影片質量無甚關聯,《食神》的存在,客觀上已是中國美食電影中的重要一部。不同時代的觀眾恰似“每個人都是食神”,各品其滋味,不是么?
(本文圖片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