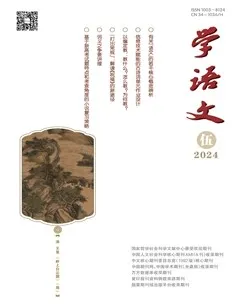呼應《鄉土中國》,銜接統編教材
摘要:近兩年高考新課標卷文學類文本閱讀《放牛記》《給兒子》和《長河·社戲》共同呼應《鄉土中國》,厚植鄉土情懷,分別描繪鄉土自由本真的成長環境,弘揚以土為生的勞動精神和展示以文化人的禮俗力量。命題體現素養立意,銜接統編教材。選擇題考查文本細讀能力,關聯教材選篇;主觀題綜合考查閱讀素養,關聯教材任務。備考應立足單篇閱讀教學,整合單元學習任務,全面梳理教材選篇,落實整本書閱讀。
關鍵詞:高考;新課標卷;文學類文本閱讀;統編教材
《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和《中國高考評價體系》作為高考評價的基本依據和核心指南,立足語文學科核心素養,強化“價值引領、素養導向、能力為重、知識為基”的多維考查模式,強調從“考知識”向“考能力素養”的轉變,突出從“解題”到“解決問題”的新動向。高考新課標卷體現了當前課程和命題評價改革的方向,分析其命題特點具有重要意義。2024年新課標Ⅰ卷、2023年新課標Ⅰ卷及新課標Ⅱ卷的文學文本閱讀試題分別選用當代作家徐則臣的《放牛記》、陳村的《給兒子》和現代作家沈從文的《長河·社戲》。文本選題呼應《鄉土中國》整本書閱讀的相關內涵,凸顯鄉土情懷;命題銜接統編教材,關聯教材學習任務和選篇,綜合考查文學閱讀素養。
一、文本選材:呼應《鄉土中國》,厚植鄉土情懷
整本書閱讀為高中語文課程標準中18個學習任務群之首,《鄉土中國》及《紅樓夢》整本書閱讀也是統編高中語文教材的必修單元,其測評問題一直備受關注。雖然近年高考試題沒有直接考查整本書閱讀,但文學類閱讀試題的選材與整本書閱讀存在諸多關聯和呼應。近兩年新課標卷的三篇文學文本堪稱《鄉土中國》的文學形態,共同呼應《鄉土中國》整本書閱讀。三篇文本同中有異,2024年新課標Ⅰ卷的《放牛記》在少年成長中回憶鄉村放牛的美好時光,蘊含自由本真的鄉土哲思;2023年新課標Ⅰ卷陳村的《給兒子》在城市變遷中追憶知青生活,弘揚了以土為生的勞動精神;2023年新課標Ⅱ卷沈從文的《長河·社戲》則在時局動蕩中書寫鄉土本色,展示了以文化人的禮俗力量。
(一)同:在“變”與“常”中書寫鄉土的精神力量
21世紀的今天,重讀《鄉土中國》的意義在于理解鄉土中國的現代轉型,從鄉土中汲取成長的精神力量。《放牛記》《給兒子》《長河·社戲》呼應《鄉土中國》的相關內涵,其共同點是在“變”與“常”中書寫鄉土的精神力量。具體而言,徐則臣的《放牛記》是在個人成長變化及鄉村變遷中回憶了童年放牛的時光,表達了對自然、生命以及成長的永恒思考。在文中,作者動情地表達了放牛生活與自我成長的關系:“牛群是鄉村的守護者,它們默默地耕耘著這片土地,見證著鄉村的變遷。而我,與它們相伴成長,從它們身上學會了堅韌與毅力。”陳村的《給兒子》寫于1984年,當時正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關鍵時期,人們對鄉土的感情也在發生著巨大的變化,文末也表現出這種微妙的心態:“要是你的船走進漕河,看見的只是一排煙囪,一排廠房,兒子,你該替我痛哭一場才是。雖然我為鄉親們高興。”作者一方面為工業化進程中鄉土的消逝而痛哭,但也為鄉親們生活水平的提升而高興,時代變遷無可避免,而鄉土之“常”正在于勞動精神的傳承。沈從文的《長河·社戲》與費孝通的《鄉土中國》都寫于20世紀三四十年代,當時中國正處于社會動蕩的變遷之中,雖然諸多具體的變化并沒有完全顯現,但沈從文和費孝通一樣,敏銳地嗅到了其中的變革氣息。《社戲》寫到“省里向上調兵開拔的事”已讓讀者感到尋常歲月隱約生變的氣氛,但蘿卜溪照舊舉行社戲,表現了鄉土的“常”,展示了鄉土文化的慣性。
(二)異:分別表現“成長”“勞動”與“禮俗”等內涵
雖然新高考三篇文本都書寫鄉土精神,但具體內涵各有側重。《放牛記》側重于描繪鄉土自由本真的成長環境,《給兒子》側重表現以土為生的勞動精神,《社戲》則側重表現以文化人的禮俗力量。
1.自由本真的成長環境
《放牛記》敘述少年放牛的經歷,以細膩的筆法講述了放牛的過程,從訓練牛、放牛的日常、與同伴的互動等多方面展示了鄉土自然生活的美好。少年時代的放牛生活是豐富多彩和自由自在的,“放牛給了我一個幾近完美的少年時代,放松,自由,融入野地里,跟自然和大地曾經如此貼近。”雖然作者在文中提到“往事總在回憶時被賦予意義”,鄉土生活的價值可能因時間距離而“拔高”,但不可否認,文中蘊含了作者對鄉土時光深切的懷念和珍視。作者深切地懷念少年時與鄉土自然親密接觸的時光,不僅因為時間距離產生的美,更因為鄉土生活中的自由本真。在城市化高度發展的今天,青少年成長壓力日益加重,鄉土生活自由本真的成長環境及其背后的價值理念應被當代人重新認識和重視。
2.以土為生的勞動精神
《給兒子》在對農村風物細致入微的描寫中體現了作者深厚的鄉土情懷,也在父親對兒子的諄諄教誨中表現了以土為生的勞動精神。文本表面敘述老知青對未來兒子的囑咐,實際暗含了自身對在鄉土插隊生活的回憶和眷戀,希望兒子能夠在大地的勞動中找到成長的力量。“下田去吧,兒子”這個段落深切地表現了對勞動的重視和大地的感恩。父親語重心長地囑咐兒子要掌握“大鍬”“錘子”“刀”等勞作工具,要認識“麥子”“稻子”“高粱”等農作物,要感受鄉土和陽光的氣息,因為鄉土是永遠無法丟棄的。正如《鄉土中國》所言:“土”是作為社會個體的命根,鄉下人離不開泥土。因為在鄉下住,種地是最普通的謀生方式。[1]通過勞動,大地在仁慈地輸出,因為大地的輸出,我們才能存活,才得以延續。
3.以文化人的禮俗力量
《長河·社戲》敘述了蘿卜溪在尋常歲月隱約生變的背景下,仍然照舊例舉行社戲的盛況。文章通過熱鬧酣暢的舞臺場景和鄉土風俗描寫,表現了鄉土文化的力量。李伯勇指出,《長河》是一部被忽視被遮蔽的,不可多得的敘寫鄉土自性的文學文本。它展現了鄉土內部道德結構和文化原型仍然保持的某種均衡性和神圣化。[2]在鄉土中國,社會治理和活動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傳統習俗來進行的,并形成禮俗社會。規矩不是法律,而是“習”出來的禮俗。[3]在社戲的開展當中,我們可以看到鄉土文化的慣性力量。文本不惜筆墨用多種手法描寫社戲的儀式感,這種儀式感正是鄉土禮俗的重要表現。另外,文本在記述社戲的籌備及演出過程中多處使用“依照往年成例”“照習慣”“照例”等詞語,則表明社戲的形式、內容幾乎都不變,體現了這種禮俗力量的慣性。
二、命題特點:銜接統編教材,考查核心素養
近年教育部教育考試院發布的高考語文試題評析反復強調教材關聯的重要性,文學類文本閱讀試題也注重銜接統編教材,考查核心素養。
(一)選擇題:關聯教材選篇,關注文本細讀
選擇題命題遵循“守正創新”的原則,穩中有變。第一道選擇題主要是“守正”,以對文本核心內容的理解為基礎測試內容,對應課標“在鑒賞活動中,能結合作品的具體內容,闡釋作品的情感、形象、主題和思想內涵”[4]的要求。試題主要考查文本細讀的能力,選項主要涉及對人物形象及環境特點的理解判斷,解題可從原文找到直接或間接的依據進行推斷,設誤項比較明顯,整體難度不大。2024年Ⅰ卷的A選項需判斷父親是否“合群”,C選項判斷“我”是否“悲觀”,D選項判斷環境是否“陰森怪異”,以上選項都可從文中找出相關依據進行排除。2023年Ⅰ卷的B選項判斷村民是否“心存善意”與文中“他們沒有壞意”顯然矛盾,2023年Ⅱ卷D選項判斷會長是否“吝嗇”,也可從原文反向推導出來。
第二道選擇題則有不同程度的創新。2024年及2023年Ⅰ卷都選取文中片段或句子設題,圍繞典型的藝術手法及特色進行設問,如先抑后揚的手法、視聽等多重感官描寫、語句單獨成段的藝術效果及前后矛盾產生的張力問題等等,對應課標“能敏銳感受文本或交際對象語言特點和情感特征,迅速判斷其表達正誤與恰當程度”[5]的要求。2023年Ⅱ卷的選項則關聯教材選篇,分別關聯教材《林教頭風雪山神廟》《社戲》《邊城》等篇目。選項關聯教材除了具有引導教學的價值,也體現了課標“能比較兩個以上的文學作品在主題、表現形式、作品風格上的異同”[6]的要求。
(二)主觀題:關聯教材任務,考查閱讀素養
主觀題同樣穩中有變。第一道主觀題延續近年高考“因文設題”的命題理念和“限定+指令”的設問方式,緊貼文本命題,關聯教材任務。如2024年Ⅰ卷限定文中原句“放牛給了我一個幾近完美的少年時代”,與高中語文教材必修上冊《我與地壇》“理解關鍵語句”相關學習任務關聯;2023年Ⅰ卷的限定是“多重身心感受”,2023年Ⅱ卷的限定是“社戲的儀式感”;設問指令分別要求“分析原因”“梳理概括”和“簡要說明”。
第二道主觀題呈創新變化,體現課標“考試、測評題目應以具體的情境為載體,以典型任務為主要內容”[7]的要求。2024年Ⅰ卷設置開放性問題,要求學生分析作者是否做到了文中所說“不愿在回憶往事時為放牛‘賦予意義’”,此題以文學體驗情境為載體,要求學生分析作者寫作心態和文本內容的關系。試題給出了多種答題的可能,鼓勵學生獨立思考和表達自己的真實見解,同時與魯迅《朝花夕拾》等回憶性散文關聯,考查對回憶性散文的閱讀理解、鑒賞評論能力。2023年Ⅰ卷試題要求“寫文學短評思路”的情境任務讓人耳目一新,關聯統編教材“學寫文學短評”單元學習任務。試題立足文本理解與文本建構的復雜因素命題,聚焦“未來·回憶·成長”和“河流”兩組關鍵詞,第一組關鍵詞指向文本的敘述結構和主題理解——表面上是父親想象兒子未來的旅行,實際是父親對過去的回憶,并希望兒子也能從勞動中成長;第二組關鍵詞則指向形象內涵和作用的理解。2023年Ⅱ卷試題要求對文本多處使用“照習慣”“照例”的語言特點分析其意味。考生需要結合文本和個人認知體驗,在了解文學史常識和文學創作一般規律的基礎上,對文本藝術創新的主題意向、思想蘊涵能有所領悟并展開聯想。[8]命題指向“語言建構與運用”“審美鑒賞與創造”等核心素養。
三、備考建議:立足單篇,整合任務,梳理教材
長期以來,高考復習采用“題型+套路+重復”的模式,這種“機械刷題”越來越難起作用,收益也越來越低。文學類文本閱讀的備考應立足單篇文本,有效整合教材單元學習任務和整本書閱讀相關內容。
(一)立足單篇閱讀教學,積累建構必備知識
雖然當前“大概念”“大單元”教學正開展得如火如荼,但實踐中要避免脫離文本、生搬硬套、膚淺零碎及抽象空洞等問題。應把握好“單篇”與“大單元”的辯證關系,語文教學的基礎是單篇的經典文本。雖然新高考多處關聯教材選篇,但命題落腳點還在于試題文本。因此,應立足單篇閱讀教學,提高學生文本細讀能力,在文本細讀中積累建構文學閱讀的必備知識。備考應引導學生逐行逐句對典范的試題文本進行解構分析,深入文本內部,引導學生感受文本的語言特點和情感特征,察覺其言外之意和隱含的情感傾向,避免閱讀的“表面滑行”。另外,復習備考中應避免以知識為核心的灌輸教學,而應在閱讀中積累建構必備知識,如閱讀2023年新課標Ⅱ卷《長河·社戲》就可以積累建構細節暗示、人物刻畫方法、景物民俗(環境)描寫作用、描寫方法等必備知識。
(二)整合單元任務內容,提高問題解決能力
以教材單元學習任務轉化為高考測評已然成為一種新趨勢,備考應有效整合單元學習任務內容。具體可從以下三方面進行:一是對學習任務涉及的必備知識進行提取、梳理、整合,如必修下冊第六單元學習任務可提取“突發事件”“講故事的藝術”“扁平人物和圓形人物”等知識。二是提煉學習任務所需要的關鍵能力,如文學點評要善于聚焦、抓住小切口,讀書札記要凸顯要點和表達心得體會等等。三是根據單元任務內容進行命題改編,以測評提高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單元學習任務設置的問題情境本身就是測評的題目形式,通過具體情境和典型任務來測評學習效果和思維品質。[9]如有關“突發事件”的學習任務:《祝福》《林教頭風雪山神廟》都出現一系列的突發事件,這些“突發事件”在文中有何作用?又如有關敘事手法的學習任務:《變形記》中采用雙重敘事視角,產生了怎樣藝術效果?[10]
(三)梳理整合教材選篇,落實整本書閱讀
近年高考文學閱讀試題關聯教材,這要求我們在備考中需要系統梳理整合教材內容,減少無效刷題,把更多精力放在重讀和梳理教材經典小說上,如重讀《百合花》《哦,香雪》《祝福》《變形記》等經典篇目,從知人論世、情節梳理、主題歸納、藝術手法、文本建構等方面進行系統復習。另外,整本書閱讀的測評不容忽視,高考文學閱讀的考查上應會延續與整本書的有機關聯。復習備考應建構系統的測評體系,具體可結合《鄉土中國》和《紅樓夢》文本內容、整本書閱讀的學習目標和測評目標,在三個閱讀能力層級的基礎上,將測評層級分為文本知識、文本理解和文本建構,從淺閱讀導向深閱讀,初步建構整本書閱讀測評體系。以《紅樓夢》為例,可以建構其測評體系如表1。

復習備考中,可根據測評體系有針對性地命制試題進行訓練檢測,以測評帶動整本書閱讀。雖然當前整本書閱讀測評方式尚未明確,但測評與考試作為課程評價的重要組成部分,關聯《鄉土中國》和《紅樓夢》想必將成為高考閱讀試題的新動向。教學備考應綜合運用多種閱讀方式落實整本書閱讀,引導學生讀懂文本,把握文本豐富的內涵和精髓,綜合提高學生的閱讀素養。
參考文獻:
[1][3]費孝通.鄉土中國[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社,1985:2,5.
[2]李伯勇.鄉土中國的文學形態——以《長河》為例[J].小說評論,2012(04).
[4][5][6][7]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2017年版2020年修訂)[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38,37,38,48.
[8]張開.基于高考評價體系的語文科考試內容改革實施路徑[J].中國考試,2019(12).
[9]楊勇.落實“單元學習任務”促進“教學評”有機銜接[J].語文建設,2023(07).
[10]謝中謀.基于教材關聯的小說閱讀備考策略——從《伍子胥·江上》說起[J].中學語文,2022(31).
(作者:謝中謀,廣東省深圳市龍崗區平湖外國語學校語文教師)
[責編:夏家順;校對:胡承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