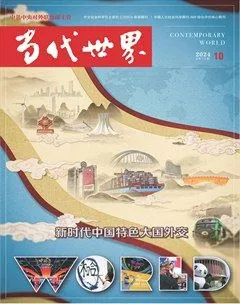未來峰會呼喚多邊合作
人類社會該向何處去,是一個帶有終極意義的重大問題。2024年9月22日召開的聯合國未來峰會給出了權威答案。這次峰會約有130位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出席,峰會最重要的成果是通過了《未來契約》及其附件《全球數字契約》和《子孫后代問題宣言》。《未來契約》繪就了一幅關于人類社會美好未來的宏偉藍圖,其著眼于人類未來,立足于多邊合作,努力建設一個安全、和平、公正、平等、包容、可持續和繁榮的世界。
多邊合作是世界各國實現共同繁榮的客觀需要
發展是各國孜孜以求的共同目標。近現代以來,后發國家無不渴望自主性發展,但真正成功躋身發達國家行列的國家屈指可數。究其原因,西方主導的世界經濟舊秩序是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障礙之一。西方國家率先崛起后,其憑借更高附加值的工業品,在與發展中國家進行國際貿易時更容易從中獲利,而那些出售原材料和初級產品的非工業國家則長期被鎖定在供應鏈的最低端。這種看似公平合理的所謂“自由貿易”,使南北發展鴻溝越來越大。尤其在資本主義國際分工體系下,世界不同區域間收入水平出現“大分流”(GreatDivergence)。在近代之前,歐洲與亞洲間的經濟差距微弱,亞洲國家甚至長期居于世界經濟中心位置。但到了19世紀,這種相對平等的互動關系,被中心與邊緣間不平等的關系所取代。

西方發達國家占據“先發優勢”后,為保持自身在全球產業鏈的高端位置,想方設法阻撓其他國家的經濟趕超勢頭,尤其是阻遏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進程,通過經濟脅迫、武力征服、戰略誤導等各種手段,迫使后發國家重新“去工業化”。要想改變這種“大分流”狀況,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必須加強多邊合作,改變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舊秩序,最終實現共同發展。
多邊合作是人類社會實現共同安全的必然要求
永久和平是人類社會的共同夙愿,但戰爭與沖突頻繁爆發。據統計,在有歷史記載的3421年中,只有268年沒有發生戰爭。尤其近代以來,西方列強憑借其在軍事和經濟領域的先發優勢,開啟了對外擴張進程。西方主導下的世界歷史,基本就是不折不扣的戰爭與沖突史。托馬斯·曼在其《社會權力的來源》一書中指出,歐洲列強在1494—1975年有75%的時間在策動戰爭,完全沒有戰爭的時間不超過25年,而權力轉移期則成為沖突高發期。在歷史上,守成霸權國為防止對手崛起而發動的“預防性戰爭”十分普遍:2000多年前的伯羅奔尼撒戰爭源于斯巴達對“雅典權力的日趨增強以及由此在斯巴達所引發的擔心”;1866年德國對奧地利戰爭,是德國抓住奧地利軍事改革未完成的時機發動的;1904年日俄戰爭是日本眼見俄國在遠東軍事力量日益強大而采取的先發制人策略;第一次世界大戰源于英法擔心德國崛起過快并侵害其殖民利益。意大利歷史學家阿瑞吉深入考察了資本累積與戰爭爆發的關系后,作出了“系統性資本累積周期,必定以大規模戰爭作結”的結論。
當前,隨著大變局深度演進,“南升北降”態勢逐步顯現,尤其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的群體性崛起,推動國際格局進入新的發展周期。美國為維護自身霸權地位,日益加大對中俄打壓力度,由此導致大國對抗愈發劇烈。烏克蘭危機、巴以沖突等種種趨勢表明,世界性戰爭爆發的風險正日益加大。
“合則兩利,斗則俱傷。”大量事實表明,訴諸戰爭實現霸權目標得不償失,甚至適得其反。古羅馬學者西塞羅曾說:“絕大多數人認為從戰爭中獲得的東西,要比在和平環境中獲得的東西有價值,其實這是錯誤的。”在現代技術條件下,尤其是核武器導致的“相互確保摧毀”條件下,指望通過發動戰爭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很可能是自取滅亡。在此背景下,大國對抗同樣需要管控危機,并盡可能通過多邊合作實現良性競爭。例如,各國就核裁軍達成一致,并承諾采取步驟防止外層空間軍備競賽和管理致命自主武器的使用等,就是多邊合作的正面案例。2022年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議,就是中國為緩解人類社會戰爭風險提供的中國方案。
多邊合作是不同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途徑
世界各國自然歷史條件不同,文化價值觀千差萬別。這種文化差異并無高低優劣之分。與此同時,各國的政治制度也因國情不同,存在不小差異,因此衡量政治制度優劣,首先要考慮其是否適合國情。習近平主席指出:“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了才知道。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合不合適,只有這個國家的人民才最有發言權。”
然而,近代以來,西方國家因率先實現工業化,將自身政治制度和價值觀念也奉為圭臬,將其打造成所謂“普世價值”,強行向其他國家輸出。“文明與野蠻”二元對立敘事是西方國家的典型政治話語。在這種敘事中,西方國家將自身塑造為“文明世界”,將非西方世界視為“野蠻”或“半開化”國家。在殖民主義時期,這種基于“西方中心論”的文明話語(實際是政治話語),使“文明國家”征服或奴役“野蠻國家”變得“天經地義”。
在后殖民時代,基于基督教和白人種族主義的“文明與野蠻”敘事已很難適應形勢發展。在此背景下,“文明與野蠻”敘事開始“轉型升級”,從相對具象的宗教標準和種族標準,轉向更加抽象的“現代性”標準,也就是將西方國家的政治制度、經濟模式和價值觀念作為衡量文明優劣的標尺。非西方國家只有認可和接受這套西方式“普世價值”,才有可能被列入“文明國家”行列。這套基于西方價值觀的文明標準看似溫情脈脈,實則仍是要將世界分為三六九等,進而在這種新的等級性文明觀基礎上塑造出等級性世界秩序。
在這套政治敘事下,只有接受這套有利于西方壟斷資本的政策主張,才會受到西方政要和媒體的認可和歡迎。反之,那些不聽西方號令的國家則可能被打入另冊,并冠以“專制國家”、“失敗國家”乃至“流氓國家”等種種惡名,甚至最終被武力推翻。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等國的遭遇就是典型案例。
當前世界政治中的種種不合理現象,更加凸顯出加強多邊合作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在很大程度上,多邊合作實際是國際關系民主化的體現。不過,世界上沒有“天上掉餡餅”的好事,要讓習慣了作威作福的某些西方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平等地進行多邊合作,不能靠一味妥協退讓,而是需要弘揚斗爭精神,堅持斗爭與合作并重。帝國主義者的天性就是“欺軟怕硬”“看人下菜碟”。只有當世界各國尤其是“全球南方”團結聯合,形成強有力的制衡力量時,全球性的多邊合作才會真正實現,聯合國《未來契約》描繪的美好愿景才可能變為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