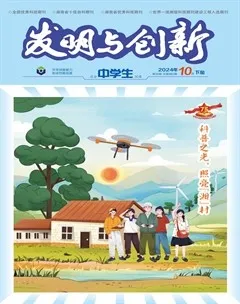魚在“江湖”





“湘江北去”而不是“一江春水向東流”,何為其然?湖南西有武陵、雪峰山,南有南嶺、陽明山,東有羅霄、幕阜山,東西南三面環山乃天然屏障,將四方的云和雨截斷,化作涓涓細流逐級匯流入江,好山好水孕育出了“魚米之鄉”的美譽。湖南的“江”是湘江,湖南的“湖”是洞庭湖,而闖蕩“江湖”的則是“魚”。
溈水是湘江一級支流,長沙市望城區境內有八曲河匯入溈水,八曲河的一條支流橫穿過白箬鋪境內,將千畝良田滋養,讓我們得以在因圍堤建壩修建的一片池塘里,對這些籍籍無名又無處不在的“江湖好漢”一探究竟。
如果你在岸邊凝視“深淵”,在“深淵”凝視你的很有可能是一條蝦虎魚。蝦虎即“吃蝦的老虎”,這可是江湖中響當當的名號,正所謂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對于蝦虎魚而言,蝦就是最好的“米”。它們幾厘米長的身軀下,有著與老虎如出一轍的獵殺方式——擬態伏擊。
水中伏擊,絕非易事。不僅需要借助魚鰾克服浮力,還需要利用吸盤結構的腹鰭長時間“潛伏”在水底。蝦虎魚的眼睛長在頭頂,關注著隨時可能到來的危險。即便如此,由于魚類沒有可調節曲度的晶狀體,所以它們天生“近視”,再加上沒有眼瞼,常常給人一種“死不瞑目”的即視感。
如果要問蝦虎魚與老虎究竟有何關聯,可以說蝦虎魚的嘴和老虎的嘴同源,世界上所有的脊椎動物都繼承了魚類祖先的嘴巴;也可以說蝦虎魚在宣示主權時能發出與老虎咆哮類似的聲音,不過這種“咆哮”聲我們無法聽到。
魚類是地球上第一種進化出上下頜的動物,這使得它們得以進行“武力輸出”。志留紀的魚依仗“頜武器”縱橫四海成為世界“霸主”,其間的杰出代表當屬盾皮魚類中的鄧氏魚,史稱“恐魚”。它們龐大的身軀和尖牙利齒讓海洋生靈險象環生,也正因為如此,輻鰭魚和肉鰭魚這對患難“兄弟”被盾皮魚驅逐出海域,被迫進入淡水區,從此淪落“江湖”。
這兩種魚在“江湖”亦是身不由己。江湖多“險詐”,說漲就漲,說干就干,在干濕交替的變化無常中,肉鰭魚最終退出“江湖”并成功上岸,成為人類的祖先,而輻鰭魚依舊在“江湖”中“內卷”,淪為人類餐桌上的河鮮。
魚類的嘴巴,有且只有三種情況:一種是上下頜一樣長,叫端位口,如鯽魚。一種是下頜長于上頜,叫上位口,如翹嘴紅鲌。還有一種則是下位口,如棒花魚。上位口的魚一般捕食位于其上方的獵物,下位口的魚則相反。棒花魚長有胡須,即口須,蝦虎魚則沒有。
口須是魚類的味覺器官,你可以理解為人類的舌頭。鯉魚有兩對胡須,分別感受左右兩邊食物的信息。黃顙魚有四對胡須,可以感受來自四面八方的味覺信息。泥鰍則滿嘴都是胡須。
并非所有的魚都能成為蝦虎魚這類的“機會主義者”,它們必須和獵物賽跑。魚的尾鰭是速度推進器,但左右擺尾容易造成側翻,于是魚類在背腹面長出了背鰭和腹鰭以協調尾鰭的運動。這樣速度也就加快了,但速度太快容易“撞墻”,再加上“眼神”不好使,魚類又進化出胸鰭和腹鰭分別負責“制動”和“轉向”。
此外,胸鰭和腹鰭作為偶鰭同樣能防止側翻,于是不同魚類的背鰭開始發生改變。有的魚背鰭很長,比如黑魚;有的魚背鰭演化成一根根小刺,如刺鰍;有的背鰭被一分為二,比如鱸魚;有的魚的背鰭特化成了尖刺,憑此“仗劍走天涯”。
鯽魚、鯉魚背鰭的第一根鰭條為硬刺,倒刺鲃還長著倒刺。黃顙魚的背鰭和胸鰭都有硬刺,分別朝向三個方向,讓掠食者無從下口, 它們甚至還能振動胸鰭和背鰭上的硬刺彈鋏而歌,發出“嘎嘎嘎”類似鴨子的叫聲,俗稱黃鴨叫。
在眾多魚中,魚鰭較為浮夸的非圓尾斗魚莫屬。“斗魚”的名號,源于它生性好斗的性格。好斗的斗魚多為雄性,它們狹路相逢于“江湖”之中,常為爭配偶、奪地盤、搶食物而大打出手。斗魚常呈現紅藍相間的彩色條紋,正所謂喜怒形于“色”,它們在爭斗時,身體的顏色也會隨之發生變化,這種變化或許也是它們為吸引配偶換上的“盛裝”。魚類皮膚中有著各種顏色的色素細胞,只要改變皮膚中色素細胞的分布,就能為它們換上一身漂亮“衣裳”。
除了“找對象”,魚要想在“江湖”繁衍下去,還需要更多策略。斗魚和蝦虎魚雖然都有護卵行為,卻都不及鳑鲏魚的高明。鳑鲏魚會把卵產在蚌殼上進行孵化,河蚌不僅是鳑鲏的“育兒床”,還是鳑鲏幼崽的“幼兒園”。而河蚌鉤介幼蟲也可鉤在鳑鲏幼崽的身體上,搭個“便車”去遠方,這樣也就解決了河蚌在一處水域繁衍所面臨的饑荒。毋庸置疑,“江湖”之中的弱者需要相互抱團。
這樣看來,每一位水族成員蕩氣回腸的故事,都與這人世間的熙攘紛爭別無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