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彥《星空與半棵樹》對城鄉問題的思考與回答
摘要:陳彥在《星空與半棵樹》中通過新時代農民與返鄉知識分子的在鄉選擇對城鄉問題作出了新的思考與回答。小說主人公對人生道路的選擇由以往的“離鄉”進城尋找生計路徑,轉變成為更好的“返鄉”所以離鄉,主動充當鄉村振興參與者的“在鄉”路徑,主人公道路改變的背后是陳彥對城市形象與鄉村新功能的全面把握。當生活在現代化都市中的人的意義感與歸屬感無法得到確證,鄉村開始承擔“心靈”之鄉的角色,召喚游子的回歸。
關鍵詞:城鄉問題;陳彥;《星空與半棵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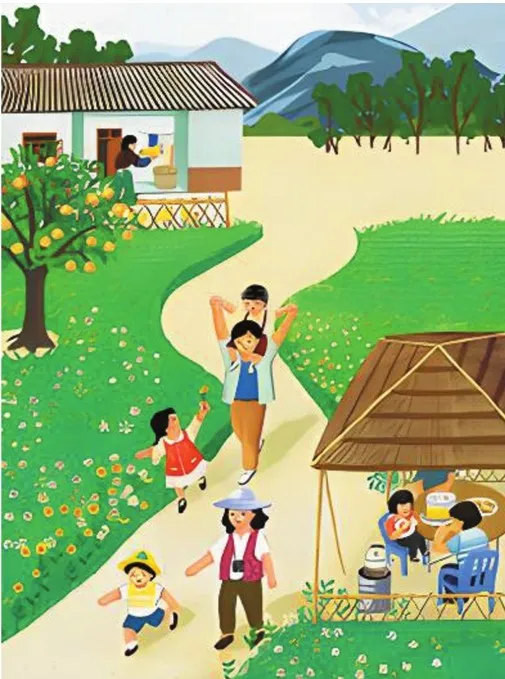
村莊是中國鄉土小說生發的源頭,也是作家成長的精神原鄉。作家之于鄉土的眷戀感與歸屬感,最直接的表現即這一群體對文學村莊的精神皈依。新時代以來,隨著現代化與城鎮化進程的加速,中國鄉村進入劇烈的社會轉型期。現代鄉村的劇變向新世紀鄉土小說創作提出新的要求,以新視野、新思想與新方法表現新的中國故事成為“新鄉土寫作”的基本美學原則,也成為新時代“新鄉土小說”的一個重要判斷標準。近40年的城鄉交往敘事以具象化、日常化、現實化的農民命運書寫,拓寬了“鄉土文學”的審美視域。[1]
陳彥從《西京故事》《裝臺》開始,持續對新時代城鄉巨變中的農民問題給予深切關注,始終注視著時代中小人物的命運,于時代洪流中為小人物立傳,是其不變的創作初心。在新作《星空與半棵樹》中,他一如既往地延續了小說中的平民意識及底層關懷,但在嘗試回答城鄉問題時,陳彥第一次將尋找答案的目光由城市轉移到鄉村,鄉村成為其主要敘事背景。在這部作品中,主人公由以往離開家鄉游離于城市的邊緣人,變成對家鄉建設的主動參與者,新時代的新農民形象躍然于紙上。當城市不再充當農民心中想象的烏托邦,鄉村于農民心中呈現出待建設振興的形象,鄉村的新功能被發掘,新時代農民何去何從、鄉村振興如何進行的問題在小說中得到探索與回答。
一、對城市生活“祛魅”
在《星空與半棵樹》中,陳彥選擇將北斗村作為與城市相比對的空間,即城市隱喻“他鄉”而北斗村暗示“故鄉”。因此,作為寄寓作者懷舊思緒的本體,北斗村的人文自然被賦予了暖色調。小說從離鄉進城鄉下人的個人經驗出發,對城市生活進行了祛魅與還原。將進城的鄉下人對城市的態度分為不同的兩個維度,以溫如風為代表的鄉下人對城市的認知打破以往慣例,呈現出不卑不亢的姿態,而安北斗的前妻楊艷梅、孫鐵錘則延續進城鄉下人固有的對城市生活的羨慕、崇拜心理。陳彥根據這兩類人對城市生活的不同看法,為其安排了不同結局。
小說塑造了一個典型的新農民形象溫如風,他離鄉是為了借助政府權力懲罰家鄉地頭蛇,以保護自己在村莊中抬頭挺胸生活的合法性,由于拒絕了北斗村“地頭蛇”孫鐵錘的權力規訓而受到其欺辱,溫家成了北斗村中的邊緣戶。溫如風選擇由村到鄉鎮,再到省城、京城不斷上訪,期望借助政府的力量改善自己家庭在北斗村中的生存環境。在一路上訪的過程中,溫如風第一次離開了自己從小生長的北斗村,通過溫如風的視角,陳彥展示了城市的多種特質,城市熱鬧精致,但也冷漠疏離,城市只能作為溫如風上訪的暫時停留空間,無法讓其獲得歸屬感。在溫如風看來,城市帶來的不僅是熱鬧,更多的是一種說不出的疲憊和空虛,在城市上訪的過程中,他看見了人們的隔閡、冷漠,在上訪遲遲得不到結果的時候,家鄉就成為溫如風情緒的寄托,他渴望早日上訪成功回到家鄉,渴望家鄉緩慢的生活、原始而融洽的人際關系和寧靜的田園鄉土。在一定程度上,鄉愁鄉思是其城市生活的衍生情感,家鄉與自由自在的生活狀態相關聯,凝結著他幸福的夢與安穩的歸處。
進城的孫鐵錘則與溫如風對城市的看法形成巨大差異,孫鐵錘覺得城市的一切充滿誘惑和吸引力,于是急于將自己包裝成老板,抹去自己農村人的氣質以融入城市生活。奢靡的享樂使其欲望不斷膨脹,為了獲得更多錢財他開始聚眾賭博、謀財害命、欺男霸女……面對家鄉鐵路建設的發展機遇,孫鐵錘利用自己的資源在村中建立公司開山炸石,除了溫如風,村民紛紛選擇加入其公司形成利益共同體,孫鐵錘公司盲目實行的“開山炸石”爆破,讓北斗村中六個無辜村民不幸殞命,他所辦的賭場更讓許多人家破人亡,但孫鐵錘的怪胎式發達,讓整個村的男女老少為了眼前利益唯他馬首是瞻。縱觀整部小說,孫鐵錘是陳彥筆下唯一的“扁平人物”,他貪婪好色,無惡不作且毫不悔改,陳彥為他安排的結局以及對他的批判態度,警醒著讀者對城市生活作出正確判斷,對現代化進程中人的異化問題進行反思。
安北斗前妻楊艷梅的人物形象呈現出雙重矛盾特點。第一重矛盾是生活表面與內里的矛盾。進入城市后,楊艷梅感受著兩種生活。一種是表面的生活,衣食住行光鮮靚麗令人艷羨;另一種是內里的生活,富足外表粉飾著家庭破碎與精神孤獨,這是祛魅和還原后的城市生活。第二重是精神與物質的矛盾,楊艷梅的兩任丈夫安北斗與儲有良分別隱喻著鄉土生活與城市想象。與安北斗在一起,可能要一直待在封閉的北斗鎮,通過儲有良,卻能追逐省城的繁華喧囂,她在精神與物質的選擇中徘徊,最終選擇了儲有良。再婚后卻發現儲有良的政治野心像填不滿的黑洞,“他似乎有無盡的電話要打,不是讓人組織給他投什么票,就是讓人引見他去見什么人。”[2]人心欲望的窟窿永遠填不滿,她無法與儲有良產生精神交流,城市是個功能性較強、生態性不足的地方,“她多少次夢見與安北斗在陽冠山上望星空的日子,可肉體又絕對回不到那個世界去了,盡管在精神上不斷回溯反觀。”她的形象深化了傳統鄉土小說對城市生活的表層書寫,享樂主義與實用主義得到反思,城市的生活不僅僅是穿著高跟鞋跳舞、咖啡屋、時髦衣服與名牌化妝品,還有人生起落跌宕后的平淡寂寞與繁華喧囂背后的煎熬。
通過溫如風、孫鐵錘與楊艷梅的對比,讀者可以看到鄉下人在面對城市誘惑時所作出的不同選擇以及人物各自面臨的問題,陳彥筆下對城市生活的探索從其精致富足的表面到人性異化、精神孤獨的深層,一方面以現代性的眼光看到了現代城市生活的復雜面貌,不再以筆下人物的向城之路當作鄉下人對現代文明追求的唯一途徑;另一方面在情感上表現出對鄉村自然環境與傳統鄰里交往方式的眷念。還原后的城市生活不再令人瘋狂地迷戀,因為建設中的家鄉呼喚著游子的注視。
二、為鄉村功能“賦魅”
時間在《星空與半棵樹》中被隱去,城市與鄉村作為互相聯系的空間清晰浮現,鄉村的新功能被發現,陳彥賦予北斗村一份特殊意義:走向振興的鄉村不應只局限于城市人偶爾消遣尋樂的游逛之處,更可以成為為整個城市人群潛在的身心癥候提供療愈與靈魂喘息的精神出口。這不但為鄉村振興中的經濟建設提供思路,更對鄉村的生態環境保護與文化生態建設提出更高要求。
在《星空與半棵樹》中,村莊內部的環境污染問題、土地拋荒問題、鄉村倫理解構問題,顯然給北斗村的自然風景與人文風景的協調造成了多重悖論。當北斗村在鄉村振興戰略的引領下,獲得經濟復蘇、環境改善、社群倫理關系修復后,其自然風景與人文風景的和諧復歸成為必然的結果。
陳彥將北斗村精神文化生態建設的希望寄托于重新發掘鄉賢文化,刻畫了一個豐滿的鄉賢形象草澤明。中國的鄉土小說一直占據文學史的重要位置,鄉賢文化從晚清到今天從未斷裂,只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發生不同的改變,鄉村治理現代化目標的實現需要鄉賢文化的支持。作品中鄉賢文化敘事始終凝聚著作家對歷史進程中鄉村傳統文化與鄉村治理問題的思考。“這樣的鄉賢敘事,不僅僅是歷史與現實的敘事反映,同時也是以敘事方式參與到中國鄉村精英與鄉賢文化的建構中,以此分擔歷史道路選擇中的迷思與焦慮。”[3]新時代鄉土問題與時代面貌正發生轉變,這需要作家及時發現并調整自己的創作方針。在小說中,民辦教師草澤明出現,這是一個平日如古代隱士般住在遠離北斗村的一個草屋之中的人物,卻會在北斗村人心浮躁、價值失落之際去京城“上訪”,只為推倒村霸孫鐵錘立在村中酷似其爺孫仨人的佛像。草澤明認為,孫鐵錘明明作惡多端卻想讓自己流芳于世,這雕像是對公平正義、道德人倫的敗壞。由閉門不出到主動上訪以守護鄉村的公序良俗,其前后轉變體現出一個鄉間知識分子天然的使命和擔當。借草澤明之轉變,陳彥再次表明了自己寫作的底層關懷——形而上的事情固然偉大,但形而下的每一個生命都值得被珍重。陳彥正是通過這些有血有肉、有愛有恨的小人物悲慘的命運遭際,反映了一個時代的民眾精神,體現出這些平凡人物大雄藏內、至柔顯外的高尚品質。他們生生不息的精神感染著讀者,將讀者的感情無間隙地帶入陳彥的文學世界之中。[4]也只有建立在真實生活之上的人文關懷和道德情感,才是堅實有力的。
風景書寫一直是鄉土文學的重要構成,文學史上以魯迅為代表的五四時期作家曾憑借啟蒙理性的批判目光“發現”了鄉村,以廢名和沈從文為代表的“京派”作家又以詩意的呈現取代文化批判,建構鄉村風景的另一重書寫維度。然而,在“被發現”“被審視”或“被詩化”的過程中,鄉村風景始終是現代作家剖析社會與人性,表達個人情感的中介,是一種背景式的存在。與之相較,新時代的鄉土文學顯然更加注重鄉村風景的獨立價值,并有意識地將之作為重塑鄉土文化空間的重要組成部分,顯示出堅定的文化自信。[5]陳彥對鄉村建設的思考則圍繞北斗鎮10多年間來來往往的三任鎮長南歸雁、藍一方和牛欄山在北斗鎮所實行的經濟發展政策展開。南歸雁在任時,選擇發展旅游業,搞“點亮工程”,又請省上的民俗專家設計了“萬人社火大巡游”,讓本就貧困的北斗鎮財政赤字更加嚴重。南歸雁被調走之后,新上任的鎮長藍一方又開始考慮“新的經濟增長點”,于是讓全鎮鄉民不惜“毀產”也要種甘蔗釀酒,做決策時,沒有考慮鄉民各家釀酒手藝的參差,也沒有提前考慮甘蔗酒的受眾與銷路問題,這種盲目激進的做法迅速暴露弊端,酒釀成后鄉民家家存著三五千斤的酒卻嚴重滯銷。北斗鎮的發展過程忽視了精神文明的建設,更沒有考慮到北斗村自身的優勢,使得村民之間人心渙散、只以各自利益為出發點,鄉土倫理逐漸瓦解,整個村莊的價值認同開始從仁義禮智信向功利時效性轉型,然而急功近利是一切生命的成長瓶頸,社會發展尤其如此,北斗鎮的經濟建設陷入困境。
北斗鎮的振興路徑最終指向了自然文化建設,在現代化進程不斷加快的今天,發現自然的力量,發揮鄉村的獨特功能,即通過保護鄉村生態,讓鄉村未被人為破壞的自然風景成為撫慰人們內心的天然療愈師,通過鄉村獨特的個性發展生態旅游,為生活在城市的人們被物質的壓力和擁擠的交通所裹挾而感到身心俱疲時提供休憩之所。北斗鎮建設路徑的最終轉向由南歸雁的改變體現,南歸雁在經歷數十年的實踐,回永安縣擔任縣委書記時,認真調整方針,選擇了研究北斗村泥石流綜合治理、修復開山炸石的生態環境并解決河流小溪枯水斷流問題,最后從安北斗對星空的癡迷與其建立天文望遠臺的建議中,發現了北斗鎮發展應重視“星空”生態旅游的可持續發展路徑。“此為全書極為重要的一筆,乃是種種矛盾種種問題多個層面復雜交織之后最具觀念和現實意涵的重要選擇,不僅具有總括全書的復雜寓意,亦是足以開出指涉現實且深具實踐意義的重要一維。其所依托之‘自然’觀念,庶幾近乎儒家所論之‘整全生機觀’,即不再將人自外于自然,以‘人力征服’自然而獲得發展,而是將人重新歸入‘自然’之宏闊背景中一并考慮。”[6]
三、“此心安處是吾鄉”
溫如風的上訪作為本書的表面線索,北斗村的建設發展則作為本書的隱形線索,但陳彥在全篇著墨最多的人物卻是安北斗,這一新時代的鄉村知識分子形象匯聚著陳彥對知識分子理想品質的具體想象,通過安北斗,陳彥嘗試回答這樣一個問題:知識分子為什么返鄉?
隨著我國現代化教育改革不斷深化,離鄉學習的青年數量一直增長,這些具備更高文化水平并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越來越多,但最終不能都留在城市中,城市的容量是有限的,鄉村建設同樣需要一部分知識分子回到家鄉,然而在“知識分子返鄉”這一問題上社會層面的公共認同尚未被建立起來。安北斗以大學生身份回到家鄉受到許多人質疑,人們覺得:念了一回大學,最后還是要回到鄉村。似乎讀完大學從城市回到鄉鎮,就會被父老鄉親釘在成功的“恥辱柱”上。這一看法背后濃縮著新時期返鄉知識分子面臨的共同困境,安北斗的形象作為這一時期返鄉大學生的縮影,反映著整個時代的精神困頓。
陳彥在小說中嘗試從精神信仰層面建立知識分子的返鄉認同。小說中描寫了一個全知全能的動物視角——貓頭鷹,它充當了小說中預言家與作者代言人的身份,在北斗鎮的斗轉星移中默默觀察,見證著人類悲歡離合的生命歷程,成為深化小說主題的闡釋點,安北斗則是全篇唯一被貓頭鷹選中的人,是整個敘述過程中的主人公。“代表著浪漫主義、理想主義化身的安北斗,是真正主宰小說光明走向的主角,他是隱藏在整個敘述主體背后的那個牽線人。”[7]
安北斗的在鄉選擇體現出個體對于獨立意識的追求,安北斗常以家鄉的星空為參照思考現實瑣事和人生進退榮辱,他拒絕領導將他調往城市,安心于在鄉鎮基層單位處理細碎繁瑣的工作,腳踏實地地解決家鄉發展中的問題,也會為了天文學知識和夜觀星空廢寢忘食。北斗鎮的鎮長來了又換,有高升的也有被貶的,安北斗卻一直被安排從事看上去窩囊有余但前途不足的“勸訪”工作,面對丈母娘和妻子對他始終待在北斗鎮的不滿與怨懟,他依然選擇認真處理工作瑣事,不卑不亢守在從小生長的土地上,他相信只要“不屈從于任何欲望糾纏撕裂,就活得游刃有余、自由奔放”[8]。在《星空與半棵樹》中,讀者能夠感受到安北斗在復雜社會環境中獨立思考的能力、豐富的精神世界和高尚的價值追求。當今世界,理想主義與個人主義上升,與之相對的是宗教、信仰消退,當上帝消失,世界缺少能夠指導利用技術發現并使之為真正的人類共同體目的服務的道德力量,所以有可能產生人們幾乎難以想象的后果。上帝消失的背后實際是人的情感、價值的失落,當人的勞動的價值被量化、成為理性主義的工具,人最終成為機器一般的人。[9]小說中“星空”的隱喻和安北斗這一具體知識分子形象的存在,正是陳彥呼喚信仰與精神價值在個人人生中存在的意義,我們有理由相信,正是有安北斗這樣懷抱信仰、獨立思考的人,人文主義才不會失落,于是就有了新時代的鄉土小說在私人以及公共層面建立知識分子“返鄉”認同的可能性。返鄉知識青年原本就與鄉土世界血脈相連,他們的逆向流動,不僅意味著城市與鄉村空間的聯通、交疊,更意味著鄉土世界的新變化需要從根本上借助自身內部的力量。由是觀之,農村新人的逆向流動便具有了明確的象征意義,新農村建設的在地性由此得以彰顯。
結 語
陳彥筆下的鄉土形象,在有意摒棄20世紀以來中國社會思想史以西方現代性為價值標準衡量城鄉的范式后,城市的價值體系不再作為走向現代的必然,農村也不再被貼上愚昧、落后、前現代的標簽,鄉村的新功能被發現并以責任與情懷訴說著對游子的召喚,呈現出主動參與建設和改變的歷史姿態。《星空與半棵樹》與時俱進,對正在發生的山鄉巨變、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的新現實進行審美書寫,在這個意義上,《星空與半棵樹》體現出陳彥對新鄉土中國敘事的有效嘗試,小說中的眾多人物的離鄉都是為了最終更好地回到家鄉——無論是為了有尊嚴地在家鄉生活或是為了更好地建設家鄉。棄鄉進城現象不再是城鄉二元問題的必然產物,陳彥以鄉村建設為背景平衡調節了長久以來鄉村人口在陌生的“他鄉”與回不去的故鄉間的矛盾,以豐富深厚的人文眼光思考并嘗試回答著城鄉碰撞的時代性問題。當古典的鄉土文學的家園品質正在遭受城市化的巨大考驗時,文學化的新鄉土敘事正在試圖與市場中國的行程同向同行,產生出警示和價值引領作用。
參考文獻:
[1]張繼紅.論新文學傳統流變中的“鄉土文學”與“新鄉土小說”[J].當代文壇,2021(1).
[2][8]陳彥.星空與半棵樹[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3:640,690.
[3]白現軍.鄉村振興戰略下的鄉賢文化傳承與創新[J].北京社會科學,2021(12).
[4]韓偉.人間·人心·人生:陳彥《裝臺》的三個面相[J].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5).
[5]朱佳寧.“回得去的故鄉”何以可能?——新時代鄉土文學初探[J].創作評譚,2022(6).
[6]楊輝.天何言哉:《星空與半棵樹》中的自然和人[J].南方文壇,2023(5).
[7]丁帆.星空下的黑暗與光明——陳彥《星空與半棵樹》讀札[J].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3(4).
[9]呂西安·戈德曼.隱蔽的上帝[M].蔡鴻濱,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8:42.
單位:西安外國語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