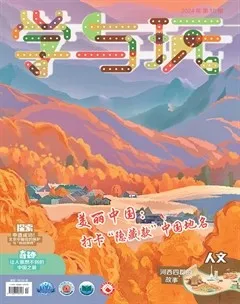閱讀的個人定義
毫無疑問,閱讀是一種純粹的個人行為,是人類這一物種專屬和獨有的精神活動。我對閱讀的個人定義可以用這樣一首小詩來表示:
書本是文字的房屋,文字住在每一本書中,開心地接待每一雙來訪的眼睛。眼睛是心靈的伙伴,文字生出歡樂、陽光和智慧,眼睛用閱讀喂養心靈。書本、文字、眼睛、心靈,像四只嗡嗡的蜜蜂,為你的人生釀造著甜蜜、深邃、開闊,還有每一個小孩子最得意的——聰明。
云南對我而言,就是一個釀造聰明的寶地與福地。從17 歲到27 歲的十年時間,我在云南宜良的大荒田軍營度過,是云南軍營給了我地下閱讀的欣喜、瘋狂閱讀的快樂和饑餓閱讀的欲望。
17 歲的時候,我以一個北京中學生的身份來到陸軍軍營。由于普通話的語言便利,我順利成為炮團的播音員和放映員,也“順便”成為一批封存書籍的管理員。這些書當時不能外借,而我則“近水樓臺先得月”。從儒勒·凡爾納的科幻小說讀起,再到馬克·吐溫、杰克·倫敦和屠格涅夫、普希金、高爾基等作家的著作,還有《先秦文學史》,中國當代詩人從公劉、賀敬之、郭小川到聞捷、張志民……都成為我當時閱讀的“對象”。
我先看小說、后看詩的“程序設計”,是因為18歲時靈感襲來,我寫了一首《號兵之歌》,然后冒冒失失地投稿到云南人民出版社,居然發表出來,并被收錄在了一本名為《云嶺山茶朵朵開》的工農兵詩集里。看到自己的作品變成鉛字,我感覺十分奇特,從此開始了對詩歌如饑似渴的閱讀。就這樣,地下閱讀拓展了我的眼界,瘋狂閱讀打造了我的閱讀速70bd857123f1b13f454b40b4138a8ccf度,而饑餓閱讀(常常是在蚊帳里打著手電筒、頭埋在被窩里的閱讀)使我格外珍惜手頭的每一本書。
十年軍旅,十年閱讀與寫作的練習,造就了我的今天。借此機會,我把自己這段閱讀體驗披露出來,為的是證明一位朋友的話:人生面臨三種風景,一種是自然風景,所以要行萬里路;一種是社會風景,所以要面對人生百態;最后一種是精神風景,那便是書籍和閱讀。讀萬卷書是獲取精神風景的唯一途徑,更為重要的一點是:也許正是由于對三種風景應對自如,逐一實現,最后你也能成為一個制造精神風景的人—— 那就是作家。
我正是借助云南這個“美麗、豐富、神奇的地方”,借助宜良大荒田經營的藏書,也借助對閱讀的熱愛,還有詩歌這一文學最古老的體裁的魔力,才成為一個為孩子寫作(制造精神風景)的人。所以,在此我要感謝軍營,感謝云南,更感謝哺育我青春歲月的一本又一本了不起的經典著作——這些“人類進步的階梯”(高爾基語)。
本文作者系著名兒童文學作家,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七、八、九屆中國作協副主席。本文寫于云南旅次。
(責任編輯:楊懿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