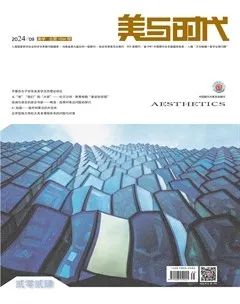是繼續(xù)融合還是分道揚鑣:也談民族聲樂的發(fā)展問題
摘 要:民族聲樂的發(fā)展曾經歷過建國之初“土洋之爭”的陣動,自80年代開始進入與美聲方法論相互融合的快速發(fā)展期,在無數前輩們的共同努力下到2000年左右基本完成了學科理論的構建,其結構體系與美聲方法論基本保持一致。但自2000年田青老師在青歌賽上提出“千人一聲”的質疑到2013年青歌賽賽制取消后,民族聲樂實際已進入審美分裂與技術崩塌的邊緣狀態(tài),民美技術理論的幾十年融合之路已然失敗。那么民族聲樂的發(fā)展是繼續(xù)融合還是分道揚鑣?本文將從美聲方法論非科學性的分析中展開主體性的反思批判,且對民族聲樂進行現象學的分析與跨學科的新路徑探尋。
關鍵詞:民族聲樂;土洋之爭;“主體性”建構;現象學
基金項目:本文系2021年度湖南省教育廳科學研究項目“后青歌賽時代民族聲樂的發(fā)展再研究”(21C0362);2024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學校教學改革研究項目:“跨學科”視野下民族聲樂理論體系的實踐改革研究(202401000937)階段性研究成果。
一、“土洋之爭”的回顧
“土洋之爭”的起點一般認為始于1948年呂驥先生《學習技術與學習西洋的幾個問題》和1949年賀綠汀《關于“洋嗓子”的問題》“呂、賀”之間的非接觸之辯,后隨著馮燦文先生《我對“洋嗓子”問題的一點意見》和張承謨于《記解放劇場〈白毛女〉觀后雜感,并談談“土嗓子”“洋嗓子”的問題》兩篇文章的跟進,發(fā)展成“賀、馮”之間的直接之爭(以下觀點摘自《人民音樂》“土洋之爭”專欄內容)。
站在傳統(tǒng)文化的立場“呂文”認為:
各地民歌的唱法,各種地方戲的唱法,以及各種說唱音樂的唱法和道白,是各各不同的,都具有相當艱難技術……其一般的發(fā)聲方法,聲音的裝飾法,各種不同的音調與音勢的應用法……都是值得我們仔細研究,并且有很多很好的經驗。
每一種技術都是與它所表現的內容密切相關聯(lián)的……表現封建社會生活,產生了昆劇平劇的唱法,表現敵偽時代的東北市民生活就產生了一種所謂流行歌曲的唱法,新民主主義社會就產生了我們的新的唱法,我們的唱法不但不同于前面西種唱法,也不同于表現資本主義社會生活的所謂西洋唱法,難道不是很明顯的嗎?
站在發(fā)展的立場“賀文”認為:
中國的、外國的歌唱家摸索的結果大同小異。外國人已把這些經驗加以科學的分析、整理,成為有系統(tǒng)的訓練聲樂人才的方法。中國大部分還是靠師傅傳授,并沒有系統(tǒng)化、科學化,因之,他們的方法局限性大一些。
一個文藝團體中的職業(yè)歌唱家,必須嚴格訓練自己的聲音,向各方面伸手去豐富自己的音樂知識,提高技術水平。無原則的接受任何遺產固然不好,無原則的反對就會變成固步自封,結果就是永不進步。
藝術究竟不等于政治,新的歌唱藝術是要繼承舊有的歌唱藝術,包括中國的外國的,但把這些遺產硬搬過來歌頌新社會的話,說得不好聽就叫牛頭不對馬嘴;說得好聽一點,是舊瓶裝新酒,這不是新的歌唱藝術。
站在懷疑的角度“馮文”認為:
西洋的歌唱方法是根據西洋的語言而來的,由于西洋的語言與中國不同,決定了它的共鳴位置靠里,中國語言的共鳴位置比較靠外,咬字時嘴也張得大一些,如果用西洋發(fā)聲法的共鳴位置唱中國歌曲,就會使群眾聽不慣,唱不慣,感覺不自然,不親切。用西洋發(fā)聲法的口形唱中國歌曲,就會使得吐字不清。
這些對我們不適合的東西,是我們應該批判的,看不見這些缺點,就會使我們對西洋歌唱技巧盲目的崇拜。
“呂文”堅持認為,中國的民族唱法必須從傳統(tǒng)唱法入手,在堅守傳統(tǒng)演唱特色及優(yōu)點的基礎上去拓展自己的體系和方法,且對西洋美聲唱法下的“洋嗓子”不屑一顧;“賀文”則認為,傳統(tǒng)唱法還沒有形成可靠的學科體系論,因此借鑒西洋美聲唱法的體系對民族聲樂的發(fā)展具有很強的指導性意義;而“馮文”雖然也認為西洋唱法有一定的科學性,但它的方法論體系并非是絕對“科學的”,且不可盲目崇拜,在借鑒的過程中要辯證的看待美聲方法論科學與非科學性,不宜用“拿來主義”的方式進行民族式的改進。在1956年“第一界全國音樂周”后,中西融合成為音樂發(fā)展的主流;進入80年代改革開放后,民族聲樂步入快速的融合發(fā)展期。但西方元音式立美方法論與我們非元音式民族語言發(fā)聲的結構性矛盾并未在西方技術理論的指導下得到真正的解決,特別是學院派歌手演唱民族民間歌曲時發(fā)聲的韻味(不接地氣)明顯不如原生態(tài)歌手的演唱。實際上,青歌賽“千人一聲”審美分裂事件正從技術之爭逐步演變成為文化之爭,且陷入到“是要文化還是要技術”的兩難境地。而幾十年民族聲樂的融合發(fā)展之路面臨著失敗下技術理論崩塌的危機狀態(tài)。這需要我們鼓起勇氣反思融合的根源問題,那就是西方高高在上的美聲方法論就一定是科學的嗎?
二、美聲方法論的質疑:主體性建構
自笛卡爾提出“我思故我在”以來,整個社會思想就進入到西方“人類中心論”。而藝術則衍生為創(chuàng)作主體、實踐表演主體和審美主體三大主體性領域。因此,“主客二分法”的藝術認識論在主觀大于(決定)客觀的必然性中永遠也無法趨于平衡而落入各種矛盾的陷阱。這種矛盾在歌唱藝術中得到最為廣泛而深刻的體現,我們從亞歷山大《訓練歌聲》中就會發(fā)現,“書中所有的歌唱概念皆由‘(各種)’的形式展開。也就是說,只要你認為是科學且正確的歌唱方法皆可在書中找到相反或矛盾的理論支撐,且這些理論皆來自國際專家學者及前輩們的經驗總結。《訓練歌聲》一書可謂真實再現了‘在矛盾中前行’是當代歌唱學理論實踐的最大特征,真與假始終懸而未決,對與錯早已失其意義,實踐是檢驗‘自我真理存在’的唯一標準,主體性的自由決斷橫掃一切”[1]72。另外,我們從亞歷山大《訓練歌聲》一書中還可明見,“現行的所有學科理論皆是歌唱家前輩們依據自我嗓音條件及歌唱經驗總結而來,因遵循著各自文化語言美的境域背景不同以及自我嗓音條件的差異性等因素,其理論的構建就必然會帶有強烈的主體個性與民族性的目標訴求而形成各自不同‘主體間性’(各自民族區(qū)域文化意識形態(tài)的內部認同)的方法論體系,而方法論的差異性必然會造成學科內在矛盾對立理論的普遍性存在”[1]72。至此,各種主觀大于客觀、主體超越本體的知識論體系昭然于世,禁錮著諸多學科的發(fā)展。書中亞歷山大分析了現行學科固有的困難,“難以觀察活著的嗓音器官、主觀本質使人難以進行準確的客觀分析、聆聽的主觀本質、嗓音的個性化發(fā)展”等因素,因此在“矛盾和含糊的概念術語中理論呈現出碎片化的非科學性,在廣泛使用形象化描述替代明確的教導下,歌唱就會落入用幻想去支配歌唱”的陷阱與現實。亞歷山大參考了上百位國際專家學者們的理論和相關研究成果,書中700多個詞條的注釋具有可靠的“歷史性”依據,之所以“所有這類資料的收集和提煉要求詳細,是因為迄今還沒有一部著作是用準確的科學語言記述我們在訓練歌唱嗓音中的知識現狀”。因此,本書只是把“引發(fā)出來的問題和仍存在爭論的疑問匯集到一起將為本行業(yè)或有關方面的研究者提供一些有益的啟示”。也就是說,該書各種相關理論的陳述并非是一種科學性的結論,而是為學科研究的后來者提供的一種資料式的相關參考。當然,我們還可參考《教歌唱》①一書,此書與《訓練歌聲》的觀點一致,亦可證明美聲方法論非科學性的存在。
關鍵是,我們的老師們難道不知道美聲方法論中的非科學性嗎?當然不是。正如馬泰·卡林內斯庫所說:“有一副現代性的面孔叫:媚俗。”因為至今很多人依然堅信:只要是西方的就等于是科學的、先進的。民族聲樂理論的發(fā)展構建,說的好聽點是“民美融合”,然所有相關核心觀點概念均來自西方的理論體系,實則是不分對錯好壞完整版的“拿來主義”。特別是在當今處于社會內部高度和諧的發(fā)展期,各種享樂主義消解著我們內心隱存的矛盾與不安,人們也就不分對錯好壞的在“主體性的占有中”牢牢把控著自我知識占有性的話語權,而任何的懷疑都是對自我存在過往的否定,而任何的否定實際又都是人們對存在于社會“人生追求與價值觀”的自我否定。人們在物質資本與鮮花掌聲雙重“占有性”的綁架下,逃避式“躺平”已成為當前多數聲樂專業(yè)教師們存在的一種新常態(tài),而任何進取式的“否定”或改變都成為一種奢求。正如多邁爾在《主體性的黃昏》中所見,人們在“主體性的占有”下哲學(反思與批判)成為一種可有可無的擺設,這是自我中心論下主體性的最大悲哀。
三、民族聲樂的“現象學”再考察
既然美聲方法論中各種觀點及概念充斥著內在無邏輯的深刻矛盾,那么現行的“以呼吸氣息為基礎,元音式擴展為方法到達語言情感內容為表達的歌唱目標論體系”就只能是妥協(xié)的產物擺了,且并不具備所謂的科學性,而民族聲樂“拿來主義”下的歌唱體系雖然可比肩美聲方法論但同樣蘊含著隨時崩塌的危機,我們可從“現象學的存在論觀點”[2]中去窺探答案。
在胡塞爾的現象學中有兩個核心概念,一是他認可經驗論下知識的“先驗性”,二是我們可根據經驗論中的知識或者體系做“意向性還原”去檢驗(懸置“先驗性”)知識的可靠性或做真理“此在”的揭示。但我們從《訓練歌聲》中已經看出,所有歌唱的先驗性知識都只是“主體間性”的體現,其規(guī)律性也僅限于各自民族文化區(qū)域內部的認同范圍,并不具備普世性的價值觀。特別是當歌唱家們頂著“先驗性”美與審美的光環(huán)閃耀大地,在無數向往目光的匯聚下,各種無關自身條件與語言文化束縛的“意向性還原”實踐行為層出不窮(歌唱中最為普遍的意向性行為:唱美聲就去壓喉,做雄壯聲;唱民歌就提笑肌,找頭腔哼鳴的感覺),在主體性自我占有泛濫與本體嗓音和文化缺失的踐行中,歌唱的三種唱法(美聲、民族、流行)及方法論始終無法統(tǒng)一,且在資本操控與主體性各自需求下走向天經地義的分裂。
實際上,任何的歌唱均可視為是對“作者作品的還原(語言的聲學闡釋)”,是歌唱者用自己的本體聲音去還原創(chuàng)作者的文化產品,而每一次“此在”式的還原實際都是對過往曾經的否定(因為任何一次歌唱呈現的肯定實際又都是對原來的否定),歌唱就呈現出在自我無限否定下的肯定中快樂的成長和發(fā)展著,這里蘊函著阿多諾非同一性下“否定的辯證法”發(fā)展觀。但現實卻又并非如此,我們的學員往往只是簡單的還原了歌唱家或者老師們“先驗性”的形式聲音。他們超越自身的本體條件(因缺失自我本體語言美的訓練步驟和方法,即否定自我本體語言的發(fā)聲條件)、越過作品創(chuàng)作的真實意義(因缺乏文化境域的體驗,很難呈現文化本體語言美的真實意圖),在“本體否定”與“文化非真”的困境中,“意向性還原”就會演變成簡單粗暴的“模仿”,而民族聲樂的“千人一聲”也就淪為“模仿論”下現象級泛濫的必然。
青歌賽“千人一身”的審美分裂事件,表面上看是學院派“科學性”與民間原生態(tài)“非科學性”之爭,但實際上仍是“土洋之爭”的一種延續(xù),只是這種延續(xù)從技術理論轉移到了文化的層面。因為所謂“科學的洋辦法”并沒有從根源上解決我們民族語言發(fā)聲的文化審美問題。現在看來,青歌賽的審美分裂事件本是“文化與技術”激情碰撞融合下提升我們民族聲樂技術理論的一次契機,但最終卻演變成“文化與技術”兩敗俱傷的“游戲”。特別是,我們從當代民間藝人“天籟之音”的傳唱表現中依然可窺到答案,當我們看完“貳強與老丁、云飛與王二妮”的網絡視頻演唱后就會一目了然:他們無視“視唱練耳”歌唱從未跑調,不提“呼吸氣息”聲音連綿不斷,不練“mima元音”韻味飽滿十足,不講“通道腔體”聲音高亢嘹亮。正如小朋友們唱著天使般的歌謠,歌唱原來可以是如此的簡單,只要審美的目標是一致的,那么就有不同路徑到達歌唱“美的彼岸”。而那些所謂的西方技術理論(以呼吸氣息為基礎,以元音式擴展為方法到達語言情感為表達目標的運行體系)就一定是可靠的嗎?答案是否定的,因為他們偏離了我們本體民族語言的習性(語言構成的能動性矛盾:現行的理論以意大利元音式發(fā)聲為基礎,而我們的語言是以非元音發(fā)聲為主),且在“意向性的還原”中“用別人的聲音歌唱著他人的美與不美”已成常態(tài),美早已失去了本真性。而原生態(tài)“天籟之音”的民間歌手們則不同,他們生活本體的語言與歌唱的文化語言始終保持一致,且沒有任何“意向性”的還原干擾,所有的美都充斥著自我民族本體語言的“完整性與自然美”。
四、結語
近年來,在專業(yè)音樂學院內,外國作品演唱的比例越來越高,而中國作品演唱的比例越來越低,這種現象正在向地方高校蔓延。當然這與出國交流的留學生激增和參加一些國際聲樂賽事相關。但如果站在藝術文化的高度來看,我們演唱的主體似乎正在背離我們文化的生活本體,教學區(qū)域內各種外國經典作品的大量傳唱,給人一種置身世外般的幻象,這偏離了我們的文化本質生活。特別是自“青歌賽”取消以來,民族聲樂的生存狀態(tài)愈顯艱難,很多專業(yè)教師和學員都將能演唱外國歌劇選段和作品作為歌唱學習的終極目標,更加大了技術化追求下對自我文化背叛的嫌疑。正如《中國音樂》原常務副主編趙志揚老師所說:“很多時候,美聲唱法好像成了中國聲樂的一個評價標準,甚至在評估價值觀念體系時實際上是拿美聲來套。其實是我們的價值觀念丟了,也就是我們的民族自信心丟了,我們看不到我們的文化豐富和底蘊的深沉……民族聲樂的重要性在于它是民族的時代的最強音,展現著我們國家的形象,我們國家的氣質,我們民族的精氣神。”[3]在這震耳發(fā)聵的警示中回頭再看,西方歌唱理論體系是建立在一二百年前的生理學和物理聲學基礎之上的,當時還沒有現代神經學與物理聲學圖譜的理論出現,就這樣一個充滿矛盾且陳舊腐化的西方技術理論體系卻支撐著我們現代的歌唱文化藝術,難道不值得我們去深思嗎?這不僅是西方技術理論解構(傷害)我們各民族文化領域的一貫伎倆,也是西方文化霸權與資本植入“文化安樂死(讓其他文化在安全快樂中消亡)”的卑劣手段。筆者認為,去媾和一個充滿霸權和陳舊腐化且充滿矛盾與困惑的西方理論,還不如及時分道揚鑣,順應國家“新文科”建設中“學科交叉與融合”的跨學科方式,且在“藝術學理論指導性綱要(2014年提出從藝術審美主體向藝術發(fā)展本體轉向)”的指引下,全面展開西方歌唱技術理論體系的主體性反思與批判,進行自我民族語言文化的本體論路徑探尋與構建。都說安全第一,文化安全也很重要。
注釋:
①伯金.教歌唱[M].肖宇,譯.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03.另:該書還連載于《中國音樂教育》2010年第3期至11期。
參考文獻:
[1]向遵紅,曾麗蓉.重回藝術本體:歌唱語言發(fā)聲態(tài)的本源論路徑探尋[J].美與時代(下),2023(3):70-72.
[2]于潤洋.現代西方音樂哲學導論[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111-113.
[3]白寧.“金鐵霖聲樂教育教學理論與方法研究”學術論壇綜述[J].樂府新聲,2017(4):15-18.
作者簡介:
曾麗蓉,吉首大學音樂舞蹈學院講師。
向遵紅,吉首大學音樂舞蹈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