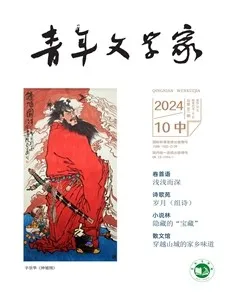故鄉(xiāng)
故鄉(xiāng),是一個(gè)地理概念,是生命最初綻放的地方;故鄉(xiāng),也是一種浸潤(rùn)血液里的深情,一處?kù)`魂的依托。離別日久,對(duì)故鄉(xiāng)的思念,像媽媽做的苦瓜,入口甚苦,品過(guò)后卻回味綿長(zhǎng),放不下。
我的故鄉(xiāng)沖田村,有一千余年的歷史。村子依山傍水,一條大河環(huán)繞大半個(gè)村子,一條古街穿村而過(guò)。古街上連婺源古縣城清華鎮(zhèn),下接瓷都景德鎮(zhèn)。我家在古街東頭路邊。
我家的老房子是前店后居結(jié)構(gòu)。房梁、窗欞、廂房門(mén)格上都雕了花鳥(niǎo)蟲(chóng)魚(yú)或歷史人物之類(lèi)的圖案。20世紀(jì)80年代初,老房子被拆倒重建,再建的是普通的磚木結(jié)構(gòu)房子。據(jù)說(shuō),古時(shí)沖田大路兩邊的人家都是店鋪。我小時(shí)候看到的民房,朝大路這邊都是店堂,杉木條做的門(mén)板墻,類(lèi)似于今天的卷閘門(mén)。開(kāi)店時(shí),門(mén)板可以全部卸下。1949年以后,商業(yè)國(guó)有化,村民的房子成了純粹的民居。
門(mén)口的石板路是孩子們游戲的樂(lè)園。孩子們常在路石齊整、平滑的地方,擺開(kāi)陣勢(shì)“拼殺”起來(lái),或走宮,或擲包。玩得起勁時(shí),人們挑東西路過(guò)都不讓?zhuān)旌诹艘膊换丶摇?/p>
故鄉(xiāng),不光是曾住過(guò)的老房子,也不光是兒時(shí)走過(guò)的路、爬過(guò)的山、游過(guò)的河,還有一代又一代口口相傳的先賢故事和融入血液里的語(yǔ)言方式、行為特點(diǎn)。“鄉(xiāng)音無(wú)改鬢毛衰”的無(wú)奈,“笑問(wèn)客從何處來(lái)”的感嘆,想必每一個(gè)落戶(hù)他鄉(xiāng)的人都會(huì)有。
故鄉(xiāng)的人,故鄉(xiāng)的事,除了熟悉的親人與鄰居,還有一些雖未曾謀面,打小兒便印刻在記憶里的那些人和那些故事。小時(shí)候,在鄰居家聽(tīng)老人講故事,聽(tīng)得最多的就是齊梅麓的故事。他名揚(yáng)徽州六府,從小就很聰明。齊梅麓最露臉的事有兩件:一是他成為“天子門(mén)生”,曾經(jīng)舊祠堂大門(mén)上懸掛有“天子門(mén)生”的匾額,據(jù)說(shuō)是嘉慶皇帝所賜;二是他七歲的時(shí)候就為村子爭(zhēng)了臉,村里大事從此由村里人做主。
相傳,離沖田五里遠(yuǎn)有個(gè)村子叫大塘源,有個(gè)士紳叫李大世。他是當(dāng)時(shí)附近幾個(gè)村子的“大爺”,哪個(gè)村子有什么大事,得由他到場(chǎng)主持拍板。村里請(qǐng)戲班唱戲,得等他點(diǎn)戲,才能鳴鑼開(kāi)演。齊梅麓七歲這一年,沖田又請(qǐng)戲班唱戲。但李大世擺譜兒,遲遲不來(lái)。小齊梅麓說(shuō):“不用李大世點(diǎn),我來(lái)點(diǎn)。”他點(diǎn)了一出《潘洪摘印》。李大世在半道兒的山嶺上,聽(tīng)到?jīng)_田村里的鑼鼓響,驚訝地問(wèn):“我沒(méi)來(lái),誰(shuí)點(diǎn)的?”有人告訴他,是村里小孩兒齊梅麓點(diǎn)的,戲名《潘洪摘印》。李大世感嘆:“雪山高不過(guò)太陽(yáng),沖田出人啦!”然后,他失落地返回大塘源。
這些故事雖沒(méi)記入族譜,但村里大大小小的人,說(shuō)起齊梅麓,都會(huì)說(shuō)起這兩個(gè)故事。在他們看來(lái),這些故事比齊梅麓是一名科學(xué)家、詩(shī)人,更自豪。
村里有位叫齊子望的老人,保存了一套完整的族譜。族譜詳細(xì)地介紹了村子變遷,鄉(xiāng)賢事跡,地方掌故。齊梅麓是族譜里最亮的一顆星,關(guān)于他的事跡記載最為翔實(shí)。三十年前剛參加工作時(shí),我曾拜訪(fǎng)過(guò)子望老人,在他家里看過(guò)族譜,讀過(guò)齊梅麓寫(xiě)的一些策論和詩(shī)文,以及為村里修建館閣寫(xiě)的記文。
改革開(kāi)放后,農(nóng)村生活發(fā)生了巨大變化,勤快的人家很快把老房子扒了,修了新房子。大路兩邊有不少老房子變成了新房子。現(xiàn)在,人們又生起思古懷舊的念想,在新農(nóng)村建設(shè)中,處處融入古典元素。村東路口,矗起一座石牌坊,上刻四個(gè)大字:翀麓古街。古街兩旁舊房子的拆建也被叫停。所剩不多的老房子,則成了旅游資源,常有游子和外地客人來(lái)參觀(guān)。村里修建了“彥槐廣場(chǎng)”。廣場(chǎng)正中安放著齊梅麓雕像,周邊還修建了籃球場(chǎng)和一應(yīng)健身設(shè)施,以及一個(gè)50平方米的表演舞臺(tái)。廣場(chǎng)成了村民娛樂(lè)休閑的好去處。與廣場(chǎng)遙相呼應(yīng)的是村北邊的翀山南麓的“太平窩”,山上修建了步道、亭臺(tái)樓閣,山下修建了龍泉山莊。
清明時(shí),我回到了沖田村,看了看村子,又看了看兒時(shí)常爬的山和常游泳的河。古街的石板路已修整過(guò),墻上還張貼著一些古語(yǔ)和村訓(xùn),這些都讓我感覺(jué)熟悉又陌生。
啊,隨著時(shí)光流逝,故鄉(xiāng)將漸漸化作一個(gè)個(gè)符號(hào),留在記憶深處。
- 青年文學(xué)家的其它文章
- 《殘荷》
- 《漂泊》
- 《海之聲》
- 《青語(yǔ)尚韻》
- 《織·調(diào)》
- 《玉兔東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