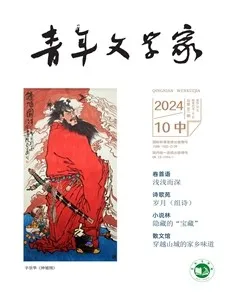韓裕文小傳


在20世紀中國思想文化史上,各種學術流派、思潮互為激蕩,爭鳴不休,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新儒學思潮的興起。自五四運動時,以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為肇端,標志著新儒學思潮的逐漸興起。新儒家學者群體試圖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找思想資源,解答中西文化轉型中所面臨的文化危機。在這些傳統先行探索者中,熊十力的貢獻無疑值得重視。熊十力(1885—1968),號子真,又號漆園老人,湖北黃岡人。熊十力學貫古今,援佛入儒,融攝道釋,創立了一個頗具特色的“心學”哲學體系,并為20世紀新儒家的后續發展培養了不少人才。提起熊十力的弟子,以徐復觀、唐君毅、牟宗三為代表的三巨子最為聲名顯赫,而像劉公純、黃艮庸、韓裕文等其他熊門弟子,則湮沒無聞,鮮為人知。值得一提的是,作為入室弟子的韓裕文,熊十力對其做人治學頗為稱許,并盡力栽培,由哲學編譯會幫助,以自費公助的方式去美國留學。惜天不假年,韓裕文英年早逝,在哲學研究上未盡其才,每念及于此,熊氏輒哀婉痛惜不已,更對韓裕文發出“吾舍汝,其誰望矣”(《十力語要》)之感慨。本文擬通過相關回憶性文字,大致勾勒韓裕文生平經歷及其思想,繼而討論韓裕文求教熊十力的問學點滴,以期學界對此問題有進一步的關注。
一、韓裕文生平述略
韓裕文(1914—1955),字質如,山東濟南萊蕪人。1929年,其畢業于萊蕪初級中學。1934年8月19日,北平《益世報》載,北大本屆新生發榜,共錄取226名,韓裕文添列其中,就讀于北大文學院。在北大就讀期間,韓裕文戛戛獨造,苦心孤詣,在中西哲學方面,浸淫至深。韓裕文和任繼愈、石峻兩位先生是同班同學,任繼愈多年后回憶說:“韓裕文是我在大學的同班同學,為人篤實,學問也樸實,對中國的理學、西方的古典哲學,有很深厚的基礎。”(任繼愈《熊十力先生的為人與治學》)
1938年,韓裕文畢業于北大哲學系,并赴四川繼續求教熊十力,研治佛學與儒學。此時,馬一浮在樂山創辦復性書院,并邀請熊十力一起授課。韓裕文跟隨熊十力同赴復性書院,后因熊、馬二人在治學思路方面發生分歧,加之書院內部人事矛盾叢生,彼此心存芥蒂,熊十力退出書院。韓裕文與熊十力共進退,一起返回璧山縣(今重慶市璧山區)來鳳驛黃家花園暫住。
韓裕文為學篤實,侍師毫無怨言,從無慍色,其尊師之念,維護師說態度之誠,絕無半點兒勉強。這可從徐復觀、唐君毅的兩則回憶材料中得到佐證:“有一次,我和他(指韓裕文)提到熊先生所說的‘超知’的問題,表明我不很贊成之意。他當時便很嚴肅地向我講解了一番,內容我現在已完全忘記。不過在當時我覺得他說得很深切,很能表達熊先生的本意;我才知道他對于熊先生的學問,是實有所得的。”(徐復觀《徐復觀全集:無慚尺布裹頭歸·交往集》)“熊先生當時生活很苦,住在一花園之臺閣中,只有一個床,熊先生睡床,裕文每天晚上便在樓板上睡。我去住三天,亦與他同睡樓板。他除隨熊先生治學外,亦照護熊先生生活上的事。如交信、買菜,都是他的事。我在那住三日,吃飯時有肉食,但裕文卻只吃菜蔬,從不拈肉,因要留給熊先生吃。”(唐君毅《唐君毅全集:哲思輯錄與人物紀念》)
熊十力早年曾在南京的一所佛學院師從歐陽竟無(歐陽漸)研習佛學,尤其在唯識學方面,造詣頗深。其學術生涯中重要的代表性著作《新唯識論》自出版以來,引起馬一浮、湯用彤等學者的高度贊揚。熊十力對《新唯識論》一書中所構建的哲學體系用功至深,曾多次修訂其中內容,以使學界受眾能夠傳播理解。熊十力指導錢學熙將《新唯識論》改寫為語體文本。1939年冬,韓裕文接替錢學熙工作,繼續《新唯識論》改寫工作。經黃艮庸核校,《新唯識論》語體本上卷成稿。
熊十力在治學思辨培養上,對韓裕文甚為苛責,每日方至饑腸轆轆,才可釋卷。然生計日艱,終日難得飽食,韓裕文被迫離開熊十力而為稻粱謀。1942年,賀麟組織成立“中國哲學會西洋哲學名著編譯委員會”,編譯會暫設在西南聯大,韓裕文、樊星南、曹仁和、顧壽觀、陳修齋等青年學者參與其中,據陳修齋回憶,編譯委員會“人員薪資由教育部通過聯大(后為北大)代發,研究編譯員大都借住在聯大的教職員宿舍里,一切待遇也大體與聯大相應的教師一樣”(陳修齋《哲學生涯雜憶》)。在編譯會工作期間,韓裕文與任繼愈等合作譯介B·Rand選編《西洋倫理學名著選輯》;抗戰勝利后,韓裕文相繼任教于西華大學、浙江大學。1947年12月至1948年3月,韓裕文連續在《申報》發表《鮑桑克底美學述要之一:審美經驗的特性》《審美經驗里的心與情:鮑桑克底美學述要之二》《審美底對象:鮑桑克底美學述要之三》《對象的形式與實質:鮑桑克底美學述要之四》《審美之對象與情感之合一:鮑桑克底美學述要之五》《鮑桑克論身心關系》等多篇文章,對英國學者鮑桑克(又譯:鮑桑葵)的美學思想予以翔實介紹。韓裕文也曾翻譯其他學者的作品,但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能夠將他的作品整理出來。
1948年夏,韓裕文由哲學編譯會幫助以自費公助方式赴美留學,在康奈爾大學、伊利諾伊大學等大學研究部,繼續研究哲學。1955年12月18日,韓裕文因患肺癌,在美病逝。唐君毅聞訊后,在日記中寫道:“美某君信,謂韓裕文已逝世,念彼最后一函謂彼不至死,因其尚未對社會他人恩惠加以報答。彼十六年來一直在孤獨中生活,在友人中彼對我為最信賴者,聞其噩耗甚為悲痛。”(唐君毅《唐君毅全集:日記》)
唐君毅致函徐復觀、牟宗三,勸諸人撰作悼念文字,緬懷韓裕文其人其事。韓裕文喪葬諸事,由嚴倚云料理,碑文由胡適撰寫。身旁友人清檢其遺稿,有英文寫作的休謨哲學著作一部,論文若干篇,亦存留日記及寫給友朋信札若干。
韓裕文旅居異國,精神上倍感苦悶,常生孤獨寂寞之感。據唐君毅回憶,二人信札往復所談內容多為哲學問題,韓裕文傾慕古希臘哲學面對自然、人生問題所做的經典思考,對此方面頗下功夫,閱讀了大量原典。韓裕文還自修德語,學習當時流行起來的語義學,對英美經驗主義哲學持保留態度,認為哲學研究應關注現實人生,面對人類生活,以內在而超越的心態去進行思考。作為知己,唐君毅評價韓裕文“是一沉潛篤實而屬于內傾型的人”(《敬悼念亡友韓裕文先生》),很少發表文章,讀書仔細,不輕言著述,與人談話,深自謙抑,性情敦厚,總是居于請益的地位。對于韓裕文治學思想,唐君毅在《敬悼念亡友韓裕文先生》一文中評述云:“他是一真正莫有中西古今之蔽的好學之士,以他的沉潛篤實,他應當是屬于大器晚成的形態的人。”“他的思想以儒學作根柢,大約此數年中其研究學問的方向,仍初是偏在西方之正宗的理想主義傳統哲學方面,由此而附及于西方之宗教思想。”
牟宗三一直寄希望于韓裕文學成歸來,朝夕相聚,共同弘揚儒學。誰料韓裕文一去不返,竟成永訣,徒增凋零傷悲之感。牟宗三認為韓裕文性情狷介,少爽朗之氣,胸懷稍欠豁達,為人處世上頗為拘謹,因此心底有事便放不開,長久積壓,則不免心境悲郁,這也是他不得永年的重要原因。
二、問學熊十力
自1935年起,韓裕文開始求教熊十力,時間跨度達十余年之久。從《十力語要》所存留下來的札記來看,熊十力在個人日常家庭雜事、內心生活等方面,對韓裕文傾吐甚多。例如,熊十力鑒于“民國”時期教育弊于浮雜而成見太深,故深覺閉門著書于事無補,決定以全副精力講學授徒,以維系儒學之道不墜,宣揚先哲之遺訓。要實現講學之愿,熊十力去函韓裕文,告知他有成立一哲學研究所的打算,“冀聚若干有志士得與吾共朝夕,專而不紛,期以數年,精神通,思理達,夫而后此學此道不失其真。斯所以上對千圣百王,下為無量人群廣植善種子,則吾之心盡,而天地生民其亦有所與立、有所與托矣”(《十力語要》)。熊氏深知自己性情孤僻,不擅長人際交往,不想勢利為之,仰人鼻息,面對哲學所經費之籌措,一籌莫展。這些內情都是不為外人所能道及的肺腑之言,而熊氏去函韓裕文,言其苦悶心曲,可見師徒之間情誼之深。
熊十力一再囑咐韓裕文對其《新唯識論》等著述要勤加閱讀體味,對韓裕文在為學取徑方面影響至深。在為學取徑方面,熊十力告誡韓裕文說:“學問之道,于此深造自得,于彼亦可深研;于此粗浮作解,于彼亦是粗浮。粗浮者,即一無所知、一無所得也。汝曹返諸良心,曾受何種嚴格訓練免于粗浮,而遽欲違吾以自立乎?汝非天才也,吾望之者,取其篤實也。”(《十力語要》)
熊氏之論,其精髓在“篤實”二字,希望韓裕文忌粗浮,以平實心面對學問,如此方可有所自得。熊氏進一步強調,治學之要,應以思考開始,然運思過程,非漫無邊際的想入非非,需要通過大量讀書。然讀書,需要沉潛往復,從容含玩,切忌浮泛涉獵。對于讀書過程中所存疑惑,時存心頭,反復思考,方可面對萬事萬物之幽深而產生問題意識,以問題意識為憑借,分析其所立所成之因果,思其所然與所以然,則可有自得之見。然“心之官則思,系于日常實際生活者,情識也,非心也。情識之役于境,是系縛也,不能思也。離系而后能見心。心不為情識所障,而后無不睿也”(《十力語要》)。因此,思考之得要證得本心,以見其理所在。所謂證者,即本體呈現也。學至于證,則本心自明,真理可得。
在辨析儒、佛之異時,熊十力對韓裕文教益頗多。熊十力認為,儒、佛二家之學,推究其本源處,皆歸于明心見性,“誠能見自本性,則日用間恒有主宰,不隨境轉,此則儒佛所大同而不能或異者也”(《十力語要》)。從體用不二的立場看,儒學即用顯體,不是滯于用而不見體。若只談用,則儒學與俗學有何分別?佛家談體,是不生不滅、不動不變,不免有將體用截成二片之嫌。
對于宋明理學之問題,熊十力亦對韓裕文時時點撥。例如,韓裕文問熊十力,“陽明教學者只求明體而不求達用,其末流遂陷于罪惡,何耶?”(《十力語要》)熊十力認為,良知乃為心之本體,是一切知識之源,但若內守而不推致此良知于事物上去,即缺乏辨物明理的知識。而此一念之間,未經磨煉亦靠不住,乃任意見而起弊,亦即以意見為天理。在教韓裕文宋明理學本體論知識時,熊十力認為理學家以靜屬體,以動屬用,此問題值得一辨。熊氏辨析說,體自是靜的,但也不能說它是凝固不動的物事。如果無動,如何顯現為大用流行。用是動的,但也不能是囂然浮動的物事。如此,則體不能成用之體,如何講得通?最恰切的理解是:“吾人于用上而識其本體,則知用之相雖是變動不居,而用之體畢竟真常寂靜。所以就用上說雖是動的,而確是即動即靜的。驗之吾心,當動應萬端時,原自湛然虛靜,此理豈待外求?”(《十力語要》)
對于20世紀上半葉儒學史研究而言,其所依托的科舉制度被停廢后,傳統“經史子集”的四部分類被打破以來,儒學被文史哲所劃分的學科門類分割,衍生出不同的專史方向。后來者治儒學史者,在聚焦主流學者學術思想及其經典文本的深究方面,取得成果累累,然多集中在某個斷代或某一固定典籍之中,以作為其畢生努力方向,難窺經學之全貌。尤其對儒學源流、損益演變之跡,難以整體貫通深入,所得流于浮泛者,比比皆是。除關注名入史冊的儒者外,對于隱入歷史塵埃中的非主流學者,學界無論在文獻整理,還是學術思想闡釋上,尚未得到充分重視,亦有進一步思索的空間。
像韓裕文這樣的學者,在20世紀上半葉的儒學史系譜中扮演的是一位居學術邊緣的角色,其人其學,隱沒不彰。若我們轉換研究視角,眼光向下,將韓裕文視作中下層邊緣儒家學者群體的典型代表,專門關注這類學者群體文獻的搜集、整理及研究,思索他們在20世紀上半葉的群體哲思成就,則無疑會擴充20世紀儒學史研究視域。以韓裕文為媒介,從學術理路層面來看,我們不僅要留意剖析這類群體學者的思想內源,還要關注他們思考的儒學議題、學術交往等。尤其是這類學者群體的時代思考,業已滲入歷史思想的潛流,被后來書寫機制所遮蔽,資料分散難尋,生平蹤跡難覓,如何返回當時思想語境,思考他們的思慮關懷、人生境遇、著述心得等,似是后來者應努力的一個方向。從更為廣闊的儒學學術生態環境而言,將這類學者群體置放于當時社會生活話語體系里,注意他們的思想與時代的互動,邊緣與主流的交光互影,新潮與舊學的對話,中西哲思互為闡發的影響等,亦是未來可值得考察的一個學術視點。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西部和邊疆地區青年基金項目“徐復觀年譜”(項目編號:23XJC720004)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