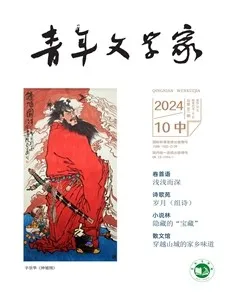鄉村振興:以詩歌的形式回應新時代文藝思潮

詩歌作為文學創作的重要體裁之一,其對時代話語的在場性表達始終都是文學書寫時代不可缺少的聲音。王單單的詩集《花鹿坪手記》是以詩歌形式回應新時代鄉村振興文藝思潮的典范之作。本文擬以詩集《花鹿坪手記》為例,從詩境、詩情、詩藝三個方面對新時代鄉村振興題材詩歌創作作具體論述,并在此基礎上,重點分析鄉村振興題材詩歌創作的時代價值,以及目前存在的問題。
一、鄉村振興語境下的詩歌創作
海德格爾曾提出過“詩人何為”(海德格爾《詩人何為》)這樣一個引人深思的命題,以此來強調詩人歌唱時代的使命與擔當。他認為詩人作為“潛入黑夜”的“冒險者”,其職權和天職出于時代的貧困而首先應該成為詩人詩意的追問。因此,在鄉村振興這股聲勢浩大的文藝思潮中,詩歌自然不會缺席,其對時代話語的在場性表達始終都是新時代鄉村振興題材文學創作書寫時代的重要版圖之一。
“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費孝通《鄉土中國》)鄉土文學與鄉土中國密切相關,且有著龐大的脈絡。從劉大白的《賣布謠》到臧克家的《難民》,再到艾青的《我愛這土地》,鄉土詩作為鄉土文學脈絡的一部分,一直都在以詩意情懷書寫鄉土大地。雖然1949年以后的許多鄉土詩僅從“題材”層面對生活作時效性反映,但20世紀80年代伊始,新邊塞詩和新鄉土詩的出現,昭示著詩歌在鄉土書寫的長河中尋找精神家園的努力。新時代以來的鄉村振興題材詩歌,作為鄉土詩在新時代的延續,有著屬于鄉村振興語境的特點。它們力求通過貼近現實的書寫,來揭示鄉村振興發展與鄉土傳統性之間的平衡,其中延續的鄉愁和煥發的精神力量,則表現著鄉村在中國式現代化發展過程中的存在形態。被評論家王士強稱為“主旋律寫作樣本”的《花鹿坪手記》,很好地體現了“大”與“小”的辯證統一,詩人沒有因鄉村振興這一時代大主題而拋棄自己的形式,也沒有被響徹其中的歡呼完全同化了自己的聲音。他投身云南“花鹿坪村”這一鄉村大地的一隅,將鄉村振興的時代大背景具化為生動鮮活的小細節,在一個又一個有血有肉的生活形象中延續著宏闊的新鄉村想象。
二、《花鹿坪手記》:詩歌介入現實的努力
與以往的鄉村詩意書寫不同,《花鹿坪手記》這部誕生于鄉村振興語境下的詩集,是王單單作為駐村扶貧隊員的親歷見證,不僅保留了他寫作鄉村詩歌特有的靈氣,還激活了鄉村振興戰略和鄉村詩意之間的關聯。
(一)詩境:再現安放鄉愁的精神原鄉
《花鹿坪手記》以鄉村變遷為主線,涉及花鹿坪村的方方面面。王單單通過對鄉村環境變遷的記錄和對鄉村情境的建構再現了花鹿坪村在脫貧和振興過程中的深刻變革。在這個過程中,王單單融入了自己切身的生命體驗,以宛若家鄉的花鹿坪村為原型再現了安放自己鄉愁的精神原鄉。
1.鄉村環境變遷
王單單對花鹿坪村這一精神原鄉形象的塑造,是通過“博物志”式的書寫展開的。詩人耐心而深情地細數著花鹿坪村的細枝末節,甚至專設《花鹿坪風物譜》一輯來展現鄉村的美麗,諸如早春時壓滿枝頭的梨花(《早春》),暮春時漫山遍野的蘋果花和遍地瘋長的野草(《暮春之初》),月上柳梢和蟬聲止息的寂靜黃昏(《黃昏記》)……這種對鄉土大地的審美發現,昭示著鄉村美感已彌漫于鄉土自然的每一個角落,不經意間便可被發現。除此之外,《花鹿坪手記》還將在鄉村振興過程中作為背景存在的“碎片式”鄉土景色用詩歌串聯起來,使其“完整圖像化”。由此,幽美靜泊的詩境隨之出現,鄉村振興變成了詩意的現場。王單單借助這一詩境,喚起的是人們對鄉土之美的記憶。其意在表明,鄉村不只有“泥滋味”和“土氣息”,天然的美麗使它本就有被振興的價值。與自然風光同在的是并不理想的人居環境,通過對其變化的書寫,鄉村振興的成果得以具象化。從坑洼泥濘的土路到平坦硬化的公路,從破舊的土屋到嶄新的樓房,從垃圾遍地到干凈整潔……位于大地褶皺中的花鹿坪村沐浴在鄉村振興的陽光下,煥發了新的生機。
2.鄉村情境建構
柄谷行人在《風景之發現》中認為,風景乃是一種認識性的裝置,它被發現、被意識從而進入審美視野的過程,緊密關聯著主體觀照世界的方式。與鄉村環境變遷一起被納入“博物觀照”視野的,還有花鹿坪的“人”。詩人在創作過程中最大程度地調動自我感情,將個體命運和人際關系組合成以鄉村情境為表現形式的藝術體系,以此來提高詩歌的審美品質。
在《花鹿坪群像圖》一輯中,詩人描寫了各種人物的生存狀態和精神面貌,諸如不忍殺羊的牧羊人(《冬至》)、從容堅毅的補瓦人(《補瓦記》)、舍己為人的老黨員羅澤新(《老黨員》)等。王單單欣慰于他們身上閃爍的美德和點滴的進步,卻也為他們身處其中而不自知的惰性和愚昧感到焦慮。他在《融化記》中耐心勸說不修牛圈的養牛人,在《激發帖》中訓斥懶漢,在《村中巡記》中勸返輟學打工的女孩……這些獨具個性的村民,如同大地上堅韌生長著的一切,潦草而又神圣。除此之外,鄉村振興過程中也伴隨著各種各樣的問題,如易地搬遷、故土難離、疾病纏身、空巢老人、留守兒童、基礎設施改善等。王單單扎根花鹿坪村,又跳出花鹿坪村,他把花鹿坪村的變遷過程看作是整個中國大地變革的縮影,從側面折射出了時代的波瀾壯闊。王單單曾在《詩歌作伴好還鄉》中直言,希望在詩歌中找到屬于自己的村莊,為期兩年的扶貧實踐,他見證了花鹿坪村的變遷,花鹿坪村也因此變成了凝聚著他情感的家園,成為他安放鄉愁的精神原鄉。
(二)詩情:回望原鄉形象的人文關懷
從文學發生學的角度來看,寫作《花鹿坪手記》的過程其實也是王單單和花鹿坪村的一次互相發現。詩人扎根鄉村,用生命來體悟花鹿坪村的一草一木,而花鹿坪村善良淳樸的村民也溫暖了他的人生。
《花鹿坪手記》寫盡了人生百態。在《放牛郎》中,他贊美把牛看得比人還金貴的“放牛郎”;《花鹿坪手記(二)》里,他感動于依偎稻草人睡著的老寡婦陳石芳;他共情于《慈母》里為給兒子減負而去蘋果園打零工的六十二歲老人……詩人懷著深厚的情感,帶著對世事人情的體諒,將一個人的命運娓娓道來。然而,好的主題詩歌創作,是會從“小我”走向“大我”,由“個人性”上升到“時代性”的。在《新時代》《花鹿坪變遷帖》這樣充滿正能量的詩中,我們可以看到詩人視野境界的升華。在《假如沒有扶貧》中,詩人從脫貧民眾的小人生中看到了扶貧工作兼濟天下的大慈悲,“假如沒有扶貧,再富強的國家/失卻兼濟天下的慈悲,也只是徒有虛名”。在《中國民工》里,他以“時代的英雄”致敬鄉村建設工作的參與者,響應了“人民是真正的英雄”的論斷。面對鄉村振興這樣的時代變革,來自鄉村的詩人熱情地投身其中,以深厚的人文關懷建構了詩人“在場”的詩歌價值體系。
(三)詩藝:詩性敘事的創造性表達
為了建構“花鹿坪村變遷史”這座整體建筑,王單單在《花鹿坪手記》中延續了自詩集《山岡詩稿》開始就一直堅持的敘事性寫作手法,并賦予了這一手法新的變奏。在《花鹿坪手記》中,散點透視變成了整體建筑,花鹿坪村鮮活又散亂的故事被整合成了詩的經驗,呈現出個體之和大于整體的詩美效果。
王單單在這部詩集中一改之前單向凝視的寫法,他將目光聚焦于留守兒童、老黨員、殘障人士等村民的同時,也在自我反視。他借花鹿坪村民的困頓與勞苦來寫自己的父輩,在群體聚焦中發酵詩意。通過對花鹿坪群像的描繪,一種在國家意識形態背景下建立個人話語的歷史意識在王單單的詩里成長起來。以此為統攝,王單單恰到好處地處理了敘事與抒情之間的辯證關系,使其呈現為“由敘事抵達抒情”的路徑。例如,《種子》一詩,整首詩都在講李三元曬茄子的方法,直到最后才點出種茄子的目的“李三元拿去集鎮上賣了/換成妻子的藥錢”,此刻詩歌不再清淡如水,而是飽含著李三元家的辛酸與不屈。經這兩句反推前文,詩歌開頭“土墻上掛著一個茄子/被風吹著,蕩來蕩去”和“把茄子從內部撐開/以便陽光照進去”在單純敘事之外,也將“茄子”和李三元家的生存狀態聯系在了一起。同樣,在《花鹿坪手記(二)》中,詩人身上的泥土卻是“小小的誤會”,其中“藏著蒼天/巨大的慈悲”。這本詩集大部分都是這樣以事傳情的書寫,據此,吳思敬在《找到屬于自己的村莊—王單單詩集〈花鹿坪手記〉序》中指出,王單單所秉持的敘事原則是一種詩性的敘事,這種敘事并不以全面完整地講述一個故事或塑造一個人物為目的,而是透過現實生活中捕捉到的某一瞬間,因此來展示詩人對事物觀察的角度和某種體悟,從而達到對現實生存狀態的揭示。
三、以詩歌形式書寫鄉村振興歷史進程的時代價值與存在問題
回望新詩歷史,每一次時代的變革都會使詩歌的面貌發生變化。在此次鄉村振興的浪潮中,以《花鹿坪手記》為代表的鄉村振興題材詩歌創作通過詩人個體和國家整體的對話彰顯了詩人的“在場性”,為鄉村振興實踐注入了詩意力量。
(一)為鄉村振興實踐注入詩意力量
以《花鹿坪手記》為代表的鄉村振興題材詩歌以文鑄魂、以文興業,將詩歌的詩意之美灑在了鄉土大地上。新時代鄉村振興題材詩歌創作“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從鄉村環境和生活情景出發來構造詩境,記錄著詩人身處其中的真情實感。此時,鄉愁不再只是知識精英站在啟蒙視角上俯視鄉土中國的代名詞,而是詩人以“貼著地面飛行”的方式為變化著的鄉土大地揮灑下的詩意,這是一種內在的生命體驗,真實而又深切。新時代鄉村振興題材詩歌作為審美特性與政治功用的結合,是詩人群體對時代主流話語詢喚的回應,這展現了詩人想象時代共同體的現實主義精神。其中,詩人對時代共同體的想象主要有以下特征:第一,鄉村振興既是振興鄉村也是想象鄉村的過程,這個過程需要詩歌將這一基于現實的想象過程描繪出來。第二,詩歌想象時代共同體的努力,體現了詩人以詩歌介入現實的文學觀。第三,鄉村振興在當下并不是完成時,而是現在進行時。詩人不僅要忠實地記錄這一歷史進程,還要對其進行個體的展望。
總體來看,新時代鄉村振興題材詩歌創作作為詩人在時代回響中建立起來的精神化現實,在詩學和社會學的深度對話中激活了詩人的感物能力和現實精神,其最終意欲達成的是以詩歌之“真”為呈現形式的“詩性正義”。
(二)“同質化”的整體創作傾向和缺乏精神升華的淺表敘事
就目前而言,現有的鄉村振興題材詩歌創作已然在助力時代意識形態宣傳的過程中,凸顯了中國政策的優勢。但“同質化”和缺乏精神升華的淺表敘事的創作傾向,仍是目前大多數鄉村振興題材詩歌創作的弊病。鄉村振興實踐的實施手段和理想目標都是在國家的統一號召之下進行的,作家面對相似的過程難免會遇到“同質化”的問題。所以,盡管該題材詩歌創作數量不少,但優秀詩歌卻不多,大多都流于概念化、模式化。由于一些詩人對鄉村振興政策的認識還不深刻,往往看不到鄉村變遷背后的本質,因此當下鄉村振興題材詩歌敘事仍停留在淺層,缺乏打動世界讀者的力量。鄉村振興作為國家行動,其意義不言自明。但文學書寫和政治實踐的結合,始終存在著一些無法忽視的先天性悖論。主題詩歌創作往往變成“唯主題”詩歌,個體性、文學性在突出“主題”創作的同時很容易被政治性、社會性所取代。即便是《花鹿坪手記》這樣的佳作,也難免存在著語言過于生活化的問題。
新時代鄉村振興題材詩歌創作作為新鄉土文學思潮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鄉村振興語境之下,也在努力以自己的方式為鄉村振興打造詩意現場。然而,面對目前“同質化”和缺乏精神升華的淺表敘事的創作傾向,詩人應重新思考詩歌創作和時代精神表達之間的關系。當“同質化”成為主題詩歌創作脫不開的魔咒,王單單選擇投身于實踐,以真實體驗來增強自身的“造血”功能,從而創作出了鄉村振興題材詩歌佳作—《花鹿坪手記》。這對處于“同質化”困局的鄉村振興詩歌創作而言,無疑具有普遍意義。
詩人與時代的關系絕不是直線式的簡單書寫,在時代的多棱鏡中他們有著更為復雜的呈現。新時代詩人不能唯題材創作,而應該在審視社會景觀嬗變的同時,回到詩歌本體性和個人主體性的本質上來,以文學性的方式將時代和現實轉化為具有獨創性的審美經驗。鄉村振興不僅是中國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大事,對于全世界人類的生存與發展同樣具有深刻的意義。如何寫出具有人類共情性的鄉村振興題材詩歌,讓詩歌始終在場,這對當代詩人來說是一個艱巨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