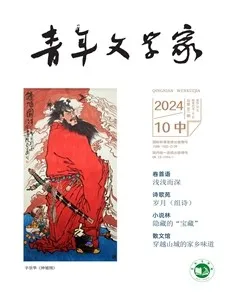先秦和兩漢“玄鳥生商”神話的文化闡釋

“玄鳥生商”神話是講述商民族始祖契的誕生與玄鳥的神秘聯系的感生神話,關于該神話的文獻記載十分豐富,其中尤以先秦和兩漢的傳世文獻最為典型,后世關于該神話的各種闡釋均出于此。
一、先秦時期的神話敘事
作為感生神話的代表,“玄鳥生商”神話最早見于《詩經·商頌·玄鳥》,“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此句講述了商族始祖契的誕生與玄鳥的神秘聯系,帶有明顯的神話色彩。在早期社會,人類的思考無法脫離具體實物而單獨存在,故將各類無法解釋的現象加以形象化,由此萌發了萬物有靈觀和視動植物為親族的圖騰意識。“玄鳥生商”神話即誕生于這種原始的圖騰意識。
圖騰既是一種社會文化形態,也是原始宗教的基本形式。圖騰崇拜觀念的物質形態為圖騰物,先民供奉自身氏族的圖騰物以求庇護。玄鳥是商族的圖騰,商人將自身感生的起點寄托于玄鳥,體現了其民族的圖騰崇拜與天命信仰。《說文解字》釋“玄”為“幽遠也”,《廣雅·釋言》釋“玄”為“遠也”,二者都可以說是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商人的宇宙觀念。
春秋戰國時期,“玄鳥生商”的神話在多地流傳,得到了不同的闡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簡《子羔》篇記載了孔子向弟子子羔講述三代始祖的誕生神話,在提及契的誕生時,有言:
子羔問于孔子曰:“三王者之作也,皆人子也,而其父賤而不足稱也與?殹亦誠天子也與?”孔子曰:“……卨(契)之母,有廼氏之女也,游于央臺之上,有燕銜卵而措諸其前,取而吞之,娠三年而畫于膺,生乃呼曰‘欽’,是卨(契)也。”
《子羔》篇詳細記載了商族始祖契的誕生過程,感生者為有廼氏之女,感生物為燕卵,已經具備了相對完整的故事情節。在感生神話體系中,感生后代的父親則往往被模糊乃至忽略,從中可以看到母系氏族社會中女性本位的思想價值觀念以及原始社會中以女性為中心的權利意識結構的遺留。從子羔向孔子的發問中也可知,到了戰國時期,生育并不是一件神秘的事,子羔發出三王究竟是“人子”還是“天子”的疑問,這堪稱漢代學者討論契是“有父而生”還是“無父感生”的開始。
《子羔》篇將“玄鳥”釋為“燕子”,是最早將“玄鳥”釋為“燕子”的傳世文獻。取吞燕卵的感生方式是感生者與感生物完成結合而受孕的必要行動,趙國華的《生殖崇拜文化論》曾提到:“吃食物可以生出乳汁,吃食物當然也可以生出孩子,這是初民的邏輯。所以,他們將食服務于生殖。”這不僅是圖騰崇拜的反映,也是原始社會生殖崇拜思想的反映。
孔傳在釋《尚書·堯典》“欽明文思安安”時云“欽,敬也”,“欽”字表示敬重與恭謹,商始祖契生而呼此字,可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權力意識結構的變動對“玄鳥生商”感生神話闡釋的影響。殷周易代以來,周人提倡從神治走向人治,強調道德在統治中的重要作用,這種道德本位價值觀最終也影響到了感生神話的闡釋。
戰國時期對“玄鳥生商”神話的闡釋發生了一定變異。屈原《離騷》中有“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氏之佚女”“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天問》言“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結合起來可以發現,屈原將“玄鳥”釋為了“鳳凰”,也最早提及了契父契母的名字,帝嚳高辛氏和簡狄。從《天問》的疑問中不難看出,屈原也對契是“有父而生”還是“無父而生”提出了質疑。在早期的神話中,各民族的始祖往往是在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情況下誕生的,而隨著父系氏族社會的形成和血統的建立,人們更多地注意到了始祖之父。《大戴禮記·帝系》中記載:“帝嚳卜其四妃之子,而皆有天下……次妃,有娀氏之女也,曰簡狄氏,產契……”該記載已初見帝系神話形成的端倪,神話就在帝系血緣的滲透中逐步走向理性化、歷史化。但在屈原的描述中,神話色彩并沒有完全褪去,如簡狄在瑤臺的描述,很明顯地將其塑造為了神女的形象,簡狄與帝嚳的結合也與楚地流行的人神戀愛故事相契合。
在《呂氏春秋·季夏紀·音初》中,簡狄的神女形象則更加飽滿:
有娀氏有二佚女,為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為北音。
《呂氏春秋》關于玄鳥的記載故事性更強,神話色彩更為濃厚,情節也有增添。感生地是“九成之臺”,即九天之臺,將感生地設為此,是將有娀氏所處之地作為溝通天、地、人的媒介,賦予了有娀氏神女形象。“飲食必以鼓”的記載也和我國古代以歌舞娛神的思想觀念相聯系,楚文化信巫鬼、重淫祀,歌舞往往和祭祀相聯系,是祭祀活動取悅神靈的必備環節。在情節上,《呂氏春秋》中的記載突出了帝的地位,從中可看出“玄鳥生商”神話的內核對象從圖騰玄鳥本身轉移到商族始祖。
二、兩漢時期神話的歷史化敘事
在兩漢的文化背景下,“玄鳥生商”神話的闡釋得到了新的發展,也發生了變異。西漢時期簡牘殘亂訛脫,學者不得其本意,老儒生便憑借記憶口耳相傳,用漢代通行的隸書體抄錄經典,從而誕生了今文經學。古文經學興起自漢武帝末年,魯恭王于孔子舊宅發現《尚書》等數十篇用籀文寫成的古文獻。西漢后期,社會矛盾尖銳,出于鞏固政權統治的需求,讖緯之學興起,至東漢發展至鼎盛。今古文經學之爭貫穿整個東漢。面對這種僵持爭斗的局面,鄭玄試圖融合今古文經學,以古文為宗,兼采今文,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今古文經學的融合滲透。在這樣豐富復雜的學術思想背景下,“玄鳥生商”神話得到了更加豐富、多樣化的闡釋。
(一)今文經學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提出:“謂契母吞玄鳥卵生契,契先發于胸。性長于人倫。……知殷之德陽德也,故以子為姓……”認為古代的神圣帝王都是受天命而稱王的,由此,董仲舒構建了“君權神授”的理論體系,為封建社會的政治統治奠定了基礎。從中也可以看出,以董仲舒為代表的今文經學學者主張契的誕生方式為“無父感生”。關于上古感生神話認知的分歧恰恰是區分今古文經學的一個重要標志,許慎《五經異義》云:“《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圣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左氏說:‘圣人皆有父。’”今文學說主張圣人是“無父感生”,以《春秋左氏傳》為代表的古文經學則主張“圣人皆有父”。
然而,圣人是“無父感生”的說法終究帶有濃厚的神話色彩,因此主張“實錄”歷史的司馬遷在《史記·殷本紀》中對該神話進行了改造:“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這段敘述中,契雖然依舊是簡狄吞玄鳥卵而生,但司馬遷特意強調了契父帝嚳的存在,兼采“感天而生”和“有父而生”兩種說法。契母簡狄不再是位于“九成之臺”的神女,而是帝嚳的次妃,身上的神性幾乎完全喪失。司馬遷的敘述有意淡化神話色彩,對殷商始祖感生神話進行歷史化的敘述,體現了神話敘事與歷史敘事的結合。
在《史記·三代世表》中,褚先生和張夫子的討論進一步佐證了司馬遷的觀點。在《詩經》中契、后稷“無父而生”與傳記記載中“有父而生”的說法存在矛盾這一問題上,褚先生回答“鬼神不能自成,須人而生,奈何無父而生乎!”充分肯定了“有父感生”的觀點。
(二)古文經學
《毛傳》對“玄鳥生商”的闡釋代表了古文經學的觀點。對于《詩經·商頌·玄鳥》,毛注云:“玄鳥,鳦也。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毛傳》從訓詁的角度釋“玄鳥”為“鳦”,實際上“鳦”即是燕子的別稱,《爾雅·釋鳥》有“燕燕,鳦”,郭璞注“一名玄鳥,齊人呼鳦”。
《毛傳》記載的“玄鳥生商”神話遠不同于前人,最早主張郊禖說,即簡狄與高辛氏在玄鳥到來的春分時節于郊禖祭祀生契。《禮記》曰:“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高禖是一種在玄鳥至日舉行、以祈求生育為目的的祭祀活動。《毛傳》認為簡狄并非吞卵感生生契,而只是參加了與生育相關的郊禖之禮,徹底瓦解了神話敘事,這是對以往“玄鳥生商”闡釋的一大突破。同時,《毛傳》也明確言及高辛氏為契之父,《史記·五帝本紀》曰:“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這種觀點強調血統的一脈傳承,完成了從圖騰崇拜到祖先崇拜的過渡,建構了完整的帝系神話脈絡體系。
《毛傳》中的見解也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后世解讀該神話時多援引郊禖說,如《竹書紀年·殷商成湯》中的“初,高辛氏之世妃曰簡狄,以春分玄鳥至之日,從帝祀郊禖”,即是繼承了《毛傳》的高禖說。
(三)讖緯學說
關于漢代讖緯學說,劉師培曾提到:“夫讖緯之書,雖間有資于經術,然支離怪誕,雖愚者亦察其非,而漢廷深信不疑者,不過援緯書之說,以驗帝王受命之真而使之服從命令爾。”(《國學發微》)緯學家們繼承今文經學的五行天命論和天人感應思想來解讀經典,以此來為政治統治者服務,增強其統治的合法性。
關于陰陽五行的界定和劃分,先秦兩漢有多種多樣不同的說法,鄒衍在前人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五德終始說,即“土德后,木德繼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文選·魏都賦》),以土、木、金、火、水為次序周而復始、循環往復,并將此順序作為歷史變遷的依據。按照該觀點,商為水德,《史記·三代世表》云:“湯之先為契,無父而生。契母與姊妹浴于玄丘水,有燕銜卵墜之,契母得,故含之,誤吞之,即生契。”《尚書中候》言:“玄鳥翔水遺卵,娀簡易拾吞,生契,封商,后萌水易。”這些關于“玄鳥生商”的記載都與水有關,遠不同于前人提到的“簡狄在臺”,可見五德終始說對“玄鳥生商”神話闡釋的影響。
(四)通經之學
鄭玄是兩漢經學的集大成者,其在注解《玄鳥》一篇時云:“天使鳦下而生商者,謂鳦遺卵,娀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此處顯然是從今文經學的說法,圣人無父,感天而生。但在描寫另一則姜嫄履大人跡生后稷的感生神話中,鄭玄則注云:“姜嫄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禋祀上帝于郊禖。”明顯受到郊禖說影響,是從古文經學的觀點。可見鄭玄注意到了兩種觀念的矛盾之處,希圖調和二者之間的矛盾差異。他曾與古文經學大師許慎進行學術論爭,作《駁五經異義》云:
諸言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謂娀簡吞鳦子生契,是圣人感生見于經之明文。劉媼是漢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神而生者也?
鄭玄認為“有父不感生”的觀點屬于偏見之說,有父和無父并不是區分是否感生的依據,有父亦可感生。
“玄鳥生商”神話的闡釋受到歷史、文化語境等因素的影響,同時也體現了不同時代的歷史和文化特點。在先秦時期,對“玄鳥生商”神話的建構體現了以生殖繁衍為目的的價值導向,神話性質不斷加強,內容逐漸完備。漢代對“玄鳥生商”神話的闡釋深受經學思想的影響,在帝系神話的滲透中逐步走向歷史化、理性化,帶有為政治統治服務的傾向。先秦兩漢時期的對“玄鳥生商”豐富多樣的闡釋基本奠定了其神話內涵,后世對這一神話的闡釋多不出《毛傳》《鄭箋》之說。例如,“孔氏疏‘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曰:‘玄鳥以春分而至,氣候之常,非天命之使生契,但天之生契,則合王有天下,故本其欲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記其祈福之時,美其得天下之命。’”(張美宏《“玄鳥生商”神話的闡釋與重構》)宋代學者在疑古思潮影響下,也對前人的觀點提出了質疑,但宋代闡釋“玄鳥生商”神話最具代表性的學者朱熹卻在《詩經集傳》中言:“玄鳥,鳦也。春分玄鳥降。高辛氏之妃,有娀氏女簡狄,祈于郊禖,鳦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明顯深受兩漢注經影響。至清代,考據之學盛行,姚際恒在《詩經通論》中說:“此詩實無吞卵而生之文義,不必為之好異也。”又主張遵從古義,不必以今論古。
從上述學者不同的闡釋中可以看到,自漢以來,對“玄鳥生商”神話的闡釋多不出毛鄭兩家,并無太多新解。到了近代,圖騰學說、弗洛伊德理論等思想傳入中國,地下考古挖掘成果不斷豐富,對“玄鳥生商”神話的解釋也趨向多樣化,玄鳥的原型出現了貓頭鷹、太陽神鳥、烏鴉等諸多觀點,而對這則神話的故事性敘事則較少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