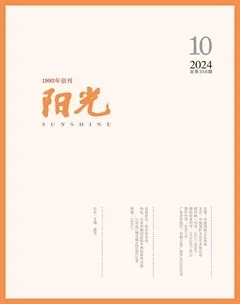煤礦人的根與情
父親已經九十多歲了。一天,他突然與我們兄弟四人拉呱起他年輕時吃下的各種酸甜苦辣,以及來到煤礦堅守,最終成為一名礦工的故事。
父親從老家木石鎮的一個農民成為相隔五十里路的陶莊煤礦工人,也是一波三折。第一次到礦上,是他和很多老家的兄弟叔侄一起來礦上打臨時工,當時條件太苦,而且招工也很難,看不到成為正式礦工的影子,他們都一起回去了。回到農村老家的父親,心有不甘,聯絡著一些兄弟叔侄再回到陶莊煤礦試試,但是其他兄弟叔侄已經嘗到煤礦的苦,也感受到在家的安適,沒有一個人愿意與父親一起重返煤礦。當時,沒有任何交通工具,父親也沒有自行車,五十里路只有靠腳板走來。一個人,背著干糧和行李,走在土路上,渾身冒出熱汗,也經受過翻越山梁時的山風冷氣,一個孤獨走在漫長道路而且不知前路如何的人,到底對煤礦抱有多少希望、懷有多少念想,才支撐著他一步步走下去。到了礦上,上一次的工友接納了他。父親租著一間農村住房湊合著住。其間家里變故多多,父親的第一位妻子不堪生活重負而離世,父親在老家續弦我的母親。那時,父親從礦上到老家用腳板來回跑,多少辛酸、多少往返的動搖、多少來自鄉親的不解指責、多少來自父母兄弟的勸說,父親都咬著牙關忍受著。仿佛一些人的命運像注定一樣,父親大概一定要成為一名礦工。
那時,父親在最艱難的時候,轉正無望,而且在當地上不了戶口,父親真的沒有辦法了,只能做出重回農村的打算。當父親和他租住房附近結識的一個當地老哥臨走說一聲時,那個老哥勸說,暫時別走,聽說有政策能落下戶口,他可以幫著問問、幫著辦。如今,父親一提起這件事,就動情地說:你們可不能忘了吳慶山大爺啊!由此,命運稍稍給了父親好的臉色,父親安穩下來,并在一個機會由礦上招工成了一名正式工,不久又把母親從老家接來,并在煤礦扎下了根。
作為礦工子女,在老家自然有著自增光鮮、讓人羨慕的一面,這是我們弟兄小時候印象非常深刻的地方。在假期或者老家有什么大事,我們兄弟幾人回家,就是農忙再忙、老家喜事喪事雜務再多,爺爺奶奶都舍不得讓我們插手,其他叔叔大爺、姊妹弟兄對我們也賓客相待,不讓干實質性的大活、硬活。記得我小時候,一回老家,奶奶就給我燒雞蛋湯或咸湯,而到飯點時,又找不到我,我往往跑到大娘家,去喝在礦上喝不到的黃燦燦、香噴噴的玉米粥,把奶奶氣得直說:“白搭上平時都舍不得吃的油了。”
在老家的這種優越感甚至連毛病也成了優點。七八歲的時候,在跟鄰居小哥吵架時,為了氣他,學他的結巴,沒想到我一點就通,一下子“青出于藍勝于藍”,且“絕技”在手、身懷不棄近四十年。有一次在老家,記得是一個結婚喜事,我們一大幫年齡相仿的小孩在一起吵鬧、嬉笑,我的結巴不時顯露出來,周圍小伙伴沒有笑的,有一個小子憋不住,要笑出來,此時,我聽到一個稚嫩卻莊重的聲音:“你別笑,人家山前人(煤礦與老家隔了一座山)說話都這樣。”我聽了,臉都紅到脖子根,立即少說話,并表現得更加穩重,自己暗自下決心,人家這樣對咱,咱就應當更板正、更好,讓人說不出來咱的孬處來。現在回想起來,這是一名礦工子女的自我鞭策、自我激勵吧。
既然是煤礦的子女,就應當有著礦山的烙印。在這點上,我是無愧于煤礦子女身份的。小時候父母要填滿我們弟兄幾張嘴,母親也要到洗煤廠干臨時工(后來轉為大集體工,也享受退休待遇)。小時候沒人看,有時就跟著母親去上班,那時才三四歲的樣子,在別人不注意的時候,我展露出煤礦人本色,不住地往嘴里填煤泥,有滋有味地吞將下去。當母親看到時,估計已經吃得“肚兒圓”了。家人現在還譏笑我,說是接連拉了七天的黑東西。現在我的臉仍然是妻子眼中“恨鐵不成鋼”的“黑”。看來我的“黑”是有出處、是有根源的,我的“黑”有著“童子功”,所以扎實、瓷實、耐久,體現了煤礦人的“本色”。
煤礦的發展在改革的風潮中,也起起伏伏,這一點,作為老煤礦工人的父母想象不到、體會不到,他們簡單地認為,我干完這些活,就該拿到錢。上世紀九十年代煤炭市場低迷,我們每月只能拿到三百多元的生活費,當時還有下崗的傳言。1992年4月的一天,我大包袱小行李地回到家,父母一看急了,問怎么回事,我事先沒有告訴父母我是到礦務局參加為期一個月的通訊員培訓班,而是裝著可憐相,謊說自己下崗了。沒想到,父母真的相信并著實驚慌、難受起來,母親是一臉的失望,父親則是煤一樣的沉默。當知道此次回去不是因為下崗,母親真的埋怨起我來:“你這孩子,可把我們嚇壞了。”即使當時效益不好,但在父輩心中,那是正兒八經的工作和飯碗啊。
后來,老礦區陸續關閉,又建設起新礦井,在我們這里叫西部礦區。建設時我們作為礦區供電單位,參與礦井初建,真正感到礦井建設工作環境艱苦、工作量大、生活條件差。礦井投產時,也有很多人不愿去西部新礦。有的同志到了新礦井,忍受不了,有不少人又申請調回到了原來的老礦,隨后跟著老礦破產、重組浮沉。說實話,一般堅持留在新礦井的職工都隨著礦井的投產、達產、崛起而在物質、精神、事業上享受著應有成果。對比這些人,留在老礦或者再返回老礦的職工則境遇就相對差一些。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也不能同時踏進兩條河流,任何選擇都有得與失。
隨著經濟的復蘇和新礦井的建成投產見效,我們煤礦人的日子越來越紅火起來了。當然,隨著國際國內形勢、經濟發展和市場形勢的變化,起起伏伏,黃金期與低谷期交叉輪回,但是確實同我們國家發展一樣,呈螺旋式上升,煤礦不斷發生著巨變、嬗變。隨著清潔生產的推進,采煤掌子面、掘進迎頭再沒有了彌漫的粉塵、煤塵,原來伴隨著煤礦人最普遍的職業病——矽肺病早已成為了歷史。隨著礦井智能化建設,遠程控制自動綜采設備、智能化開拓及噴漿固定設備的廣泛采用,采煤一線的工作面、掘進一線的迎頭,已經能夠實現遠程控制機器作業了,不需要人在最靠近煤、漆黑的深處輪鎬攉鏟、抱著鉆機躬腰使勁了。近期聽到喜訊,煤礦專用盾構機即將投入礦井建設,這些都是煤礦緊跟時代潮流的巨大進步。機械化減人、智動化換人正在逐步擴展,這些都減輕了煤礦人的工作強度、提高了安全系數,本質安全型建設正在成為煤礦的現實。煤礦人實現了體面勞動,煤礦再也不是“黑、大、粗”的形象了,我們煤礦工人已經變成新時代的“煤亮子”。
煤礦上一直存在著的一個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就是人們對煤礦安全的擔心和擔憂。剛參加工作時,到了一個老礦,煤層很薄,最厚的也就是1米,最薄的才0.6米。沒下井前,聽人家說,到了井下要“爬面”,我以為是爬山式的俯身彎腰式的“爬”。而到了高度只有0.8米左右的巷道和采煤面里,才知道那是在上下都是堅硬黑色巨石之間四肢著地、甚至大氣不敢出、憋著氣息的匍匐爬行。在黑暗的、巨石間的毫不讓人自由喘息的堅硬現實面前,這種擠壓與恐懼是巨大的。煤礦詩人老井曾寫到:“在地心狹小的巷道里勞作/我們只感到被一種滄桑和悲愴壓低海拔”,在地心深處的壓低感讓人聯想到滄桑,沒有聯想無疑則是一種實在的沮喪。煤礦人永遠不能忘記的和永遠揪心的是煤礦事故對人身心的傷害和對家人帶來的悲痛。新時代的煤炭產業已經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礦井的安全管理、安全保障越來越提升和增強,本質安全型建設日益把這一陰霾驅散。
有一段時間,我在集團公司工會從事文體工作,在一次春晚的籌備工作中,領導要求要有一個反映激勵赴外開發新礦山的語言類節目。在研究創作節目時,我們是挖空心思、絞盡腦汁,然而久久不得其法,一直找不到感情著力點、拉不出故事發展線、把握不準正向激勵的呈現面。冥思苦想、深思入夢,終于有一天靈光閃現、豁然開朗、柳暗花明。“以父輩從農村走進礦山處著墨,以父輩改變礦山、改變自己、改善生活的過程,映照今天赴外開發的從無到有、從苦到甜、從艱辛創業到適應苦難到平穩發展到事業升騰、生活美好的歷程,不是就能夠反映出赴外開發的意義、價值和美好的未來嗎?”思路一開,文思泉涌。僅僅一天的時間,我們就完成從確定思路到初步定稿的關鍵步驟。在排練時,我們反復與青年職工演員交流父輩這些付出、吃的這些苦、受的這些罪,加深對創業的情感理解、加深對開拓發展的激情體會,從內心激發出勇敢走出去、向外進發、創業發展的澎湃力量。在那年春晚上,這個小品得到了肯定,收到了預想效果。
靜下心來,反思這個小品,更多的想法涌上心來。我想,經歷過艱苦創業而獲得發展、贏得幸福美好生活,不僅僅是煤礦工人,其他的石油、鋼鐵等等產業不也是這樣嗎?就是我們不理解的智能、新興產業也一定存在著從小到大、從難到易、從苦到甜的播種、耕耘、收獲過程。煤礦人的根與情,那是作為一個個體,恰好與煤礦、煤炭產生了這種情愫,與長年累月的無間相融,任何事業、事情都有苦與樂的交織,都蘊含著苦與樂、付出與收獲甚至生與死的辯證,我們人類就是以這樣的姿態一步步走來的。人類之神奇、之偉大,頓時出現在腦海間、升騰到宏闊的高天之上。此時,我深深感到,煤礦人的根與情,更加深厚、更加沉重、更加飽滿地伸向這滾燙的、無邊無際的大地……
劉兆軍:山東能源棗礦集團中興電氣公司職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