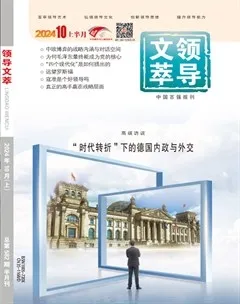中歐博弈的戰略內涵與對話空間
歐盟對華不尋求美國式的霸權護持,只是不希望中國有過大的國際規則制定能力,這奠定了中歐貿易博弈的大體框架。
2024年7月5日,歐盟針對中國電動車的臨時關稅進入實施階段。這是一個過渡方案,為期4個月。如果博弈破裂,之后將是為期5年的正式關稅。
這項關稅源于6月16日,歐盟委員會宣布對原產于中國的電動汽車征收17.4%~38.1%的臨時反補貼稅。在10%原關稅的基礎上,歐盟根據不同公司的具體情況,額外征收了不同的稅率。如比亞迪的稅率提升至17.4%,吉利為19.9%,其中上汽最高,達到37.6%。
事實上,早在去年9月13日,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未按照世貿組織規則事先通報的情況下,公開宣布將對中國電動汽車發起反補貼調查。
調查聚焦兩方面:一是中國電動汽車是否獲得政府補貼,二是中國電動汽車的進口是否對歐盟車企造成損害。對該調查,中國一直主張對話協商化解;相關企業也積極配合,展現出了極大的克制與善意。

盡管如此,9個月后,歐盟委員會還是不顧歐盟汽車產業的全力反對,宣布了關稅政策的落地,這也被認為貿易保護主義達到新的高度。
那么,歐盟緣何付出昂貴成本,仍堅持對華加征高額關稅?我國有何種應對方略?這些問題都涉及當前的國際秩序和地緣政治格局。
政治操控
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反補貼調查應該說不少,但多數是基于產業本身,尚未上升到政治層面。
譬如,巴西就對自中國進口的多個產業進行反傾銷、反補貼調查。然而,歐盟這次調查和其他產業調查有著本質區別,地緣政治內涵尤為突出。歐盟也開始和美國一樣,日益從戰略競爭的角度,看待我國相關產業的發展,其操作過程有著明顯的政治性。
首先,這次調查并沒有基于歐盟汽車產業界申訴,而是馮德萊恩在歐盟自行啟動,這也引來了歐洲行業代表在不同場合表達對調查的擔憂。
其次,調查對象指向中國企業而非在中國的歐美企業。2023年,我國向歐盟出口的純電汽車為48.2萬輛,占電動汽車出口總量的45.1%。
出口的純電汽車有三到四成是特斯拉,約兩成是歐洲汽車品牌,中國自主品牌不到總量的一半,而調查卻主要針對中國自身的企業而非外資企業。
另外,雖然號稱“反補貼調查”,但其實歐盟還調查中國企業技術和商業秘密。其調查結論也很有預設性,也就是不管調查過程咋樣,結論已經注定,即中國汽車企業存在嚴重的政府補貼,要的數據信息也只是用來佐證早已定下的結論。中國企業的舉證門檻非常高,最終不得不放棄抗辯。
調查將企業分類,還有分化中國產業界的意圖。歐盟清晰了解中國汽車產業有國有、民營的區別,作為國企的上汽集團,拒絕提供包括電池成分和配方在內的多項非必要關鍵核心信息,歐盟為此決定對上汽出口汽車加征37.6%關稅,總征稅率高達47.6%。
其實,歐盟和中國都有的數項補貼中,歐盟補貼比中方還高;歐盟還在補貼認定上施行“雙重標準”,即一些科研研發的支持,被認定為補貼,而自身卻不認定為補貼。很顯然,這些“補貼”指控并不符合世貿組織規則。
美歐協同
電動汽車,一方面是產業,另一方面連接著氣候政策,事關國家核心競爭力,世界各國都努力在這一新賽道獲取競爭優勢。
近年來,我國新能源汽車在創新速度和品質把控上取得驚人成績。中國品牌電動車在歐洲電車銷售中的占比,從2019年的0.4%猛增到2023年的7.9%。歐盟國家普遍擔憂,歐盟對華汽車貿易一直是強項,一旦出現逆轉,將引發嚴重的政治社會危機,故要求對中國采取保護主義措施的聲音急劇升高、增多。
除了產業層面的原因,俄烏沖突后,歐盟對美國的依賴明顯上升,電動汽車產業受美國挾制程度增加,充滿地緣政治意識的“去風險”和“多元化”,成了對華的主基調。
事實上,歐盟關稅決定之前,美國已于5月14日宣布對中國電動汽車關稅增加至102.5%。歐盟此輪的跟進,可看成美國推動下歐美協調性的表現。當下歐洲輿論認為,中國市場準入的不對等,對歐洲實體的經濟脅迫,加速了歐盟離心。
今年G7峰會進一步推動了美歐協調性,針對中國迅速崛起的電動汽車和其他新能源產業在“產能過剩論”下有明確一致的聲音。美國財長耶倫呼吁以市場為導向的國家,針對中國由國家主導工業政策,筑起“反對之墻”。
在G7的帶動下,包括墨西哥、印度和南非在內的國家,都對中國在電動車、太陽能產品、半導體、鋼鐵和其他戰略行業的“過度投資擔憂”明顯上升。
6月8日,收到歐盟風聲的土耳其,宣布對原產地為中國的燃油及混合動力乘用車征收40%額外進口關稅,而此前土耳其已對中國產電動汽車加征40%附加關稅。
橫向比較而言,中國給電動汽車的補貼金額大嗎?其實并不大,法國每輛電動汽車能補到4000歐元,低收入家庭消費還能再多補3000歐元。美國電動汽車能補到7500美元。
問題關鍵并不在于補貼金額多少,還在于是否有歧視性,譬如美國的《通脹削減法案》就規定不能買中國電池和原材料。這其實是一種進口替代,并不為世貿規則所允許。
如果美歐能使用世貿組織允許的補貼,把電動汽車產業發展起來,對中國未必不是好事。畢竟,更好的產業鏈接以及市場擴展,可以加快推進低碳經濟轉型。
但不能一面歧視性遏制打擊中國的新能源產業,另一面又不維持氣候與能源政策的穩定性。這實際上宣示地緣政治已完全成為核心考量。
博弈空間
長期以來,歐盟對華一直有著歧視性政策,譬如,歐盟一共發起了190個反傾銷反補貼調查,中國對歐盟只發起了37項。“雙反案”數量上,歐方對華是中國對歐的五倍多,中歐關系在經貿領域確實有著部分的不平等。
針對這種不平等和歧視,中國依舊主張開放,甚至愿意在某些領域單邊開放強化國內的競爭和產業升級動力。然而,歐盟卻將這種善意視為簡單讓步,仍潛意識覺得中國別無選擇,只能承受。
事實上,如今,中國是全球唯一年度汽車銷售量近3000萬輛的國家,這決定了任何車企、任何國家的汽車產業都不能無視。這也給予中國最強大的談判能量。
歐盟要對中國電動汽車征稅,而中國同樣也可以在合理范圍對歐盟的汽車產業加征關稅,譬如將大排量汽車臨時關稅從15%提升到25%。這就迫使雙方不得不坐下來進行直接雙邊磋商。
事實上,中國的政策工具箱中,仍有多個工具,除了將大排量汽車臨時關稅從15%提升到25%,使歐盟的奔馳、寶馬遭遇更大的銷售壓力,還可對若干歐盟與中國聯系密切且涉及就業較多的行業進行反傾銷調查,譬如中國產業界已要求政府對從歐盟進口的乳制品、白蘭地和豬肉產品展開反補貼與反傾銷調查,調查機關將依法進行審查。
這些都意味著,未來雙方還有諸多博弈空間與對話空間。從這個角度看,這種境況可能比與美國交涉要好些。
表面上,美國通過G7鞏固了與歐洲盟友的對華共識,都希望減少對中國產品的依賴,但歐盟與美國的戰略目標仍有明顯不一致。歐盟追求產業發展,仍希望我國在電動汽車產業投資幫助其配套完善供應鏈,比如在歐洲建廠的比亞迪,受關稅波及就較小。美國則基本不希望任何中國元素進入。歐盟對華不尋求美國式的霸權護持,只是不希望中國有過大的國際規則制定能力,這奠定了中歐貿易博弈的大體框架。
因此,中國和美國有可能走向不同的汽車產業和技術發展路徑,但在和歐盟的博弈中,擴大共識、求同存異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摘自《南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