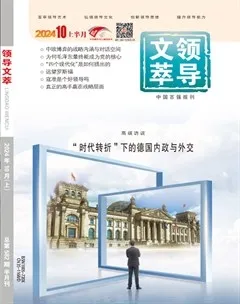對一戰負責的,不應只是德國
法國數學家埃克朗說:“世界不分因果鏈,不是線性地安排事件,使得前者是后者的原因,后者是前者的結果……任何事件永遠不會只有一個原因,越往前尋找,越能找到任一特殊事件發生的越多的前因。”保羅·哈姆正是采取了這樣的思路,將一切追溯到1870年,回顧了歐洲整體社會氛圍以及權力格局的重塑。
伴隨工業革命發展,歐洲經濟蒸蒸日上,進入了機器時代。生產力的迅速進步給歐洲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歐洲君主制及其象征的等級制度頑固地拒絕社會改革,歐洲整體社會氛圍直到20世紀初仍然是保守的。然而要求社會變革的潛流始終在看似穩固的表象下奔涌,對歐洲各國特權階層來說,他們所認識的世界遭受了嚴重的政治和社會威脅,戰爭不失為一個機會,可以團結民眾一致對外,從而解決國內危機。
與此同時,科技發展日新月異,戰爭領域的技術進步尤為神速——火車、飛機、汽車、大炮和機槍令歐洲人掌握了前所未有的殺戮力量,但歐洲的軍隊還跟不上技術變革的步伐,歐洲的君主、政客和將軍們都知道將要到來的戰爭是恐怖的,但都想象不到自己將要開啟的是何等規模和烈度的戰爭。
當時歐洲的大國關系合縱連橫,如同“四對舞”一樣,不同國家間有時緊張,有時緩和。在這之中,1871年普法戰爭后崛起的德國是位于歐洲心臟的一股新生力量。剛剛完成統一的德意志缺席了瓜分非洲這場帝國主義盛宴,隨bEG9i6/RVGaXRoHnYLjeLuAxtEYl7rCyEGEgnLbyeBM=著經濟快速發展和國力迅速提升,德國也想要進行海外擴張,以滿足國內發展需要,卻一再受阻于英法,這令柏林憤懣不已。俾斯麥下野后,德皇威廉二世放棄了相對克制的對外政策,并推出了所謂“世界政策”。受此影響,無論是高層還是普通國民,都夢想德國成為世界強國,正如提爾皮茨海軍上將認為的,德國取得全球主導地位,就像“自然規律一樣不可抗拒”,英德關系因此逐漸惡化。
而在巴爾干半島,危機正在孕育。奧匈帝國與站在塞爾維亞背后的俄國交惡,德國和奧匈帝國,之后又加上意大利,組成了三國同盟,以對抗俄國。隨著法國民族主義抬頭,德國與法國的關系在19世紀末迅速惡化。1892年,法俄締結協定,將三國同盟視為敵人,加深了裂痕。英國也不得不做出自己的選擇,并逐步向法俄靠攏。
進入20世紀,歐洲列強都處于國內外重重矛盾之中,但戰爭并非必然選項。然而,它們卻并未試圖彼此協調,而是以不同方式籌劃戰爭,任由局勢進一步惡化。德國認為自己受到法國和俄國兩個不友好的鄰國威脅,并擔憂自身生存。1906年,德國首相比洛在帝國議會首次使用了“包圍”一詞,此后大眾一致認為“包圍已成事實”——法國渴望為1871年的戰敗復仇,英國希望粉碎德國的新生帝國,俄國的斯拉夫人對德意志民族懷有與生俱來的仇恨。1907年,英國與法俄締結三國協約,這更令德國的民族主義者驚恐萬分。
英國外交部的鷹派對德國崛起高度警惕,認為德國海軍是對英國生存最大的威脅,對德國有著歇斯底里的敵視,并斷言德國和英國正走向“必然的戰爭”。
法國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希望奪回阿爾薩斯-洛林,恢復昔日的榮耀。在這種氛圍中,法國領導層拒絕改善德法關系,放任國內的戰爭叫囂。而兩次摩洛哥危機加劇了英法兩國對德國的警惕,他們將與德國的戰爭視為最大的現實威脅。1910年被任命為英國軍事作戰局局長的威爾遜更是無視英國官方政策,僭越職權秘密制定了動員英軍參加大陸戰爭的計劃。
奧匈帝國正在分崩離析,軍隊高層將戰爭視為維護哈布斯堡王朝自尊和延續的唯一手段,并擺出好戰姿態,而他們的目標是征服塞爾維亞。正是這一魯莽決策點燃了歐洲的火藥桶。
總之,歐洲各國沒有付出任何認真的外交努力,通過談判來協調各方,相反,各國都熱衷于軍事手段,認為戰爭“迫在眉睫”。歐洲各國主流媒體的宣傳,使得公眾意識中也接受了戰爭的“必然性”。
1914年6月28日,薩拉熱窩一聲槍響,奧匈帝國認為“解決塞爾維亞問題的機會到了”,并向德國求助。威廉二世在7月5日明確表示,將無條件忠于盟約。但是,實際上德國并沒有認真考慮過可能到來的大規模戰爭問題,皇帝照常出門旅行。奧匈帝國的反應也沒有像德國預想的那樣迅速,直到7月23日才向塞爾維亞發出最后通牒,其中所提的要求甚至連德國方面也認為有些過分,聲明自己對此毫無所知。最后,盡管塞爾維亞滿足了絕大部分要求,奧匈帝國仍斷絕了兩國關系,在7月28日向塞爾維亞宣戰。沙皇俄國作為塞爾維亞的保護國,隨即發布了軍事動員令,其盟友法國也表示將全力以赴支持沙皇俄國。德國作為奧匈帝國的盟友,則于8月1日和3日分別向俄、法兩國宣戰并入侵比利時,導致英國對德宣戰。
令人感嘆的是,在如此重大的歷史關頭,歐洲歷史舞臺上卻盡是一群庸碌之輩。德皇威廉二世經常做出“愚蠢甚至孩子氣的行為”,雖然嘴上發出戰爭叫囂,但“在面對威脅時,威廉確實是在躲避暴力,傾向于躲在他的羽毛帽子下求和”。沙皇尼古拉二世名為專制君主,實際上只是將軍和大臣們的傀儡,無法牢牢把握國家事務,被即將到來的屠殺嚇得不輕。英國的喬治五世已經無法理解事態發展,只是表達了老派的沮喪。奧皇約瑟夫則自己在宮中忙來忙去,眼不見心不煩。
幾國文官也大多反復無常、手忙腳亂,奧匈帝國外交大臣貝希托爾德優柔寡斷,他大力促成了對塞爾維亞的最后通牒,事到臨頭卻失去了勇氣,擔心真的開戰會壞事。德國首相貝特曼敦促奧匈帝國開戰,并愚蠢地希望英國在德國與法國的戰爭中保持中立,但當得知英國會站在法國一邊后,陷入崩潰,對時局發展感到驚恐。英國外交大臣格雷后知后覺,他本以為塞爾維亞問題無關緊要,對奧匈帝國與塞爾維亞之間的沖突漠不關心,直到7月27日才意識到大事不好,因此如坐針氈,但他依然沒有采取任何有力措施阻止各國加速走向戰爭。
于是,在誤解、爭吵、猶豫之間,博弈過程一錯再錯。德國錯誤地給了奧匈帝國一張無條件支持它的“空白支票”;奧匈帝國錯誤地估計形勢,向塞爾維亞遞交了最后通牒;俄國錯誤地在談判中拒絕撤回總動員令;德國錯誤地低估了英國保護比利時中立的決心……
“七月危機”釀成了外交史上最大的一次失敗,一連串的冒險和誤判把大家都逼進了死胡同。終于,各國紛紛動員,戰爭機器啟動了。各國人民懷著“為國捐軀,美好且光榮”的想法,熱切地涌入戰爭。
德軍借道比利時入侵法國,按照“施里芬計劃”的宏大構想,展開對法軍的兩翼合圍,但最終在馬恩河折戟,之后西線轉入塹壕戰。奧軍入侵塞爾維亞,連戰皆敗,但塞爾維亞人也損失慘重。俄軍為策應西線,向德奧發起進攻,但在坦能堡遭到慘敗。無論在東線還是西線,任何一方都未能取得決定性勝利,戰爭又持續了4年。
費曼說過,真實世界中最重要的東西,看起來就像是一大批定律共同起作用而帶來的一種復雜的偶然結果。歐洲各國對戰爭爆發都負有責任,看似偶然的結果,其實早就注定。集體愚蠢和麻木不仁導致了一代人的死亡。
(摘自《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