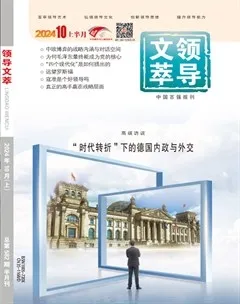帝制時代的最后時光,為何還內斗

1900年1月24日,慈禧通知朝廷宗室親貴、王大臣及大學士、軍機大臣、各部尚書侍郎等重要臣僚,來西苑儀鸞殿單獨召見。這次背著皇帝的召見,必然不符合規矩——出大事了。
一上來慈禧就降諭:“當初立載湉為帝,天下不滿之聲四起,只因穆宗同治皇帝無子,不得已而為之。皇上但凡稍具天良,都應日日思想如何孝順報答。可是前年康黨謀逆,意圖圍頤和園殺我,為皇上張目。載湉竟然贊成,實屬大逆不道。現在我已經決定,另立他人為穆宗之后。”這個重磅炸彈讓大臣們都傻了眼——原來太后召見是要廢皇帝,她并不是征求意見,而是通知——這讓大臣們誰都不敢說話。
見此情形,慈禧拋出了自己制定的解決方案,她想按前朝明英宗給予景泰皇帝的待遇處置光緒皇帝,將他降為親王。此方案一出終于有人呼應了,與光緒政治路線有分歧的體仁閣大學士徐桐率先表示支持,之后大臣們礙于慈禧的權勢紛紛表示贊成。一些受正統儒家教育的大臣含蓄地表示這個做法有所不妥,忍著怒火的慈禧直接說:“皇室的事是我們滿人的事,非你們漢人所能參與。今日召見漢人尚書大臣,知會此事,已屬格外開恩,哪里由得你出言。”此時,他們才恍然大悟,這位手握清朝最高權力的太后是鐵了心要廢帝,事情已沒有可商量的余地了。
這次會議發生在八國聯軍攻入北京的半年前,慈禧如夢初醒,那個被自己一手扶持上來的孩子竟然想要她的命。這讓慈禧出離憤怒,頂著清朝二百多年的祖制施行廢立之事,滿心都是失去權力的恐懼。與此同時,中國這艘巨輪已經駛入了河道狹窄崎嶇的險境,列強的瓜分,混亂的社會,崩潰的經濟,階級的欺壓,已使中國千瘡百孔,而作為這艘輪船的掌舵者,慈禧太后仍舊進行著權力斗爭,力圖消滅任何不愿同沉淪的異議者。
1900年這個被稱為“庚子國難”的一年,就在慈禧和光緒的爭斗中拉開序幕。
慈禧本打算庚子年正月初一直接廢帝立新君,但心腹榮祿對此并不認同,不過,多年的官場生涯教會了他無論如何也不要和太后對著干。因此,時任直隸總督的榮祿借著別人的意見,跟慈禧提出不要立儲,而是改為立大阿哥,不要剛立大阿哥就廢皇帝,要分兩步走,先向天下公告,觀察中外反應,等風頭過去后再行廢立,這會讓事辦得更合情合理。榮祿的小九九是,或許事情還可以有變。
立大阿哥后,慈禧很關注洋人的反應,畢竟英國人在戊戌年間就保護過光緒皇帝,曾向大沽口出動艦船,也保護過康有為逃至香港。所以,慈禧提前給各地總督發了密諭,告訴他們如果洋人逼我退居二線,咱們就跟他們拼個魚死網破。同時,慈禧也親自接見外國公使夫人們,請客吃飯拉攏感情,樹立開明友好的形象。
建儲一事天下皆知后,總理衙門才就此事給各國公使發出正式照會。照會發出后會收到怎樣的回應,大家心里都沒底。端王載漪沒主持過外交工作,缺乏經驗和定力,照會發出沒幾天就召各國公使入賀,結果沒有得到任何回應。這使得朝廷內本就心虛的廢立派,認為洋人持反對意見,心生怨恨。
作為在華利益最大的英國,此時在南非正陷入布爾戰爭,且慈禧主政后并沒有損害英國的在華利益,所以英國朝野有所共識,慈禧雖然保守,但并不排外,她只關心自己的權力,在不損害英國利益的前提下不隨便干涉。德國在1898年和清朝簽訂了《膠澳租界條約》,剛占得便宜沒必要因立儲一事與慈禧發生沖突。美國則更沒有興趣干涉,很早美國就察覺高層的權力爭斗不會影響中國經濟過渡和商業發展,不會損傷美國的利益,自然也沒有干涉的必要。而俄國本身就傾向于后黨,長期通過太后與傾向帝黨的英美日爭奪在華利益,扳倒光緒他們反而樂見其成,法國也與俄國結成了聯盟,利益趨于一致。
只有日本嘗試采取積極行動。日本表明如果只是選繼承人,日本無話可說,如果是為了廢光緒皇帝,日本將進行干涉。日本如此表態的目的是希望遏制俄國的野心,讓親英美的光緒對抗住親俄的后黨勢力。
1900年還存在一個偶然因素,就是熟悉中國情況的駐華公使們紛紛離任,換上的大多數是從非洲殖民地來的,他們用治理非洲的經驗來指導中國外交,自然既不了解中國政治,又聽不懂官場的潛臺詞,連翻譯都不合格,譯出來的意思都天差地別,在總理衙門經常以恐嚇拍桌子的方式來解決問題,這樣更是讓慈禧誤以為他們想要自己歸政,把權力交還給皇帝。
新來的駐華公使想迅速立功,如果外國人出現損失,就可以借此要求中國給出更多賠償,甚至簽訂新的條約。不僅是這些駐華公使,慈禧、李鴻章、端王其實也是在謀求現有的限制條件下對自己最好的結果。推動東南互保的盛宣懷想保住自己的地位與洋務事業;義和團的拳民想讓自己吃飽飯,進一步最好能當上大師兄;剛毅想的是要當上大學士……
所以說,并不是少數幾個關鍵原因決定了歷史,在環境推動下,歷史的每一個參與者都在謀求更好的出路,每個人的努力和掙扎匯聚成了這段歷史。
(摘自《讀好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