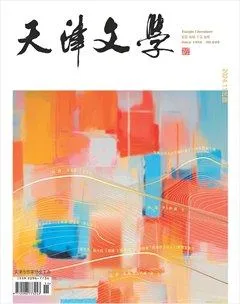小鎮(zhèn)車事
有人說:“汽車最能代表一個國家的工業(yè)化水平。”這些年,我在小鎮(zhèn)和汽車之間發(fā)生的種種故事,就是共和國工業(yè)化飛速發(fā)展的一個縮影。
20世紀(jì)60年代后期,我出生在隴東大山深處的一個偏僻小鎮(zhèn)——安口窯,從小就與生活在那個時代的所有人一樣,經(jīng)受了物質(zhì)匱乏,曾陷入貧窮拮據(jù)的生活困境。汽車對于普通人來說更是稀罕之物,小鎮(zhèn)人就很少能見得到。按理說我與汽車是不沾邊的,可巧鄰居王叔就在縣商業(yè)局開汽車,他經(jīng)常會將全縣唯一一輛草綠色的解放牌大卡車開回家來,我就有機(jī)會近距離接觸它了。
王叔的兒子祥子與我年齡相仿,是我最要好的玩伴。每逢王叔開車回家,他就是那輛卡車當(dāng)然的看護(hù)者。他時常站在高大的車廂里,手持一根長長的竹棍,居高臨下,威嚴(yán)地圍繞著車幫來回巡邏,不時還將手中的竹棍用力甩打在木頭車廂上,發(fā)出啪啪啪的巨大聲響,警示圍觀的人員不得靠近半步,哪怕是鄰居、親戚家的孩子,甚至成年人也不例外。但他對我卻寬容大度,欣然邀請我爬上車廂,站在他身邊觀看。有時我也會作為他的幫手,分別站在汽車兩邊寬大的踏板上,抓了車門的把手,完全探出身子,不斷嚴(yán)厲呵斥已近前看稀罕的人群:“靠后站靠后站,不許碰!”每每在眾人羨慕的目光中狐假虎威、吆五喝六,出盡了風(fēng)頭。逢到圍觀人員稀少的時候,他也會拉開車門,讓我坐在副駕駛位置,自己則坐在駕駛座前,手握方向盤,來回轉(zhuǎn)動,嘴里模仿著汽車發(fā)動機(jī)嗚嗚的聲音,表示汽車已經(jīng)開始行駛。汽車“走”著“走”著,他的身子一會兒在裝了彈簧的座椅上上下跳躍,好像經(jīng)過顛簸不平的道路一樣上躥下跳;一會兒又將身子使勁歪向一邊,好像車輛正在快速通過彎道,要將乘客甩出車外一般;一會兒嘴里模仿汽車機(jī)器沉悶遲緩的轟鳴聲音,臉也漲得通紅,又好像載了重物的車輛正在艱難爬坡上山……祥子“開車”時神情專注,動作既夸張又帥氣,非常生動形象。祥子經(jīng)常坐汽車,自然乘車體驗真切,見多識廣。他知道油門、離合、擋位、儀表、閘(剎車)……都會一一指給我看,但僅僅是看,絕不許我觸摸。為了防止我情不自禁伸出手來,他要求我必須雙手背后,互相抓牢。只有我老老實實依了他,才能在汽車駕駛室里多待一會兒。
聽祥子說,王叔是抗美援朝時期的功勛汽車兵,退伍后才回到縣商業(yè)局開上了大汽車。全縣的生活、生產(chǎn)物料就靠這一輛車運輸,責(zé)任重大,但也好處不少。那時我們一般人家大多定量供應(yīng)的多是雜糧,還經(jīng)常吃不飽肚子,根本見不到白面。祥子卻整天都有白面饃饃吃,管夠,這就是明證。但好景不長,有一天晚上,地處鎮(zhèn)外五公里的縣二中公映電影《秘密圖紙》,惹得四方八面的人都去觀看,整整站了一個足球場的觀眾。電影放映結(jié)束,小鎮(zhèn)去的人都認(rèn)識王叔開的汽車,知道他要回鎮(zhèn)上,遂呼朋喚友,不管不顧,硬擠著全攀爬上了車廂。盡管王叔和祥子大聲呵斥,再三阻止,車上人卻趁著夜色遮掩,就是不下來。王叔無法,只能用不發(fā)車對抗。興奮的車上人此前哪里有過親身乘車的體驗呀,遇此良機(jī),誰肯輕易放過。眼看著電影散場已半個多小時了,竟沒有一人下車。第二天還要出車的王叔內(nèi)心焦急,只得妥協(xié)。但窩了心火的王叔,回家路上就把汽車開得飛快,轉(zhuǎn)彎也不減速,甩得車廂里密密匝匝的乘客哭天喊地、叫苦不迭,氣昏頭的王叔卻不管不顧,我行我素。悲劇就在這個激烈的行車過程中發(fā)生了:車到鎮(zhèn)上后才發(fā)現(xiàn),一個七八歲的小男孩被擁擠的人群擠壞了,送到醫(yī)院還是沒有救下來。王叔因為這次事故影響,被單位調(diào)去看了大門,再也不能開大汽車了。后來過了很長一段時間,我再沒有機(jī)會接觸到汽車,祥子也沒有白面饃饃吃了。
20世紀(jì)90年代初,我在小鎮(zhèn)一家煤炭企業(yè)工作。那時候,小鎮(zhèn)上的一些企事業(yè)單位已開始有了卡車和小汽車,但數(shù)量依然很少。我結(jié)婚的時候,為了節(jié)省開支,減輕家庭負(fù)擔(dān),便響應(yīng)單位號召,參加了集體婚禮。為了鼓勵我們移風(fēng)易俗的精神,單位破例批準(zhǔn)用唯一的一部北京吉普車輪流接送我們八對夫妻新人。
婚禮那天早晨,母親早早起床,找來許多親戚幫忙,做了一大桌上好的菜,還包了餃子、搟了長面。按照小鎮(zhèn)風(fēng)俗,“上轎餃子下轎面”,接親的人出門前要吃餃子,寓意婚事順順利利;接親回來要吃長面,寓意日子長長久久。因為吉普車從我家出發(fā),去妻子娘家接了人就直接去婚禮現(xiàn)場了,不再回來,所以餃子、長面和一大桌菜就一起端上了桌。奇怪的是被我們一家人眾星捧月般圍坐在上席的司機(jī)師傅,卻沒有吃一口面、一個餃子,甚至面對一大桌琳瑯滿目的菜肴竟沒有動一下筷子,只是一個勁兒督促我們趕快起身。不明就里的一家人實在拗他不過,只得讓我和一個大嬸急急拎了接親的禮品,悻悻隨他去了。好在那天婚禮進(jìn)行得非常順利,特別是那輛草綠色的帆布篷吉普車,披紅掛彩,打扮一新,在噼里啪啦的爆竹聲中慢慢駛進(jìn)岳母家的小院,風(fēng)風(fēng)光光地迎接新人,算是給妻子娘家賺了臉面,也不致讓經(jīng)濟(jì)拮據(jù)的我過分暴露實在寒酸的家底。但許多年過后,母親每每念及接親出發(fā)前的情景,都自責(zé)有加,特別是我們夫妻后來在生活中出現(xiàn)矛盾,一旦被她知道,都要說全怪她沒本事,那時家里條件太差,自己做不出更好的飯菜,所以司機(jī)師傅才沒有吃一口。現(xiàn)在回頭分析這事,可能就是司機(jī)一大早要輪流接送八個新娘子,每家都要吃幾乎同樣的飯菜,到我家后的確吃飽了,吃撐了,實在吃不下去了。加上那天時間緊急,接親過程冗長,司機(jī)也實在無力應(yīng)對這種俗禮罷了。
步入二十一世紀(jì),小鎮(zhèn)寬闊平整的大街上,不知不覺間竟冒出了許許多多的汽車,有單位車,有私家車,但私家車已越來越多;有進(jìn)口車,有合資車,但更多的是國產(chǎn)車。這么多的車,鋪天蓋地、川流不息,搞得小鎮(zhèn)上下班時間、交通要道處常常會出現(xiàn)大城市的交通病——堵車。好在政府馬上加大了城建投入,拓寬了街道,提升了公路品質(zhì),有了汽車的小鎮(zhèn)人,生活得更加快捷、舒適和幸福。
2010年前后,禁不住身邊有車族的誘惑,我報考了駕校,半年后順利拿到汽車駕駛證,并馬上購買了一臺轎車。車剛開回家的那段時間,我一直像做夢一般,懵懵懂懂,怎么也不相信樓下停放的那輛漂亮的紅色轎車真就屬于自己,很久不能恢復(fù)正常。此后的日子,白天開車出門上班,路遇熟人總要主動停車搭訕,熱情邀請人家搭一段順風(fēng)車。下午回家收車,第一件事就是擦洗車輛,不忍落下一點兒灰塵。遇到車友,也是三句話不離自己的愛車,免不了流露出神采飛揚、眉飛色舞的豪情和底氣。周末假期,也常與家人、朋友相約,自駕出游。祖國的大江南北、雪域高原,大漠長河、邊寨村落,皆有涉足,留下了許多深刻的旅游體驗,也給身居西部小鎮(zhèn)的我,搭設(shè)了與大城市一樣的生活平臺。也是在不知不覺間,汽車居然已經(jīng)成了我們家生活、工作不可或缺的工具和助手。
前天晚上,已經(jīng)躺在床上的妻突然提議,我們應(yīng)該換車了,換一輛有越野功能的SUV,能去更遠(yuǎn)更險的地方,能看更好更美的風(fēng)景。我們大略盤算了一下家底,這個計劃完全可以馬上實施嘛。
那一夜我做了一個夢,夢見自己帶著全家人,開著剛買的新車,飛馳在平坦筆直的高速公路上。路兩邊綠樹成蔭、花團(tuán)錦簇,前方道路寬闊、陽光明媚。我們一路唱著、笑著,享受著我們的美好生活,一直駛?cè)肓税倩ㄊ㈤_的深處。
庚申,原名劉根生,甘肅省華亭煤業(yè)公司員工,有散文隨筆作品在《中國煤炭報》《甘肅日報》《唐山文學(xué)》《仙女湖》《崆峒》《教師報》《烏魯木齊晚報》《蘭州晚報》等報刊及中國作家網(wǎng)、中國煤礦文化網(wǎng)、學(xué)習(xí)強國等網(wǎng)絡(luò)平臺登載、獲獎,著有散文隨筆集《遙看草色》。
責(zé)任編輯:楊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