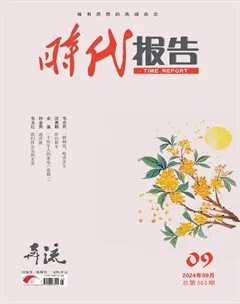玉米兄弟

玉米,家鄉人不叫它玉米,叫它包谷,包米,玉蜀黍,玉黍棒子,就像在叫自家兄弟。
老家豫南,在由莊稼組成的大家庭里,雖然成員不少,但能像玉米愿意和你結為兄弟的莊稼確實不多。比如小麥吧,雖然常常以坐第一把交椅的姿勢出現,但農民想指望賣小麥花錢根本指望不上;大豆吧,雖然被冠以高蛋白植物的美名,但也只能耍個花拳繡腿;大麥和高粱,屬于小雜糧門戶,常吃未免有點兒捉襟見肘;紅薯產量雖高,很多時候都派不上用場;剩下的,花生和油菜是油料作物。說來說去,還是玉米,產量又高,產值也不低,站著偉岸,砍倒后也是干板直正,打下來的籽粒亦是金燦燦的,蒸饃烙餅,熬粥煲湯,香噴噴甜滋滋,拿得起,放得下,曬干了往集市上一拉,一家人全年的花銷就有了指靠。
可以說,那個時期,玉米支撐著農民的半拉子家園。假設沒有玉米的鼎力相助,農民的日子不知該怎么過。
春天,杏花開了,柳眼睜了,小燕子也從南方飛回來了。去冬預留下的秋地里,煙苗已經下地,棉花正在拱土,新栽的紅薯也已躥出一拃多長,綠波蕩漾的麥田也在做著拔節的準備,拾掇好的谷種正待一場春雨的降臨。自然界的生靈們,一個個蠢蠢欲動,都在謀劃著一年的歷程,玉米仍不為所動。
玉米這不是不為所動,它是在瞅準時機。它抱定信念:既然兄弟一場,那就對得起兄弟這個名分,不干則已,要干就干個轟轟烈烈。小麥收割完畢,正是初夏那段最難耐的日子,大太陽在上面烤著,滾燙的南風在下面逼著,可農時不待人啊!俗語說,五黃六月爭回耬,農民們得抓緊時間把下茬的作物種上。種什么呢?種瓜果菜蔬綠木花卉?這些弱不禁風的綠植能勝任嗎?種高粱,谷子,紅薯,蕎麥?面對騰茬后的大片大片一望無際的田野,它們有那么大的格局嗎?只有玉米。
說玉米是臨危受命,這不是人為強加于它的,這是由它骨子里的秉性所決定的。玉米不辜負農人的期寄,它不嫌坡高谷深,沙礫壤土,只要你給它哪怕是能挺起腰身的空間,必要的水分和陽光,它就能豐厚地回饋你。玉米的生長速度是驚人的,它知道天光給它的時日不多,滿打滿算也不過三個多月一百來天,它要在這有限的時間內,去完成生命的飛躍!因此,它不敢耽誤每一分每一秒,從播種時起,它就制定好邁向秋天的里程表了:三天扎根,五天發芽,七天展葉,十天揚綠,半個月后,它就能跳出麥茬地搖曳生姿翹望秋天了!
那時在農村,土地是一個家庭的全部家當,莊稼是農民的命根子,任何時候都不能疏忽。每逢星期天或節假日,我都會從學校回來和家人一起在自家的責任田里揮汗如雨。這不,小麥剛剛入屯,父親也和大家一樣,攆著太陽奔著月亮,腳跟腳地播上了玉米,播下了他心中的愿想,然后數著日子,琢磨著時光,付予汗水,一天天等待著那個日子的姍姍來遲。閑下來時,我也常常撫摸著匍匐在胸前的一棵棵玉米,望著高遠的蒼穹發呆。我知道,我這是又開始憧憬著山那邊,水那邊,天那邊的世界了。
或許是我長期在農村生活久了,經常被荒野的風吹著,就越來越長得像田里的一棵玉米了。其實,我就是一粒玉米,只不過,我是被父親種在了知識的泥土里,并伴著父親種在大田里的玉米一起成長。上高中時,正趕上物質匱乏,父親送的小麥不夠吃時,往往是拿家里的玉米趕場救急。我就讀的高中坐落在一灣風景秀麗的洪河岸邊,河岸邊是周圍村子里的老農種的玉米田,一到夏天,玉米田蓊蓊郁郁的,總給人一種親切感,我常常坐在玉米田邊讀書學習。困了累了,我就合上書本,一邊摩挲著玉米棵一邊讓思緒飛得很遠。我想,家里的玉米田也該截腰深了吧,再過幾天,就該出穗揚花了吧,很快又到玉米收獲的季節了,等到金桂飄香的秋期,我又能拿著玉米贊助的錢交下個學期的學費了。這樣想時,似乎此時的天也藍了,河里的水也清了,遠處的山也碧了,山外邊的路也就不遙遠了。
說玉米是自家兄弟,不只我說,記得上初中時生物課本里也這么說:“玉米是個大肚漢,能吃能喝又能干。”說得一點兒不錯。能吃,是說玉米耐肥,別管是土雜肥,農家肥,也別管是現代科技合成的化肥,只要是肥,只要讓它吃飽,它總能加倍地償還你。為了讓玉米兄弟吃飽飯,天還不亮,我就早早地起床,拿著鏟子,挎著籃子,去雞們白天容易刨食的草棚下拾雞糞,到池塘邊鴨鵝們時常棲息的地方拾鴨糞鵝糞,平日里就下地弄草喂豬喂羊喂牛攢豬糞羊糞牛糞,夏天時,就和父親一塊兒把公路邊的草皮鏟下來,再潑上大糞制成高溫堆肥,總之,凡是能積肥的地方,我們都不放過。那時流傳著一句話:莊稼一枝花,全靠糞當家,只可惜,彼時條件有限,積的農家肥也有限,化肥更是奢侈,即便如此,玉米仍是莊稼中的佼佼者,沒有哪一樣莊稼能與之相比擬的。
說它能喝,是說玉米是喜水作物,能付出,就是水分不能缺。若是碰上好年景,不旱也不澇,老天爺三天一小場,五天一大場,瀝瀝啦啦的雨不斷溜兒,玉米就像手提著的一樣“噌噌噌”地往上躥。碰上旱天,父親就把家里的噴灌機拉來,把水泵插進河里頭,突突突地三天三夜不停歇,與天斗,與地斗,就是不能讓玉米兄弟受委屈。有了家人的悉心照應,到秋后,地里打的玉米堆成山,望去,場院里,路邊,樹底下,房頂上,冒尖尖的哪都是,實在堆不下,就編成辮子掛在屋檐下,窗欞上,樹上,黃橙橙的玉米連綿一片,看著堆的玉米像小山,父親的嘴巴笑得咧到了脖子上。有玉米兄弟作后盾,父親的腰也直了,說話時也有底氣了,好像腳也輕了,很遠的路,一抬腳就走到了。
心中有念,節奏不亂。玉米就仿佛山里的硬漢子,有吃有喝往前沖,沒吃沒喝也不歇著。有年夏天,豫南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災,其他莊稼幾乎沒有產量,玉米仍然獲得了大豐收。記得剛開始時,雨水還比較順利,一場接一場地下個不停,可誰知等玉米長到有半人深時,雨水卻戛然而止了。打那兒,火辣辣的太陽從東邊懟開了,一翅子晴了有一個多月沒下一滴雨,那時農民是靠天吃飯,沒有機井,等河里的水抽干了,父親只好在農田里打壓水井,用架子車從坑塘里拉水抗旱保秋,盡管父親流的汗似小溪,可還是沒能阻擋著旱魔的腳步,玉米旱成了地趴趴兒,摟起來能當柴,砍下來能擰繩,趕晌午時用火柴一點能冒煙兒,存不住氣的人,干脆割回家喂牲口算了,眼看快要立秋了,老天終于落了一場透犁雨,大豆和紅薯旱得枯蜷著腿,成了殘疾,玉米卻像打不垮的兵,抖抖身子又站了起來。記得那年俺家種的玉米品種是丹玉13,本來屬稀植大棒型,等掰下來時,玉米棒子和棒槌轱轆子一般大,喜見人。就是那年,收了玉米,父親給我買了一輛自行車,從此,我和外面世界的距離更近了。
玉米耐旱,這是有目共睹的。相比于旱,澇對于它更是小菜一碟了。且不說它那高大的身軀,僅是它那碩大的根系就使得它防風抗澇力大無比。玉米的根是復根,最下面的一層是須根,能深入地表土層里,支持著玉米堅不可摧;最外面,生得粗大肥壯,裸露在空氣里的這層根,叫氣生根,像是農民兄弟赤腳走路時露在外面的一排腳丫子,固定著玉米的身軀盎然挺立,頂風搏雨,傲視同儕。這又令我惦起了那年發洪水時,所有的矮桿作物:紅薯,大豆,芝麻,谷子,都被洪水埋頂淹死了,高粱呢,高是高些,但又顯得纖弱,洪水一來就繳械投降了,只有玉米兄弟抗爭在風里,和家里的石磙,磨盤,水井一樣,靜待著家人的歸來。記得那年漲水時,家里的糧食都因為過水霉爛了,在危難之時,是父親從自家地里掰回了玉米給我們煮煮吃,才度過了饑荒。
在那個年代,玉米的最大敵人好像并非是旱情和洪澇,因為畢竟發生歉收的年份占個例,還是正常年景的居多。權衡之下,雜草才是玉米生長道路上的攔路虎。那時節玉米地里的雜草可真洶涌啊,谷子豆子紅薯地里的雜草還好,鋤頭撥拉一遍就過去了,大塊的玉米田就難辦了,從出苗到入伏,不鋤個三遍五遍子總是過不了關。即使這樣,一到秋天,玉米田里的牛草,星星草,老驢拽,抓地龍,長秧子草,仍是半人深。暑假里,我常常和父親一起去玉米地里割青草,割回家的青草不光喂豬,更主要是喂牛。昔時沒有農業機械,畜力是農家最主要的生產力,割回家的青草先要過鍘才能飼喂,常言說牛馬一口兒,經養得很。鍘草通常由兩個人完成,往往是父親負責往鍘口里續草,我按鍘。
我喜歡秋天家人們迎接玉米回歸時的莊重儀式。秋天是收獲的季節:豆莢搖玲,稻禾舞蹈,野菊曼妙,雁陣高歌,溪水婀娜,秋蟲唱晚,大地一片金黃。瞅個晴好天氣,父親披著夕陽,趕著老牛,高興得像過年似的,哼著一曲土得掉渣的老歌,在村口大槐樹下自留地旁邊擇出一片空地,鏟平,套上石磙,碾壓成平平展展的一個叫場院的空地,開啟秋收模式。一切都準備停當之后,父親又趕著驢車,把在田野里已經恭候多時的玉米棒子請回來,脫粒成籽,攤在場院里接受陽光的親吻。看著滿天滿地堆著的玉米閃著金光,起著波浪,父親的臉笑成了一朵菊花,成群結隊的鳥兒也趕來助陣,共同慶祝這個豐收喜悅的時刻。我也放下在學校里讀得泛著毛邊的課本,偷得浮生半日閑,一邊幫家里晾曬秋糧,一邊在不著邊際地想著心事。來這里光顧的鳥兒可真多啊,五彩斑斕的雉雞,花肚皮的喜鵲,藍尾巴的馬喳,長腿的白鸛,圍著粉紅頭巾的山雀,叫聲婉轉的鷓鴣,偷一把米就走的斑鳩,灰不溜秋的麻雀,還有引吭高歌排陣長空的大雁,它們一波一波地來,又一波一波地去,有的鳥兒走了又回來了,有的鳥兒走了就再也沒有回來,只有這些灰不拉幾的麻雀留了下來,伴著家鄉永不變調兒的風,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園時光。此刻,我常常把自己比喻成那只麻雀,可有誰知,我多想是天空那只大雁,飛越高山,森林,草原,大海,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啊!
在一個金色的秋里,我考學走了,父親送我時說,還是玉米兄弟給了我盤費,讓我終于如愿以償,走出了那個逼仄的農村,才得以在一個更廣闊的天地里扎根,然后開枝散葉,葳蕤蓬勃。
感謝玉米兄弟的一路陪伴。
作者簡介:
張富存,河南省作協會員,奔流文學院第十七期研修班學員。作品散見于《海外文摘》《散文選刊》《奔流》《時代報告》《河南文學》《西部散文選刊》《青年文學家》《河南日報·農村版》《老人春秋》《駐馬店日報》等報刊,獲2021年度全國散文年會征文二等獎,多次入選《河南文學作品選散文卷》,并被多省市高考模擬試題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