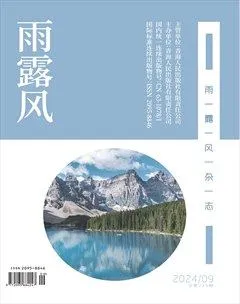李娟散文《遙遠的向日葵地》生態意識探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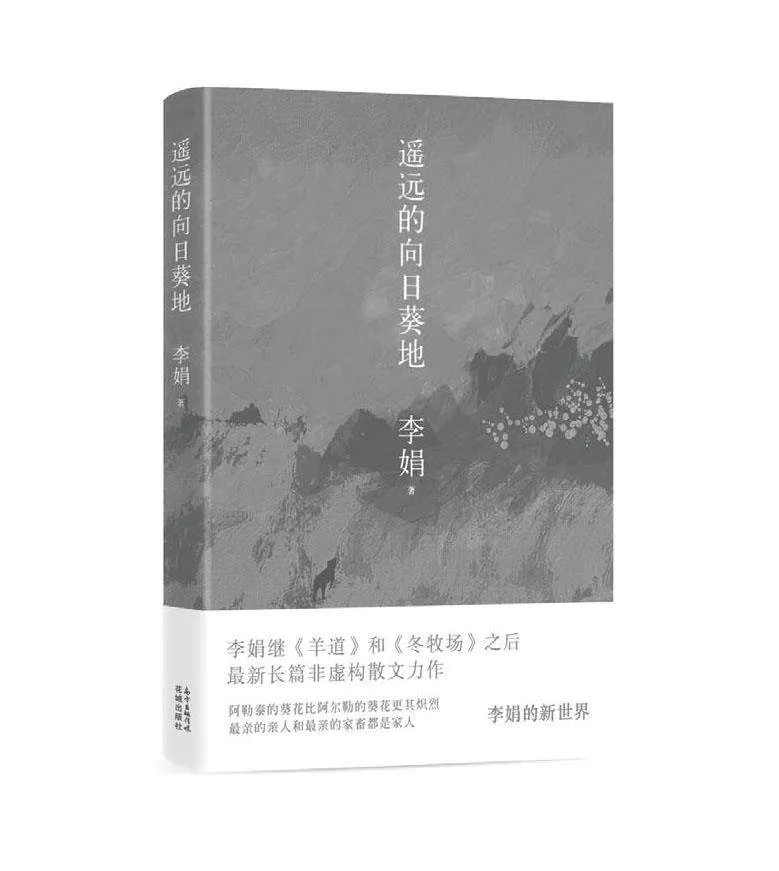
李娟的散文《遙遠的向日葵地》表現出強烈、自覺、客觀的生態意識。作者擁有難能可貴的自我反思精神,為自身作為生態資源“掠奪者”感到自責、不安,反思生態環境遭到破壞背后的人類文化因素。自然地理環境的影響是李娟獲得生態意識的主要因素,在與大自然的親密接觸中,李娟產生了主體間性的生態整體意識。相較于之前的《我的阿勒泰》《阿勒泰的角落》《冬牧場》以及“羊道”系列,《遙遠的向日葵地》打破了“地域書寫”“非虛構書寫”的標簽,由介入和關照哈薩克民族的生活趨轉為真摯“向內轉”的自我關注,由淺層的感性描摹轉變為深入的理趣思考,其中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生態意識書寫也變得更加深入、成熟。
一、《遙遠的向日葵地》中生態危機的呈現及反思
《遙遠的向日葵地》用想象和經驗描繪了一個生態被嚴重破壞的荒地空間。荒地空間處于前現代的狀態,保持著一種尚未大量開發的原生狀態,每一次人為改造自然的行動都會引起較為明顯的外貌改變。“死掉的土地”堅硬、發白,看上去像無邊無際的白色搓衣板,“表層板結得異常平整光潔,寸草不生,毫無生氣。像一塊死去的皮膚,敷在大地的肉身之上。”[1]230-231在淡淡的甚至略顯冷漠的敘述中,其實包含更多的是李娟對生態景觀破壞的感喟及無法接受,作者雖沒有直接表露這些情緒,但悔恨與不安的情緒似箭在弦,蓄勢待發,在對大地觸目驚心瘡口的白描展示中,對于生態破壞的反思也到達了無聲勝有聲的地步。生態的破壞也使得動植物、自然資源發生了改變。想象與經驗的交織視角使“我”看到了幽陰處的物種命運發生了變化:石頭下的蟲子王國毀滅、植物白嫩的根系曝曬于日光中,“億萬萬蟻窩和蟲穴的毀滅,億萬萬微小的驚駭與怨恨游蕩于天地之間”[1]162;河中的魚隨著定居者的出現數量由多變少、體型由大變小,隨著我們一家的到來,魚彼此間一條遠離一條,深深隱蔽在水底陰影處,魚的數量、體型與人的活躍度形成了反比例關系;發電站使得水被截流,生態生生斷裂,魚類回溯和產卵的道路被封堵。工業和科技給人類帶來了極大的便利,但也改變了物種的休憩繁衍,而人類本就根植于生物圈,一旦生物圈走向紊亂,人類的生存也必定受到威脅。
面對嚴重的生態問題,作者認識到人類的行為是導致生態沖突與生態危機的根源,其間有對人類文化、思想、歷史等的自責與反思。然而作者并沒有以凌虛高蹈的姿態進行教導、言說,也沒有以旁觀者的姿態批判人類行徑的貪婪、狂妄,而是從自我經驗與體悟出發,將生態資源損耗的矛頭真誠地指向自身,以難能可貴的自我反思精神進行自我審視。在《繁盛》一文中,“我們一家”在這片土地上種滿了對地力損耗極大、收益卻極高的向日葵,像極了最開始來這片土地上肆意開發、掠奪自然資源的定居者,這一宿命式的、悲劇性的“掠奪者”身份承襲的閉環結構,象征著生態問題在人類一代代的發展中不斷惡化,蘊含著作者強烈的生態危機反思意識。在《石頭》中“我”喜歡撿各種顏色絢麗的石頭,這是一種不牽涉利益的喜愛、欣賞,與商人們在戈壁灘上使用機器大量暴力開采玉石的行為形成了鮮明對比。起初認為自己撿石頭不足以影響真正的現實世界,然而面對全人類為攫取利益損害戈壁灘生態環境,甚至自己的母親也在用石頭送禮的行為,“我”無法將自己從全人類中全然抽離、置身事外,文章的最后沒有站在旁觀者的視角批判人類行為,而是把全人類的暴行全都置于個人名義之下,將人類對于審美能力缺失的文化危機看作是自己的責任,因此是“我”改變了季節、氣候、降雪量,甚至是冰川融化、雪線后退、全球變暖。作者以生態整體主義的視角,強調每個人都是良好生態構建的一個主體部分,生態的保護需要每個人參與。
李娟的《遙遠的向日葵地》將生態整體視為觀照對象,從自身的經驗、情感出發,批判人類主體膨脹的欲望,檢視工業化、現代化帶給自然環境及生命的傷害,體現出一種強烈而自覺的生態意識。
二、《遙遠的向日葵地》中生態意識的主要來源
一個作家的生態意識來源可能是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結果。例如生態危機現象的直接刺激、自然環境的浸染、中外文學的熏陶、宗教文化的借鑒、民族文化的吸收、作家個人氣質與個性的加持等,都有可能造成作家生態意識的形成與成長。對于李娟來說,她的生活經歷較為特殊,與遠離城市和工業商業文明中心的牧場有著較多的親密接觸,這是她確立尊重自然生命內在價值生態意識的最為關鍵的原因。
李娟1979年出生于新疆奎屯,籍貫四川樂至縣,童年時期不斷輾轉于四川、新疆兩地。少年時期經常跟著媽媽、姥姥和哈薩克族牧民轉場、遷徙、做生意。2000年高中輟學的李娟已經在烏魯木齊打工一年多,同年夏天從工廠辭職,回到沙依橫布拉克夏牧場的雜貨店,和媽媽姥姥一起生活。不久后,姥姥因摔跤癱瘓,為了方便給姥姥治療,李娟離開牧場,在縣城醫院附近租了一個房子,一邊照顧姥姥,一邊寫作。2003年,李娟在朋友的幫助下進入機關上班,結束了多年的動蕩生活。2007年李娟離開機關辦公室,進入扎克拜媽媽家生活三個月。2008年,李娟正式從機關辭職,前往江南一帶工作,并戀愛。這一年,她的媽媽決定種葵花。自2013年起,李娟供職于新疆文聯,2017年11月《遙遠的向日葵地》首次出版。2008年是中國現代化進程快速推進的時期,阿勒泰地區的原生生態環境發生巨大變化,這成為李娟思考生態平衡的一個刺激點,而多年在牧場、山區生活的經歷牽引出了李娟思想中潛隱的生態意識。
大自然中的各種各樣的生命及自然環境啟發了李娟的生態意識,它們觸動作者情感的同時,作者的內心對其亦有所回應,自然和人之間相互開啟生命價值與意義,保有精神默契。
在《遙遠的向日葵地》中李娟常以單要素入文,比如雞、鴨子、兔子、石頭、蜂蜜、沙棗等,人在喂雞、趕牛、撿石頭、摘沙棗、聞花香等動作中參與自然、寓居于自然,人與自然在交互感知中發生共振,構成了一個須臾難分、水乳交融的生態整體。以向日葵的地理物象為例,人和植物之間共振的命運和難分難解的聯系消解了主客二分的隔膜,從而呈現出人與植物之間互相照亮生命意義的生態審美韻味。在散文集碎片化的記憶敘述中穿插著兩條彼此纏繞的主線,一條是向日葵的生長時間線,另一條是人在種植過程中的情感線。在向日葵的成長時間線中,從播種到稀稀拉拉地抽芽,再到茁壯繁盛地長出花盤,最后到成熟,向日葵順應農時,在人悉心照顧下最終完成生長周期。在人的情感線中,播種時人面對荒蕪干旱的野地,在一遍遍“這能長出來什么”的質疑聲中否定自身的勇氣和這片土地的未來;當向日葵已經開出手掌心大小的花盤,“我”還是在不斷猶疑它們是否真的能存活下去;直到向日葵已經成長為一片植物海洋,蒙古包可以在綠色的海洋中隨波蕩漾,花稈整齊茁壯,花盤金光四射,“我”感受著人與地之間的心靈感應:“它產生的財富滋養我們的命運,它的美景糾纏我們的記憶,與它有關的一切,將與我們漫長的余生息息相關。”[1]126再到后來葵花成熟,黑壓壓的葵花籽飽滿地頂出花心,所有人都投身于豐收的忙碌之中,滿當當的葵花籽看在眼里令人喜悅,向日葵不僅總是與美好、激情、勇氣相關,“它們遠不止開花時燦爛壯美的面目,更多的時候還有等待、忍受與離別的面目”[1]254,作者不僅是在寫植物,也是在寫葵花地中落魄、不安、窘迫、遺憾的人的命運。“我”在憐惜沙棗林中麻雀短暫生命的時候,在同情鵝喉羚為了生存不惜冒著危險啃食農作物的時候,也不忘關懷人的艱難生存和生命的脆弱。在與自然物相處的過程中,李娟并沒有將它們當作獲得感官愉悅的對象,也沒有把它們當作寄托思想情感的載體,而是將其視為共同體,與具體的自然物種或個別自然物確立了主體間性關系,擺正了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從貧瘠到豐盈,從絕望到希望,自然的物性和人的情感交相輝映,人真正地在和自然的互相陪伴、互相成長中獲得生態整體主義思想。
李娟散文中的生態意識是其特有的思維模式與民族精神的表現,是其特有的地理環境的產物。在李娟的詩性思維的想象書寫中,自然環境和自然物有著自身的主體性,人與自然處在一種互相賦予生命價值的平等地位,并且負有彼此守護、照料的責任。獨特的自然地理空間極大地影響了李娟對于人與自然環境、人與非人類生命體之間關系的體悟。
三、散文《遙遠的向日葵地》中生態意識的意義
“散文與小說、戲劇等文體最大區別在于,它有著其他文學樣式所沒有的‘自我表現’——一種率真的、裸露靈魂的直覺表現”。[2]生態文學作家在創作時,一定不能為達到表達生態思想這一目的而照搬和套用生態理論而忽視主體情感的中介作用,因為過于明確的表意行為會遮蓋其作品的美學追求。中外文學史上最好的作品都是認真思考和呈現人類的生存處境,關懷人的靈魂和感情,呈現人希望和恐懼的本真文學,如果生態文學缺失了主體的情感、想象與創造,只在社會現實、社會實踐等平面空間上觀光游覽,僅僅是通過展現外部環境表達生態意識,那么生態文學就很難看到生態危機背后更為幽隱精微的人性思考;死板地按照生態理論來創作甚至會掉進激進生態中心主義的陷阱,一味強調自然和非人類生命體利益與權力的至高無上,貶低人的價值、否定人的生存權利、否定人在生態系統可以承載的限度內進化發展,讓人類無條件退出荒野,其文學作品的審美意蘊難免要被削減一部分,作為生態文學獲得支柱性力量的深邃哲理也在主體情感的缺位中喪失,只有在個人認知的視角和個人思想的浸潤之下,最終才能在文本上進行最有力的感染力和完好藝術性的表達。二者的融合,是客觀世界的“大道”與主觀世界的“小道”的統一,以辯證、完整地實現生態文學的書寫價值與意義。
《遙遠的向日葵地》書寫自我真實見聞、抒發自我內心情感,構成了李娟散文真實性的向度,傳達出一個真實自我的為文品格。她在展現生態危機、反思人類文化、體現了一名作家的社會良知與擔當的同時,也在以一名農民的角色觸摸天空大地、深入現實農業生活,從內心深處真誠地書寫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當人與自然或非人類生命體產生沖突時,李娟展現出相當冷靜且辯證的思考。一方面,她意識到現代化進程中造成的生態危機反噬了人類,促使人類改錯和贖罪,促使人類修正人類主義驕狂虛妄的部分,秉持生態整體主義思想,注重人對自然的“善”,重視人發揮主體性和能動性去保護自然、維護生態平衡,并探尋和揭示造成生態危機的社會根源,表達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自覺生態意識;另一方面,李娟又能夠從真實的情況出發,沒有掉進陷入貶低人的價值、否定人的生存權利、否定人在生態系統可以承載的限度內進化發展的極端生態中心主義陷阱。摒棄人類中心主義絕不意味著自然是壓迫人的神圣力量,而是應當建立與自然友好相處的主體間性關系。李娟體恤人的生存之艱辛,肯定人在荒地中創造奇跡與希望的強大意志力,看到了人與自然能夠建立友好相處的主體間性關系的一面,其散文在生態書寫之間彰顯了一種溫情色彩和相背的審美張力。“現代性建構應該有其強大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批評、自我更新、自我淘汰功能,如果做作的、矯飾的、虛情的浪漫主義情緒控制了作者的審美自覺,鄉土敘事可能淪為意義愈加空洞爛俗的符號,成為偽傷感主義的廉價點綴,一不小心,這種懷舊真的走到了文人所期待的相反的路徑。”[3]只有從本土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內心最真實的體驗出發,作家筆下流露出的生態意識才有可能探索出更有深度的現實、歷史和生命的內涵。
四、結語
21世紀伴隨著“人類紀”與生態文明時代的到來,意味著人類要反思與改變自己的行為方式,生態問題已經成為全球性的棘手問題,而中國要走向生態現代化文明必須保證生態文化的建設與發展。李娟的散文《遙遠的向日葵地》經歷十年的記憶沉淀,用柔軟細膩、真實質樸的筆端觸及內心深處隱秘的不安,在仰天俯地、擁抱自然、審視自我的姿態中探尋和揭示生態危機的社會根源,呼吁人們保護大自然、善待大自然,與自然界的萬物和諧相處。她將面對自我和世界感性經驗的自由書寫镕鑄到對21世紀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中頗具時代感的生態思考中,在新疆生態環境中探尋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的審美路徑。
作者簡介:劉甜擔(2000—),女,漢族,山東棗莊人,碩士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為中國當代文學。
注釋:
〔1〕李娟.遙遠的向日葵地[M].廣州:花城出版社,2017.
〔2〕吳周文.散文文體自覺與審美訴求[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20.
〔3〕黃軼.生態批評的偏誤[J].南方文壇,2011(5):9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