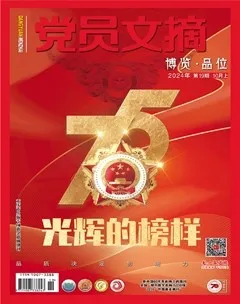抗拒長(zhǎng)大的真正原因,是恐懼

一
有許多的人,在許多的時(shí)刻,心中都會(huì)或明或暗地浮現(xiàn)出拒絕長(zhǎng)大的念頭。
我的小說(shuō)《四十一炮》,主人公羅小通,他的身體已經(jīng)成年,但他的精神還停留在少年。
拒絕長(zhǎng)大的心理動(dòng)機(jī)——源于對(duì)成人世界的恐懼,源于對(duì)衰老的恐懼,源于對(duì)死亡的恐懼,源于對(duì)時(shí)間流逝的恐懼。
羅小通試圖用喋喋不休的訴說(shuō)來(lái)挽留逝去的少年時(shí)光。
而我企圖用寫(xiě)作挽住時(shí)間的車(chē)輪。仿佛一個(gè)溺水的人,死死地抓住一根稻草,想借此阻止身體的下沉。盡管這是徒勞的,但不失為一種自我安慰的方式。看起來(lái)是小說(shuō)的主人公在訴說(shuō)自己的少年時(shí)光,但其實(shí)是作者讓小說(shuō)的主人公用訴說(shuō)創(chuàng)造自己的少年時(shí)光,也是用寫(xiě)作挽留自己的少年時(shí)光。
借小說(shuō)中主人公之口,再造少年歲月,與流逝的時(shí)光抗衡,這是寫(xiě)作這個(gè)職業(yè)可以驕傲之處。所有在生活中沒(méi)有得到滿(mǎn)足的,都可以在訴說(shuō)中得到滿(mǎn)足。
這也是寫(xiě)作者的自我救贖之道。
二
在這樣的創(chuàng)作動(dòng)機(jī)下,訴說(shuō)就是目的,訴說(shuō)就是主題,訴說(shuō)就是思想。如果非要給這部小說(shuō)確定一個(gè)故事,那么,這個(gè)故事就是一個(gè)少年滔滔不絕地講故事。
所謂作家,就是在訴說(shuō)中求生存,并在訴說(shuō)中得到滿(mǎn)足和解脫的過(guò)程。
與任何事物一樣,作家也是一個(gè)過(guò)程。許多作家,終其一生,都是一個(gè)長(zhǎng)不大的孩子,或者說(shuō)是一個(gè)生怕長(zhǎng)大的孩子。當(dāng)然也有許多作家不是這樣。
生怕長(zhǎng)大,但又不可避免地要長(zhǎng)大,這個(gè)矛盾,就是一塊小說(shuō)的酵母,可以由此生發(fā)出很多的小說(shuō)。羅小通是一個(gè)在訴說(shuō)中得到了滿(mǎn)足的孩子。
訴說(shuō)就是他的最終目的。羅小通講述的故事,剛開(kāi)始還有幾分“真實(shí)”,但越到后來(lái),越成為一種亦真亦幻的隨機(jī)創(chuàng)作。訴說(shuō)一旦開(kāi)始,就獲得了一種慣性,自己推動(dòng)著自己前進(jìn)。在這個(gè)過(guò)程中,訴說(shuō)者逐漸變成訴說(shuō)的工具。與其說(shuō)是他在講故事,不如說(shuō)故事在講他。
訴說(shuō)者“煞有介事”的腔調(diào),能讓一切都變得“真實(shí)”起來(lái)。
一個(gè)寫(xiě)小說(shuō)的,只要找到了這種“煞有介事”的腔調(diào),就等于找到了那把開(kāi)啟小說(shuō)大門(mén)的鑰匙。當(dāng)然這只是我的一種感悟,無(wú)論是淺薄,抑或是偏執(zhí),也還是說(shuō)出來(lái)。
其實(shí)這也不是我的發(fā)明,許多作家都感悟到了,只是說(shuō)法不同罷了。
三
這部小說(shuō)中的部分情節(jié),曾經(jīng)作為一部中篇小說(shuō)發(fā)表過(guò)。
但這絲毫不影響這部小說(shuō)的“新”,因?yàn)槟侨f(wàn)字,相對(duì)于這三十多萬(wàn)字,也是一塊酵母。
當(dāng)我準(zhǔn)備了足夠的“面粉”和“水分”,提供了合適的“溫度”之后,它便猛烈地膨脹開(kāi)來(lái)。
羅小通在講述自己故事的時(shí)候,從年齡上看已經(jīng)不是孩子,但實(shí)際上他還是一個(gè)孩子。
他是我諸多“兒童視角”小說(shuō)中的兒童的一個(gè)首領(lǐng)。他用語(yǔ)言的濁流,沖決了兒童和成人之間的堤壩。也使我的所有類(lèi)型的小說(shuō),在這部小說(shuō)之后,彼此貫通,成為一個(gè)整體。
在寫(xiě)作這本書(shū)的過(guò)程中,羅小通就是我。
但他現(xiàn)在已經(jīng)不是我了。
(摘自《感謝那條秋田狗》浙江文藝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