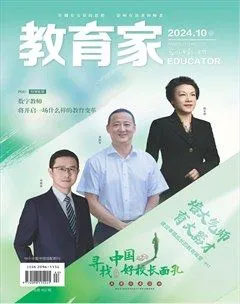語言暴力,傷心也傷腦
家庭本應是孩子溫暖的港灣,父母本應給予孩子無條件的愛,但是,有的孩子在家中卻深受傷害。“你怎么這么笨?”“為什么別人能做到,你就做不到!”很多人在成長過程中都聽到過類似的言語,乃至到成年也難以釋懷。“父母為什么不會好好說話?”“父母語言暴力是一種怎樣的體驗?”類似的發問在網絡上屢見不鮮。
美國的愛荷華大學就曾經對親子溝通做過相應的調查,調查結果顯示:父母在和孩子溝通過程中,鼓勵的話語僅占不到30%,超過70%的話語都是打壓孩子的。我國相關研究機構的調查結果顯示,親子溝通中存在的語言暴力現象也不容樂觀。2023年中國兒童中心聯合首都師范大學、北京大學開展中國兒童校外生活狀況調查發現,受訪家庭中有三成左右的家長經常或總是批評孩子。
語言暴力是指通過語言對他人施加的心理或情感傷害,包括直接的辱罵、嘲笑、貶損、諷刺、威脅,以及那些更為隱蔽的、帶有控制和貶低性質的言語。可以說,語言暴力造成的負面影響與目睹家庭暴力、非家庭造成的童年期虐待相當,甚至比父母造成的身體虐待還要嚴重。看似“輕飄飄”“無形”的語言到底是如何化為利刃在孩子們心中留下難以磨滅的暴力之傷的呢?腦科學的相關研究發現將告訴我們語言暴力會給孩子的大腦結構和發育帶來什么樣的影響。
語言暴力“傷心”又“傷身”
有人認為,吼孩子兩句沒什么大不了,又不會在身體上留下傷痕。實際上,情感虐待對心理功能的損害可能和身體虐待一樣嚴重。2011年的一項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研究顯示,當一個人在情感上體驗到強烈的厭惡和排斥時,情緒疼痛在大腦次級軀體感覺皮層和背側后腦島的激活模式與被試經歷身體疼痛時的激活模式極為相似,也就是說,他們的大腦會真真切切地產生“疼痛”體驗。從這個角度上講,語言暴力所帶來的情感傷痛和體罰一樣會讓孩子“身心俱痛”。
人類天生傾向于更多地關注潛在的危險或負面信息,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也往往更容易關注、記住負面的事物和信息,這種現象被稱為負面偏差效應,它對我們的情緒、決策和行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負面偏差效應是人們適應社會和進化的產物,使個體能迅速地發現威脅,是個體賴以生存的一種自我保護機制,也是在長期進化過程中形成的一種自動化加工。有研究發現,消極刺激誘發的事件相關腦電位振幅要大于中性和積極刺激,即負面信息使大腦更加“興奮”。也有研究者用現實中的政治新聞作為材料進行實驗,發現被試接觸負面新聞時的皮膚電導率更高且心率更低,這意味著此時被試被更大程度地生理喚醒,且專注度更高。暴力的語言本質上是一種消極信息,因此,孩子對于批評、辱罵、威脅等語言信息的反應往往比對贊美更為深刻和迅速,他們能夠更精確地記住和回憶那些令人泄氣或傷害自尊的言辭。
另外,人類通過不同的系統對積極信息和消極信息進行加工。加工情緒的大腦回路包括前額皮層、杏仁核、海馬、前部扣帶回、腹側紋狀體等。前額皮層中的不對稱性與趨近和退縮系統有關,左前額皮層與積極情緒加工和趨近行為有關,右前額皮層與消極情緒加工和退縮行為有關。杏仁核容易被消極的情緒刺激所激活,尤其是恐懼。因此,在親子關系中,正面事件無法輕易抵消負面事件的影響,消極語言的影響更為突出,語言暴力更容易被注意、被加工,也更容易被保留。
語言暴力對大腦結構帶來的不良改變
通常認為,一般人的語言中樞位于大腦左側半球的顳葉皮層,其中,顳上回主要對聽覺信息進行初步加工,顳上回后部屬于聽覺性語言中樞威爾尼克區,與言語的聽覺信息處理與理解能力有關。美國哈佛大學醫學博士馬丁·泰徹爾(Martin Teicher)開展的一項基于體素的形態測量學(VBM)研究顯示,童年時期經歷過父母言語暴力的被試,其左側顳上回灰質體積與父母的言語攻擊水平呈顯著正相關關系,與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呈負相關。在此項實驗中,相比于普通被試,童年時期經歷過父母言語暴力的被試左側顳上回灰質非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大了14.1%。這說明,顳上回灰質體積較小反而可能是健康發育的典型表現。對此一種可能的解釋是,具有較高教育水平的父母可能傾向于為他們的孩子提供更多、更豐富的語言刺激,使得其語言發育神經通路在青春期結束前經過了大量修剪,這種大量修剪有利于語言聽覺理解能力的正常發展。可見,語言暴力的早期經歷會影響到此處大腦皮層結構的發展通路,會通過減少神經抑制的方式造成左腦語言神經系統發育的緩慢。
除了對大腦皮層灰質的影響,語言暴力還會影響大腦皮層下的白質纖維束。一項彌散張量成像(DTI)研究探索了父母的嚴重言語虐待(如嘲笑、羞辱和蔑視)對孩子大腦皮層下神經通路整合性的影響,結果發現,父母言語虐待影響的神經束主要有三處:左側顳上回皮層下的弓形束、左側海馬后尾旁的扣帶束及穹窿左側。弓狀束連接著位于顳頂葉交界處的威爾尼克區和額下回的布洛卡區,前者是負責言語理解的聽覺性語言中樞,后者是負責言語生成的運動性語言中樞。同時,弓形束還為前額葉皮層接收和調節聽覺信息提供了一條通路。扣帶束連接邊緣系統和新皮質,易受壓力的影響。左穹窿連接著海馬中隔系統,在焦慮的調節中起著重要作用。這項研究結果顯示語言暴力會對皮層下的神經通路造成消極影響,進而影響個體的言語智商和言語理解,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家長輔導作業時,提高音量不僅無助于孩子的學習,反而適得其反。
此外,也有研究發現,沒有親身經歷而只是目睹父母的語言暴力行為也會對兒童的大腦結構產生負面影響。目睹家庭暴力是一種與抑郁、創傷后應激障礙和智商降低風險增加相關的童年創傷經歷。2012年一項關于目睹家庭語言暴力是否與白質纖維束完整性有關的彌散張量成像研究顯示,被試左枕葉的下縱束結構異常與童年目睹父母言語攻擊的時間長短和7至13歲期間的語言暴力暴露程度有關。下縱束連接枕葉和顳葉,是視覺邊緣通路的主要組成部分,為視覺特有的情感、學習和記憶功能提供支持。這一發現證實兒童目睹虐待的經歷與額葉、顳葉或邊緣系統的纖維通路的改變有關。
以上來自腦科學研究的證據顯示,語言暴力不僅在大腦皮層結構水平上影響語言發展通路的發育,也會在大腦皮層下白質纖維束的水平上影響個體感覺系統的正常發育,進而影響其感官信息的感知、處理和整合,導致感覺尋求或回避等問題行為風險增高,如成癮行為、社交困難等。
如何做到親子間的非暴力溝通
語言暴力一旦出現在孩子的生命歷程中,就會在大腦中留下難以磨滅的負面影響。因此,在親子溝通中,要盡量避免語言暴力的發生。
那該如何說、如何做,才能在親子溝通中避免語言暴力呢?馬歇爾·盧森堡博士在《非暴力溝通》一書中提出,非暴力溝通包含“觀察、表達、需要、請求”四個步驟。
步驟一:觀察。所謂觀察,通俗地說就是此時此刻看到的是什么。在親子溝通時,首先要摒棄評價式的語言,避免帶著主觀的想法、情緒和猜測來展開交流,而應該用觀察式的語言客觀、具體地描述當下發生的事實。
步驟二:表達。就自己看到的事情表達感受,比如開心、高興、氣憤、害怕等,簡單說就是“少說想法,多說感受”。家長多表達對孩子情緒和感受的共情與接納,孩子才能感到放松和安全,才愿意繼續交談下去。
步驟三:需要。在親子溝通中,要充分了解彼此的感受和需要,表達自己“需要什么”,同時傾聽孩子的需要。可以嘗試用“我感到……因為我……”的句式有意識地去正向表達自己的需要。
步驟四:請求。在運用了前三個步驟,表達出觀察、感受和需要之后,家長可以以請求的方式向孩子表達這些期望,引導孩子自主選擇。要多用正向的說法,而不是負向的表達,不斷地引導孩子思考并找到更多、更好的方法,學會解決問題的思維方式。
傾聽孩子的心聲,與孩子進行平和、平等、尊重的對話,和孩子一起尋找改變的辦法,從而避免語言暴力的發生,是更有建設性的親子溝通方式。
【本文系科技創新2030-腦科學與類腦研究重大項目“中國學齡兒童腦智發育隊列研究項目”(項目號:2021ZD0200500)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