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被看見的情緒勞動,永遠沒完沒了
母親節那天,我要了一份禮物:房屋清掃服務。具體來說,是清掃衛浴和地板,如果加洗窗戶的費用也合理的話,那就一并清洗。對我來說,這個禮物與其說是打掃屋子,不如說我終于可以擺脫家務責任一次。我不必打電話向多家家政公司詢價,不必研究及比較每家公司的服務質量,不必付款及預約清掃時間。我真正想要的禮物,是擺脫腦中那個老是糾纏著我的情緒勞動。
我丈夫等著我改變主意,換成一份比房屋清掃服務更“簡單”的禮物,例如他可以上亞馬遜一鍵下單的東西。但我堅持不改,他失望之余,在母親節前一天終于拿起預約電話,但詢價后覺得太貴了,信誓旦旦地決定自己動手。其實我真正想要的,是希望他上臉書請朋友推薦幾家家政公司,自己打四五通電話去詢價,體驗一下這件事要是換我來做,勢必得由我來承擔的情緒勞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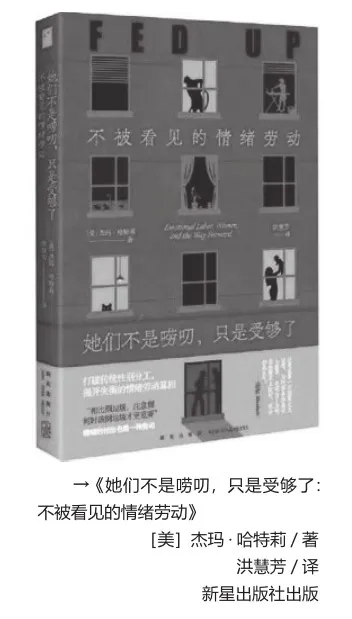
結果母親節那天,我收到的禮物是一條項鏈,我丈夫則躲去清掃衛浴,留下我照顧三個孩子,因為那時家里其他地方一片混亂。他覺得,自己正在做我最想看到的事——給我一個干凈如新的浴室,而且不必我自己動手清洗。所以當我經過浴室,把他扔在地板上的鞋子、襯衫、襪子收好,卻絲毫沒注意到他精心打掃的衛浴時,他很失望。
我走進衣帽間,被一個擱在地板上的塑料儲物箱絆倒——那個箱子是幾天前他從高架子上拿下來的,因為里面有包裝母親節禮物所需的禮品袋和包裝紙。他取出需要的東西,包好他要送給母親和我的禮物后,就把箱子擱在了地板上,儲物箱就變成礙眼的路障,也是看了就生氣的導火線。每次我要把換洗衣服扔進臟衣簍,或是去衣帽間挑衣服來穿時,那個箱子就擋在路中間。幾天下來,那個箱子被推擠、踢踹、挪移到一旁,但就是沒有收回原位。而要想把箱子歸位,我必須從廚房拖一張椅子到衣帽間,才能把它放回高架子上。
“其實你只需叫我把它放回去就好。”他看到我為箱子心煩時這么說。
這么明顯的事情。那個箱子就擋在路中間,很礙事,需要放回原位。他直接把箱子舉起來、放回去,不是很簡單嗎? 但他偏偏就是繞過箱子,故意忽視它兩天,現在反而怪我沒主動要求他把東西歸位。
“這正是癥結所在。”我眼里泛淚,“我不希望這種事還要我開口要求。”一個顯而易見的簡單任務,對他來說只是舉手之勞,為什么他偏偏不肯主動完成? 為什么非得我開口要求不可?
這個問題促使我含淚據理力爭。我想讓他了解,為什么當一個家務管理者,不僅要發現問題、分配家務,還得若無其事地要求大家配合是那么累人的事;為什么我會覺得自己承擔了所有的居家打理責任,使其他人免于承受心理負擔。有事情需要處理時,只有我注意到,而且我的選擇很有限,要么得自己完成,不然就得委托別人來做。家里牛奶沒了,我得記在購物清單上,或是讓丈夫去超市購買,即使最后一口是他喝光的。家里的衛浴、廚房或臥室需要打掃時,也只有我注意到。再加上我十分注意所有細節,往往導致一項任務暴增成二十項。我把襪子拿去洗衣間時,注意到有個玩具需要收起來,于是我開始動手整理游戲室,接著我又看到一個擱在一旁的碗沒放入水槽,于是我又順手洗了碗盤……這種無止境的循環令人煩不勝煩。
家務不是唯一令人厭煩的事。我也是負責安排時間表的人,隨時幫大家預約行程,知道行程表上有哪些待辦事項。我也知道一切問題的答案,比如我丈夫把鑰匙扔在了哪里、婚禮何時舉行及著裝規定、家里還有沒有柳橙汁、那件綠毛衣收在哪里、某某人的生日是幾號、晚餐吃什么,等等,我都知道。我的腦中存放著五花八門的清單,不是因為我愛記這些事情,而是因為我知道其他人都不會記。沒有人會去看學校的家長聯絡簿,沒有人會去規劃朋友聚餐要帶什么餐點前往。除非你主動要求,否則沒有人會主動幫忙,因為一直以來都是如此。
然而當你主動要求,并以正確的方式要求時,又會是一種額外的情緒勞動。我希望丈夫打掃院子,但又想維持婚姻和諧時,必須注意自己講話的語氣,以免言語間流露出些許的怨恨,因為要是我不主動提醒,他永遠不會注意到院子需要打掃了。
那個母親節迫使我潸然淚下的原因,不單是那個一直擱在地上的礙眼儲物箱,也不是因為丈夫無法送我真正想要的禮物,而是經年累月下來我逐漸變成家中唯一的照護者,照顧每件事、每個人,而所付出的勞心勞力完全不被看見。當我意識到自己無法向丈夫解釋為何如此沮喪時,我終于達到情緒爆發的臨界點,因為我再也找不到那些情緒的源頭了。
我這輩子已經習慣了超前思考,預測周遭每個人的需求,并深切地關心他們。情緒勞動是我從小就接受的一項技能訓練。相反地,我丈夫從來沒受過相同訓練,他懂得關心他人,但他并不是體貼入微的照顧者。然而,當我認為自己不僅是那份工作的更好人選,更是最佳人選時,那也表示我把一切事情都攬在了自己身上。我比較擅長安撫孩子的脾氣,所以這件事情由我來做。我比較擅長維持屋內整潔,所以我負責絕大多數的打理及任務分派。我是唯一在乎細節的人,所以由我來掌控一切是很自然的事。當他不需要我開口就主動完成一項任務,并承擔過程中的精神負擔時,那是在對我展現“美意”。但同樣的任務由我來做時,卻無法指望同樣的回報。對我來說,情緒勞動變成一個競技場。
我感到憤怒,精疲力竭。我不想戰戰兢兢地走在一條微妙的分隔線上,一邊要顧及他的感受,一邊又要清楚傳達我的想法。我不想事無巨細地管理家里所有大事小事,我希望另一半可以跟我一樣主動積極地面對家務。不過我試圖向丈夫解釋這點時,他很難理解“倒垃圾”和“注意何時該倒垃圾”的差別。只要任務完成了,管他是誰要求完成的! 那有什么大不了的? 聽他這樣反問時,我一時也不知道該如何解釋。
最終,我決定把導致那一刻混亂的所有掙扎和沮喪寫下來,以專文發表在《時尚芭莎》上。我知道有些女性馬上就抓到了我那篇文章想表達的重點,因為我們每天都在做這種隱形工作。當這篇《女人不是嘮叨——我們只是受夠了》以驚人的速度被瘋狂轉發時,我還是很驚訝。數千名讀者留言及評論,很多女性紛紛分享她們的“母親節時刻”,她們也遭遇過伴侶不明就里的反駁,不知該如何解釋自己的所思所想。數百萬來自各行各業的婦女紛紛點頭說:“是啊,我也是!”那個聯結時刻令人欣慰,也令人灰心。我不禁納悶:“為什么現在才引起那么大的回響?”
我并非第一個思考“情緒勞動”這個概念的人。社會學家當初創造這個詞匯,是為了描述空乘人員、女傭和其他服務人員必須在工作上展現出快樂的模樣,以及愉悅地應對陌生人的樣子。這種“情緒勞動”的定義在霍克希爾德1983年的著作《心靈的整飾》中受到矚目,其他的社會學家在學術期刊上進一步闡述“情緒工作”這個主題。2015年,杰絲·齊默爾曼(Jess Zimmerman)聚焦女性在個人社交圈里(其實是隨時隨地)從事情緒工作的方式,再次開啟了大眾對情緒勞動的討論。
齊默爾曼的文章引發熱烈討論,數千位女性到網站上留言,并分享自身的情緒勞動經歷。所有讀者似乎都把情緒勞動視為一種需要特別投注的心力,其中包括對需求的預期、對各種優先要務的權衡和平衡、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的同理心,等等。羅絲·哈克曼(Rose Hackman)在《衛報》上發表的熱門文章,又進一步擴展了情緒勞動的定義外延。她主張情緒勞動可能是女權主義的下一個戰線。其后兩三年間,“情緒勞動”這個議題持續獲得愈來愈多的關注,有無數文章探討情緒勞動及這種勞動的無處不在。
坦白說,我覺得那是因為女性已經受夠了,忍無可忍。情緒勞動不僅僅是令人沮喪的關于家事抱怨的來源,更是系統性問題的主要根源,那些問題涉及生活的各個領域,并以破壞性的方式將我們文化中普遍存在的性別歧視凸現出來。社會深深地寄希望于女性擔負起家中一切累人的精神勞動和情緒勞動,而那些受惠最多的人大多沒有意識到這類勞動,導致那些隱約的預期在我們小心翼翼穿越一個幾乎別無選擇的文化時,輕易地跟隨著我們42570c72f483324ffbd860d630d97803進入家庭之外的世界。我們只好改變自己的語言、外表、言談舉止、內心的預期,以維持和睦。我們已經感受到這些勞動所付出的代價,而且這些代價往往不被看見。
在許多看似無關緊要的小事中,這種加乘式的情緒勞動會變成常態。日積月累下來,你的生活變成一張錯綜復雜的網,只有你自己知道怎么駕馭它。你必須引導其他人在這套精心打造的系統中穿梭,以免他們卡住或陷落。為了管理他人的情緒和預期,你需要越過重重障礙才能讓人聽到你的心聲,耗盡你本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起來的寶貴時間。但當我們的言行不符合既定的權力動態時,就必須付出高昂的代價。身為女性,我們必須在生活的各個領域營造出同樣的溫馨感。我們不僅在工作中這么做,回到家里或在外面,也必須對親友、同仁、陌生人這么做。女性之所以覺得受夠了,是因為我們意識到這種情緒勞動無法打卡下班。
每個人都必須改變對情緒勞動的看法,這樣一來,我們才有可能重新獲得情緒勞動這項技能背后的真正價值。沒錯,情緒勞動可能是我們的克星,但也可能成為我們的超能力。我們需要了解這種勞動有其價值,并把它公之于眾,讓大家可以清楚看到。這種關懷和管理情緒的智慧是一種寶貴的技能,是一種密集的解題訓練,還可以獲得同理心的額外效益。我們應該把情緒勞動變成一種人人都該擁有、人人都應理解的寶貴技能,因為它能使我們更充分地體驗生活。這樣一來,我們不僅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也可以改善伴侶和后代的生活。當我們一起消除情緒勞動的不平等時,孩子的未來就被改變了,我們的兒子可以學會恪盡本分,我們的女兒可以學會不必承擔別人的分內工作。(本文摘自《她們不是嘮叨,只是受夠了:不被看見的情緒勞動》)
(摘自3月6日《中華讀書報》)
■ 本欄編輯 朱湘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