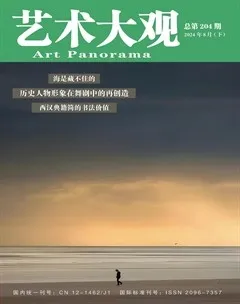西方運動題材油畫作品中的構圖的動感表達


摘 要:在悠久的西方藝術長廊中,運動題材以其獨特的動態美,受到油畫家的青睞。這些極具動態表現力和強烈的視覺沖擊力的作品,通過構圖性處理,打破畫面的穩定性,傳達出張揚的運動精神以及對運動中的人的贊美。為解決構圖在畫面中呈現效果的問題,本文將著力對西方運動題材油畫進行研究,提出構圖營造的形式美感可以實現增強畫面運動感效果的想法,以期為創作運動題材油畫作品的藝術家和將運動題材繪畫作品作為研究課題的學者提供更多參考。
關鍵詞:運動感;構圖;視覺張力;斜線;輻射線
中圖分類號:J2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7357(2024)24-000-03
古往今來,運動題材的藝術作品數不勝數,從原始時期的洞窟壁畫,原始先民狩獵追逐野獸的場景;到文藝復興時期尼德蘭畫家老彼得·勃魯蓋爾的《雪中獵人》,呈現16世紀普通民眾捕獵及滑冰的生活狀態;到19世紀荷蘭畫家梵高的《圣瑪麗的海景》,表現澎湃海浪中的漁船;再是20世紀意大利畫家波丘尼的《足球運動員的活力》,通過抽象解構具體形象,描繪運動員的力量感與活力……不勝枚舉的作品向觀者呈現了藝術家在贊揚人性、生命活力方面的不遺余力,而這一視覺效果的實現,也證明藝術家在構圖方面下了更多功夫。關于繪畫構圖在國內有很多成熟的研究,比如下文將會引用的文獻《繪畫形式語言與創作研究》,對于構圖的具體表現、效果及相關因素都有非常系統的論述。關于繪畫作品中運動感的研究,隨著對體育運動及身體健康的關注,這方面的成果也不知凡幾,可以說這兩個都非冷門領域。但是將單獨的構圖形式與運動題材油畫的運動感放在一起,研究資料卻不多,這也是筆者將此作為研究重點的原因。
構圖是什么?馬蒂斯在日記中這樣ieapPis8Miy/Cm9RjqOiuA==說:“構圖,就是畫家為了表現自己的感覺,使所配置的一切因素形成裝飾和秩序。[1]”在構圖中,包含了藝術家對外界的體驗及對內心的自我關照,甚至表達出比自身更為強烈的情感。運動題材繪畫作品的構圖非常富有運動性質和特點,體現畫家更為主觀和強烈的藝術表現。不同的構圖給人以不同的視覺感受,作品若想實現動感,大多不會采用平靜、安寧、穩定的純水平線的構圖方式,而會進行精心設計,以斜線、輻射線(或稱“V”字形)、對角線等為主,力求調動觀者的視覺興奮,與畫家產生共鳴。
一、斜線構圖
畫面整體構圖形式與畫布邊框不平行時被稱為斜線構圖,這種構圖方式可以表現畫面的動感和運動的狀態,從某種程度上而言,斜線坡度越陡,動感愈強烈。阿恩海姆曾以轉動中的風車為例來說明這個原理:“我們畫轉動中的風車,就不能畫成正十字形,這樣會顯得十分穩定;但把它稍加偏離,畫成對角線形狀,就能感覺到微小的動感;再次加大它的傾斜度,就會產生明顯的轉動效果。[2]”
(一)斜線構圖增強畫面動蕩感
荷蘭畫家文森特·梵高(Vincent Van Gogh,1853—1890)在創作油畫作品《圣瑪麗的海景》(The Sea at Les Saintes-Maries-de-la-Mer)(見圖1)時,便對海浪進行較多的構圖性處理。中景與遠景處的帆船在澎湃激蕩的海浪沖擊下起伏、傾斜出各種角度,似乎在下一刻便會傾覆,船帆也鼓出最大弧度以增強畫面真實性。為使觀者能更身臨其境地感受到海浪的洶涌,畫家又將近前的海浪從左側向右上角斜去,形成三條明確的延伸線,造成畫面的不穩定性,在視覺上產生強烈的動蕩感。梵高通過這種動蕩的充滿張力的構圖方式,捕捉到大自然的無限生機和活力,這是梵高對自己內心世界的審視和內心情感的投射,波濤中勇敢前行的帆船,彰顯梵高自身面對困境進行抗爭的真實狀態,他對生活永遠保持著滿腔熱忱。運動感構圖的成功實現,不僅得益于畫家的巧妙構思,動感極強的筆觸與視覺沖擊力極強的色彩也為構圖效果的實現起到了重要的輔助作用。
(二)夸張畫面形象增強運動感
在輔助增強斜線構圖運動感的過程中,除了筆觸與色彩的運用,形象的夸張同樣可以達到這種效果。以法國畫家泰奧多爾·席里柯(Théodore Géricault,1792-1824)的《艾普松賽馬》(derby at epsom)為例,畫面呈現出四位青年策馬狂奔的場景。斜線構圖繪制出賽馬奔跑的軌跡,運動的趨勢非常明顯,更像是在某個視覺圖像中截取的瞬間,使觀者輕易地聯想到運動的過程。為增強畫面構圖的視覺張力,馬匹四蹄騰空,營造出一種下一刻即將起飛的狀態,賽馬的激烈感呼之欲出。一生摯愛賽馬,最終還因賽馬導致墜馬而亡的席里柯能沒有觀察過馬的真實奔跑狀態?這只是藝術家在著力夸張人與馬的動勢,應和主題的巧妙設計而已。阿恩海姆在評價席里柯這件作品時也曾說:“好像在繪畫中將馬腿分離到最大限度,才能將激烈的物理運動轉換為繪畫的運動力。[3]”賽馬的運動帶動整個畫面的運動,這一過程不僅使比賽的競速感增強,同樣彰顯浪漫主義的張力,體現畫家對生命的熱愛和對馬的深刻理解,對生命活力和不屈不撓精神的贊揚。
二、輻射線構圖
輻射線(或稱“V”字形)構圖對于眾多觀者來說似乎并不陌生:“指繪畫構圖的所有形式線從一處向某一處集中或放射。輻射線在形式感上至少起到以下作用:在強烈的動勢中,使中心非常明確;宏大場面構圖中,簡單概括、易于統一;潛在力量凝聚在畫面中心,具有特殊活躍的動感、愉快感。[4]”這種向特定方向集聚或傾斜所形成的具有傾向性張力的構圖方式,可以使觀者輕易就能產生一種千軍萬馬、氣勢如虹的感覺,在大場景塑造中尤為常見。
法國印象主義畫家愛德華·馬奈(édouard Manet,1832—1883)在他的油畫作品《隆桑的賽馬》(Races at Longchamp)中著重渲染這種輻射線構圖方式,畫面中疾馳運動的馬匹朝我們沖來,兩側的觀眾正在為賽馬選手們搖旗吶喊,場面熱鬧、奔放,共同組成輻射線的構圖方式。藝術家獨辟蹊徑,選擇一個大膽的視角,讓賽道正對觀眾,以第一視角直面賽馬,多余的細節被刪減,每匹馬只在畫面中展現兩條腿,以凸顯瞬間的速度感,強烈的視覺沖擊力造成畫中馬匹在下一刻就要邁蹄沖出畫布的錯覺,緊張感與運動感油然而生。這件作品最初的設計比我們今天看到的油畫大三倍還多,兩側的觀眾占據畫面大部分,著重突出當時人們時尚流行的生活方式,但在最終定稿時卻裁去大部分,原先悠閑浪漫的氛圍在透視緊縮法(此處也指輻射線構圖)的加持下蕩然無存,六位騎手,好像是迎面而來,形成一種很強的沖擊力。作品立意與主題瞬間改變,這才有了我們今天看到的緊張激烈的賽馬場。
三、對角線構圖
(一)對角線構圖打破穩定性
對角線的構圖方式與輻射線的構圖方式在實際操作中,其實并沒有根本性差異,只是在實現效果與畫面結構上會稍有區別。對角線構圖在背景設置中會更為豐富一些,動態的人物活動更多置于前景部分。所謂的對角線構圖是作為一種強烈的視覺引導線出現的,引導觀者視線從畫面一角到另一角,這種視線移動過程本身就是一種動態的體驗,加之,對角線所具有的傾斜特性,打破畫面的對稱感與穩定性,創造出一種動態張力。法國畫家亨利·朱利安·費利克斯·盧梭(Henri Julien Félix Rousseau,1844—1910)創作的油畫作品《足球運動員》(The Football Players)(見圖2)便是采用了這種構圖方式。畫面中展現了幾個被畫成囚犯的運動員,在兩旁排列緊密的樹木中間玩橄欖球,后方是球場的欄桿。通過四人伸展的肢體邊緣組成一個不規則的四邊形,讓觀者感受到運動過程中強烈的起伏與不穩定感。
(二)視線引導突出主體狀態
畫面中的樹木沿著運動員的移動方向排列,兩排樹木樹冠的延伸方向,共同構成一個“X”形,也就是我們所強調的對角線構圖,不僅展現出一種動態的引導視線的效果,也增加了畫面的深度感。對角線具有一定的指向作用,視線向主體物集中,突出藝術家著重刻畫的主角,即畫中的運動員,這也是視點跟蹤后的結果,此刻交叉點的圖像也在視覺上得到加強。焦點處運動員的各種動作被畫家捕捉,通過夸張和簡化的手法,展現運動員的力量和在比賽中的運動狀態。另一個設計比較精巧的是,畫家對畫中人物進行的差異化區分,藍色衣服、黑色頭發與黃色衣服、棕色頭發,形成對峙的兩方。同一隊隊友形成虛擬的斜向形式線,結合不同隊伍的色彩的區別使畫面節奏感非常強。與此同時,藝術家通過運動員的動作傳達了一種積極向上的情感,視覺上的動態與情感上的動態相結合,使畫面更加生動和真實。
四、反思
以上我們通過分析畫面構圖方式,得到它在對畫面運動感的呈現上起到舉足輕重作用的結論,眾多藝術家和理論家都將此作為自己終身研究的重心。如印象主義畫家埃德加·德加一直強調的:“最使我感到高興,甚至可以從中得到慰藉的,莫過于事物和人的運動了。一棵樹,要是它的葉子連風也吹不動,那它將是多么可悲,人們也將為此而悲哀。[5]”鑒于此,再次強調運動感的實現在作品活力上的重要性,但筆者也并非認為,這種動感是畫面物體本身的特性或者以往視覺經驗在畫面中的反映,而應該是為整體構圖效果所服務的色彩、筆觸、形狀等,在相互配合和作用的情況下,于觀者所造成的一種運動的視錯覺。正如漢斯·霍夫曼所說的:“畫面制造不出真正的運動而只是運動的感覺。[6]”這種運動的感覺在詮釋作品內在生命力,激發觀者的審美情感。
對于繪畫構圖和畫面內的具體形象而言,運動感與穩定感是相互對立和排斥的兩個方面,但西方的二元論又告訴我們,對立與統一是物體存在的兩個方面。整體畫面的和諧,不僅需要運動感極強的視覺沖擊,也需要穩定性的調節。這種穩定性在畫面中是如何實現的呢?一方面是構圖上體現的穩定性,另一方面是與主題相協調的統一性。我們還以《艾普松賽馬》為例,奔馳的賽馬作為畫面主體而言,無非是吸引眼球的,通過奔跑的動作能感受到馬群呼嘯而過帶來的震撼力以及整體賽事的緊張。但除此之外的近景部分,卻給我們不同的感受,浩瀚的草原以整片黃綠色呈現,給我們寧靜統一穩定的感覺,與賽馬的動形成鮮明對比。動靜相襯,人動景靜,動靜結合,在這種變化中增強動感,畫面活了起來。
五、結束語
本文將研究重點放在畫面的形式特征之一——構圖上,但并非將構圖與畫面內容分割開,在秉承形式與內容相結合共同服務于畫面主題的基礎上,找到構圖形式存在的自主性與合理性,在這個過程中構圖本身成為一個獨立的、有意義的系統,通過塑造斜線、對角線、放射性的視覺形式,成就畫面運動感。這也是我們從構圖角度分析油畫作品中動感性的實踐意義所在,以此為正在創作此類型作品的畫家提供一些構圖上的思考方向。由于篇幅有限,只能在僅限的文字內闡述筆者觀點,不盡詳細,但也為筆者未來研究方向做初探,可以在中西方運動題材繪畫作品相比較的基礎上進行分析,或許可以得到更具有信服力的結論,以彌補本文在僅側重西方油畫研究上的局限性。
參考文獻:
[1]金冶.色彩的理論和實踐[J].新美術,1981(01):91-101.
[2]喬國鋒.論西方繪畫構圖中的運動感[J].藝術百家,2015(06):248-249.
[3]魯道夫·阿恩海姆,著.藝術與視知覺[M].滕守堯,朱疆源,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4]蔣躍.繪畫形式語言與創作研究[M].合肥:安徽美術出版社,2020.
[5]楊身源.西方畫論輯要[M].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2010.
[6][美]Herschel Chipp,著.歐美現代藝術理論[M].余珊珊,譯.長春:吉林美術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