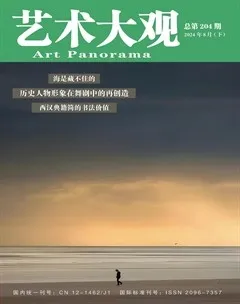蒙古族英雄史詩(shī)的傳唱者:江格爾齊的技藝要素
摘 要:《江格爾》是蒙古族英雄史詩(shī)的代表,也是蒙古族文化寶庫(kù)的一顆璀璨明珠。它以口頭傳唱的形式流傳于蒙古族民間,具有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蘊(yùn)。本文從《江格爾》史詩(shī)的傳唱者江格爾齊入手,通過(guò)文獻(xiàn)分析和田野調(diào)查總結(jié)了江格爾齊所具備的三個(gè)代表性的技藝能力要素,并討論了在《江格爾》史詩(shī)藝術(shù)發(fā)展中江格爾齊的重要作用。
關(guān)鍵詞:江格爾齊;《江格爾》;技藝要素
中圖分類號(hào):J607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2096-7357(2024)24-00-03
《江格爾》是蒙古族英雄史詩(shī)的杰出代表,這部史詩(shī)講述了英雄江格爾及其勇士們?cè)趯毮景偷胤脚c邪惡勢(shì)力斗爭(zhēng)的故事。史詩(shī)中不僅展現(xiàn)了蒙古族的英雄主義精神,還融入了蒙古族的宗教信仰、風(fēng)俗習(xí)慣和自然環(huán)境等元素,具有很高的文學(xué)價(jià)值和歷史研究?jī)r(jià)值。它以口頭傳唱的形式流傳于蒙古族民間,具有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蘊(yùn)。這部史詩(shī)不僅反映了蒙古族人民的生活習(xí)俗和信仰,還體現(xiàn)了蒙古族的歷史觀和價(jià)值觀。
能夠流利演唱并傳承蒙古族史詩(shī)《江格爾》的藝人也被稱為江格爾齊。作為史詩(shī)的傳承者,江格爾齊肩負(fù)著將這部古老史詩(shī)代代相傳的使命,是蒙古族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江格爾齊的分類與內(nèi)部辨析
(一)江格爾齊的分類
常見(jiàn)的《江格爾》說(shuō)唱表演分為兩種形式:一種是無(wú)曲調(diào),以敘述表演為主的表演形式,另一種是有固定曲調(diào),以說(shuō)唱表演為主并常伴有樂(lè)器伴奏的表演形式。因此,按照江格爾齊的演唱形式作為區(qū)別,一般將江格爾齊分為吟誦類和曲調(diào)說(shuō)唱類兩大類。目前常見(jiàn)的江格爾齊都為后者,本文主要討論的對(duì)象也為曲調(diào)說(shuō)唱類的江格爾齊。
(二)江格爾齊的內(nèi)部辨析
江格爾齊作為《江格爾》的傳播主體兼具人與傳播媒介雙重屬性,“齊”也是對(duì)說(shuō)唱《江格爾》的民間藝人的尊重[1],因此并非所有能夠演唱《江格爾》的人都能被稱為江格爾齊。
加·巴圖那生在調(diào)查報(bào)告中表示,只能講五個(gè)章回以下《〈江格爾〉傳》的人不被人們認(rèn)為是“江格爾齊”[2],同樣的,仁欽道爾吉在其專著《〈江格爾〉論》中也有相同的觀點(diǎn):“由于過(guò)去新疆的江格爾齊很多,因而僅會(huì)演唱三五部的人就不被當(dāng)作江格爾齊;只有懂得許多部,而且演唱技巧高超的人才會(huì)被人們稱為‘江格爾齊’”[3]。例如,和豐的朱乃能講26部《江格爾》,同為和豐的冉皮勒會(huì)唱21部,烏蘇縣的洪古爾能演唱10部,這些都是新疆著名的江格爾齊。
但由于老的江格爾齊相繼去世,加之《江格爾》表演活動(dòng)減少,江格爾齊在20世紀(jì)末數(shù)量驟減,于是仁欽道爾吉在研究中將能演唱完整的一到兩部《江格爾》的藝人稱作江格爾齊[3]。
筆者通過(guò)對(duì)當(dāng)今江格爾齊的訪談?wù){(diào)查發(fā)現(xiàn),以演唱篇章數(shù)量來(lái)判定藝人是否為江格爾齊的標(biāo)準(zhǔn),在江格爾齊的內(nèi)部認(rèn)同中得到的結(jié)論是不盡相同的。被訪談江格爾齊有的認(rèn)為一名合格的江格爾齊需能完整表演三四部《江格爾》,也有的認(rèn)為《江格爾》的學(xué)習(xí)難度較大,至少需要能夠完整表演一部《江格爾》的章節(jié)。如和靜縣的滿都來(lái)能夠演唱20部《江格爾》,焉耆縣的巴音孟克可演唱4章,博湖縣的岱日曼能夠演唱3章。
由此看來(lái),對(duì)江格爾齊的界定,在江格爾齊的內(nèi)部認(rèn)同中,演唱的篇章數(shù)量尚未得到一致判斷,尤其是在當(dāng)今《江格爾》說(shuō)唱藝術(shù)受到空前重視,學(xué)習(xí)《江格爾》說(shuō)唱的人數(shù)逐漸龐大,對(duì)于江格爾齊的內(nèi)部認(rèn)同卻變得清晰,并不是所有能表演《江格爾》的藝人都能被稱為江格爾齊,筆者結(jié)合對(duì)多名江格爾齊的訪談總結(jié)為:一名江格爾齊除能完整演唱《江格爾》章節(jié)外,還需具備多樣的表演能力,換句話來(lái)講,除了系統(tǒng)地學(xué)習(xí)完整的《江格爾》篇章,還需要具備技藝要素。
二、江格爾齊技藝要素
(一)記憶能力
史詩(shī)藝術(shù)作為口頭文學(xué)藝術(shù),口傳心授是其最主要的學(xué)習(xí)模式,被采訪過(guò)的幾位藝人均有青少年時(shí)就學(xué)習(xí)過(guò)《江格爾》的經(jīng)歷,并且在當(dāng)時(shí)就發(fā)現(xiàn)了自身遠(yuǎn)超常人的記憶力。
仁欽道爾吉通過(guò)句法結(jié)構(gòu)分析模型得出《江格爾》史詩(shī)具有并列復(fù)合型結(jié)構(gòu)特征,即《江格爾》各篇章節(jié)之間沒(méi)有故事情節(jié)上的連貫性,各個(gè)篇章在結(jié)構(gòu)上具有完整獨(dú)立的特征[4]。因此由許多獨(dú)立的章節(jié)組成,每個(gè)章節(jié)都可以獨(dú)立成篇,但它們共同構(gòu)成了一個(gè)宏偉的史詩(shī)體系。《江格爾》的演唱就是以篇章為單位進(jìn)行表演的,一個(gè)獨(dú)立完整的章節(jié)包含了該章節(jié)的《〈江格爾〉贊》和隨之其后的《講〈江格爾〉》正文,一場(chǎng)完整表演少則一兩個(gè)小時(shí),多則四個(gè)小時(shí)以上,如此大篇幅唱詞文本,需要江格爾齊強(qiáng)大的記憶能力。
那么,《江格爾》的文本內(nèi)容有無(wú)記憶技巧呢?研究《江格爾》史詩(shī)文本可以發(fā)現(xiàn),《江格爾》的文本具有固定的程式化詞匯和語(yǔ)句。例如,“英明蓋世的諾言江格爾”“殘暴的希拉·莽古斯可汗”“鐵臂的薩布爾”等[5]。這些固定短語(yǔ)或語(yǔ)句不僅點(diǎn)出了被修飾者(名詞,人或物)的某些特點(diǎn)、屬性和品類,還渲染和修飾了史詩(shī)凝重、宏偉和肅穆的詩(shī)品特征,使得表演者可通過(guò)程式化的語(yǔ)匯來(lái)輔助記憶。
可見(jiàn),江格爾齊能夠記憶長(zhǎng)篇史詩(shī)內(nèi)容,這種記憶力不僅涵蓋了史詩(shī)的情節(jié)、人物、事件,同時(shí)他們能夠長(zhǎng)期保持這些記憶,即使經(jīng)過(guò)多年,也能準(zhǔn)確無(wú)誤地復(fù)述史詩(shī)的內(nèi)容。這種強(qiáng)大的記憶力還兼具了長(zhǎng)久的穩(wěn)定性,這是江格爾齊最為顯著的能力特點(diǎn)之一。
(二)唱奏能力
除了少部分吟誦類江格爾齊外,大部分江格爾齊都是以說(shuō)唱形式表演《江格爾》,可見(jiàn)《江格爾》的音樂(lè)表達(dá)也是江格爾齊在學(xué)習(xí)過(guò)程中的重要環(huán)節(jié)。在同焉耆縣江格爾齊巴音孟克的訪談中,他給出了一個(gè)很經(jīng)典的學(xué)習(xí)范本:第一個(gè)階段是先學(xué)唱《〈江格爾〉贊》,第二個(gè)階段為故事情節(jié)的背誦,以《洪古爾迎戰(zhàn)莽古斯》這一章節(jié)為例,故事情節(jié)大致分為人物介紹環(huán)節(jié)、展開(kāi)戰(zhàn)斗環(huán)節(jié)和勝利歸來(lái)環(huán)節(jié)三個(gè)部分,能夠?qū)⒐适虑楣?jié)記牢后,第三個(gè)階段就是將故事用說(shuō)唱的形式演唱出來(lái)。用他的原話說(shuō)是:“故事背下來(lái)后要‘變’,這個(gè)和說(shuō)的話不一樣,這個(gè)是藝術(shù),得配著音樂(lè)講述出來(lái)。”可見(jiàn),除了記憶史詩(shī)文本,史詩(shī)唱詞轉(zhuǎn)化同樣需要江格爾齊高超的演唱能力和依據(jù)行文韻律改編唱詞的編創(chuàng)能力。在這個(gè)模式中,學(xué)習(xí)《江格爾》是由文本過(guò)渡到說(shuō)唱的轉(zhuǎn)化,音樂(lè)的關(guān)照同史詩(shī)文本的韻律和程式是相輔相成的。
另外,具有說(shuō)唱表演能力的江格爾齊通常都配有樂(lè)器伴奏,樂(lè)器多為新疆蒙古族傳統(tǒng)樂(lè)器托布秀爾。托布秀爾為主要流傳在新疆蒙古族的彈撥類樂(lè)器,音色清脆、悠揚(yáng),兩根弦,常由一個(gè)扁平的共鳴音箱和一根較長(zhǎng)的琴頸組成,共鳴箱有個(gè)小孔,方便聲音的傳播,同時(shí)扁箱長(zhǎng)柄的設(shè)計(jì)便于演奏者進(jìn)行各種演奏技巧的展示,同時(shí)也便于攜帶。
過(guò)去,許多著名的江格爾齊都能彈奏托布秀爾演唱《江格爾》,如博爾塔拉的賓拜、道爾巴,和布克賽爾的阿乃·尼開(kāi)、額爾赫太、加甫,尼勒克縣的達(dá)瓦等。但隨著《江格爾》說(shuō)唱的落寞,加之諸多江格爾齊相繼去世,在賈木扎20世紀(jì)80年代的調(diào)查報(bào)告中記錄了現(xiàn)在除了朱乃、巴桑—哈爾、普爾布加甫等江格爾齊外很少有人會(huì)彈著樂(lè)器演唱《江格爾》[6]。觀之當(dāng)今的《江格爾》學(xué)習(xí)者多數(shù)都延續(xù)了表演《江格爾》時(shí)演奏托布秀爾伴唱的特征。巴音孟克的原話為:“江格爾說(shuō)也可以呢,厲害的就能唱,再勞道①的就可以彈著托布秀爾唱了。”同時(shí)在訪談中他還為我們介紹了一個(gè)有趣的現(xiàn)象:“以前的國(guó)家級(jí)傳承人滿都拉老師,托布秀爾彈一個(gè)地方,唱一個(gè)地方,不配合,(托布秀爾和《江格爾》演唱)合不到一塊去,后面好不容易才學(xué)會(huì)了,能在一起了。”綜上可見(jiàn),托布秀爾和《江格爾》的演唱是高度綁定的,并在表演環(huán)境中不斷去熟練和打磨技藝。
(三)綜合表演能力
《江格爾》史詩(shī)說(shuō)唱因其史詩(shī)文本的龐大,演唱一部完整的章節(jié)時(shí)間較長(zhǎng),因此在《江格爾》的演唱中有很多需遵守的傳統(tǒng),如表演時(shí)必須在夜晚,以表示對(duì)英雄的贊頌和尊重,還有《江格爾》的表演不能隨意終止,表演者要完整地唱完一部方可結(jié)束。仁欽道爾吉對(duì)此解釋:“演唱一部長(zhǎng)詩(shī),就得完整地演唱,不能隨意終止,聽(tīng)眾要堅(jiān)持聽(tīng)到演唱結(jié)束,不能隨意離開(kāi)等。違反了這些規(guī)則,會(huì)被認(rèn)為是罪過(guò),會(huì)遭受災(zāi)難。[4]”但現(xiàn)如今,聽(tīng)眾快節(jié)奏的審美已不再適應(yīng)《江格爾》長(zhǎng)篇的表演節(jié)奏,再加之現(xiàn)如今的表演場(chǎng)域已經(jīng)從廟會(huì)和祭祀場(chǎng)所變更到了諸如藝術(shù)節(jié)、文化展和比賽的舞臺(tái)場(chǎng)域,對(duì)《江格爾》的表演時(shí)間和空間進(jìn)行了進(jìn)一步的壓縮。這樣的表演環(huán)境,江格爾齊的表演能力也有了相同的適應(yīng)性。
從表演內(nèi)容選擇上,表演者在有時(shí)間限制的表演中通常會(huì)選擇《〈江格爾〉贊》,問(wèn)及什么是“江格爾贊”,巴音孟克回答:“‘江格爾贊’是一個(gè)段落,少得很,‘江格爾贊’緊接著江格爾的故事篇章,已經(jīng)是縮減完了的了,把簡(jiǎn)單的部分都拿到前面來(lái)了。”我們把《江格爾贊》通常理解為相對(duì)應(yīng)《江格爾》篇章故事情節(jié)中人物、景物和情節(jié)的贊頌,是《江格爾》篇章中的高度概括,也是學(xué)習(xí)《江格爾》的基礎(chǔ)。接著巴音孟克又說(shuō):“《江格爾》可以縮短,如說(shuō)馬怎么樣跑的這一段,這個(gè)樣子跑,那個(gè)樣子跑的就不說(shuō)了,直接說(shuō)騎馬跑過(guò)去就行了。”這是對(duì)史詩(shī)文本情節(jié)中對(duì)人物形象、事物特征的具體描述的縮減,相反,史詩(shī)的內(nèi)容文本也可以增加上述的描述來(lái)擴(kuò)充表演的內(nèi)容。在江格爾齊岱日曼的訪談中也有此類表演技巧的表述:“《江格爾》唱駱駝的時(shí)候,毛、腿、鼻子、嘴巴、眼睛、耳朵、尾巴都是可以描述的。”由此可見(jiàn),能力強(qiáng)的江格爾齊可以通過(guò)增加或刪減史詩(shī)人物或事物的具體描述內(nèi)容來(lái)達(dá)到控制表演時(shí)間。
此外,在表演過(guò)程中,因表演環(huán)境和高壓以及長(zhǎng)時(shí)間的演唱難免有唱錯(cuò)情節(jié)或忘詞的情況,據(jù)巴音孟克回憶:“以前在蒙古包里,江格爾齊很放松,中間斷了喝杯茶就想起來(lái)了。”可見(jiàn)表演環(huán)境對(duì)《江格爾》的表演也至為重要。筆者觀看《江格爾》的比賽時(shí)發(fā)現(xiàn),舞臺(tái)上的表演者因忘詞被迫停止表演的現(xiàn)象也屢見(jiàn)不鮮。面對(duì)這樣的情況,藝人也有應(yīng)對(duì)的策略:“有一次我在和豐比賽,要唱20分鐘的江格爾,中間我忘掉了,我會(huì)用托布秀爾代替旋律,在這個(gè)空當(dāng)回憶,如果想不起來(lái),就把這一段節(jié)再唱一遍,將其順下來(lái),只要我保持連貫,對(duì)江格爾不熟悉的人是聽(tīng)不出來(lái)的。”可見(jiàn),成熟的江格爾齊擁有較強(qiáng)的抗壓能力,以及在表演中能夠運(yùn)用同觀眾的互動(dòng)因素或自身對(duì)表演內(nèi)容的重復(fù)運(yùn)用來(lái)巧妙化解演出的失誤,當(dāng)然這也離不開(kāi)此部分江格爾齊熟練的技巧和豐富的表演經(jīng)驗(yàn)。
以上是筆者在田野調(diào)查的過(guò)程中,對(duì)江格爾齊藝術(shù)能力的總結(jié),這些記憶要素共同構(gòu)成了江格爾齊的藝術(shù)特質(zhì),使他們能夠在蒙古族史詩(shī)文化中扮演重要的傳播角色,并確保《江格爾》史詩(shī)得以世代相傳。
三、江格爾齊之于《江格爾》藝術(shù)的重要意義
(一)文化傳承與創(chuàng)新
《江格爾》藝術(shù)雖經(jīng)低迷,但從未斷絕,蒙古族的英雄史詩(shī)也在一代又一代江格爾齊的傳唱中得以延續(xù)。《江格爾》說(shuō)唱藝術(shù)不僅是藝術(shù)表現(xiàn),更是文化記憶的傳遞,對(duì)于保持蒙古族的文化特色和民族認(rèn)同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傳承的基礎(chǔ)上,江格爾齊不斷進(jìn)行藝術(shù)創(chuàng)新,使得《江格爾》史詩(shī)的內(nèi)容和形式得以豐富和發(fā)展。《江格爾》因其口頭史詩(shī)的文本特點(diǎn),江格爾齊在說(shuō)唱表演中也不拘泥于固化的唱詞和旋律,并在表演中持續(xù)再度創(chuàng)作,使《江格爾》說(shuō)唱藝術(shù)呈現(xiàn)了江格爾齊的個(gè)人創(chuàng)作風(fēng)格和特點(diǎn)[7],這也是《江格爾》說(shuō)唱藝術(shù)獨(dú)具魅力且經(jīng)久不衰的重要原因。
如果說(shuō)《江格爾》的表演實(shí)踐過(guò)程是在吸收、學(xué)習(xí)并創(chuàng)新,實(shí)質(zhì)上屬同步發(fā)生、同步實(shí)踐和同步運(yùn)行的過(guò)程。那么在這個(gè)過(guò)程中,英雄史詩(shī)包含的豐富道德觀念、歷史知識(shí)和社會(huì)經(jīng)驗(yàn),在江格爾齊的演唱過(guò)程中被民眾所接納,并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的教育意義,傳遞了正義、勇敢、忠誠(chéng)等價(jià)值觀。而《江格爾》史詩(shī)中的人物和故事往往成為蒙古族人民共同的精神象征,在江格爾齊的演唱中增強(qiáng)民族凝聚力和共同體意識(shí)。
(二)學(xué)術(shù)價(jià)值與意義
《江格爾》作為蒙古族歷史悠久的口頭文學(xué),包含了歷史、文化、語(yǔ)言、民俗等領(lǐng)域的寶貴資料,對(duì)于學(xué)術(shù)研究具有重要意義,《江格爾》史詩(shī)是蒙古族早期文學(xué)的最高成就,具有很高的文學(xué)價(jià)值和珍貴的史學(xué)價(jià)值,對(duì)于研究蒙古族遠(yuǎn)古時(shí)期的哲學(xué)思想、宗教信仰、風(fēng)俗習(xí)慣等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若是將《江格爾》比作蒙古族歷史文化的寶庫(kù),那么江格爾齊就是手握寶庫(kù)鑰匙的守護(hù)者。豐富的文化歷史在江格爾齊的口口相傳中得以延續(xù),江格爾齊在《江格爾》的學(xué)術(shù)研究中也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在受到國(guó)內(nèi)外學(xué)者的廣泛關(guān)注下,從20世紀(jì)50—60年代開(kāi)始,《江格爾》的研究已發(fā)展成專門學(xué)科,逐漸形成了國(guó)際性的“江格爾學(xué)”[8]。
四、結(jié)束語(yǔ)
在現(xiàn)代社會(huì),江格爾齊已成為蒙古族文化交流的使者,他們不僅在國(guó)內(nèi)各地展示蒙古族的傳統(tǒng)文化,強(qiáng)化了各地域各民族之間的交流,同時(shí)《江格爾》也逐漸走出國(guó)門,通過(guò)江格爾齊的傳唱向世界介紹這一獨(dú)特的史詩(shī)藝術(shù),增進(jìn)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對(duì)蒙古族文化的了解,展現(xiàn)著我們的藝術(shù)精神和文化自信,《江格爾》的史詩(shī)故事跨越了語(yǔ)言和文化的界限,成為全人類共同的文化財(cái)富。
參考文獻(xiàn):
[1]道·道圖那.《江格爾》在新疆的傳播與傳承研究[D].西北大學(xué),2022.
[2]加·巴圖那生,王清.《江格爾傳》在和布克賽爾流傳情況調(diào)查[J].民族文學(xué)研究,1984(01):42-54.
[3]仁欽道爾吉.江格爾論[M].呼和浩特:內(nèi)蒙古大學(xué)出版社,1994.
[4]仁欽道爾吉.蒙古族英雄史詩(shī)《江格爾》[N].中國(guó)民族報(bào),2004-03-05(010).
[5]朝金戈.口傳史詩(shī)詩(shī)學(xué):冉皮勒《江格爾》程式句法研究[M].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0.
[6]特·賈木查.王清,喬倫夫,譯.蒙古族英雄史詩(shī)《江格爾傳》調(diào)查報(bào)告[R].新疆民族文學(xué),1982.
[7]哈斯巴特爾.英雄史詩(shī)音樂(lè)的風(fēng)格構(gòu)成與結(jié)構(gòu)程式——以史詩(shī)《江格爾》五首曲調(diào)為例[J].中國(guó)音樂(lè),2022(03):118-124+185.
[8]郝蘇民.中國(guó)江格爾學(xué)的建立:認(rèn)識(shí)與實(shí)踐[J].西域研究,1992(03):1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