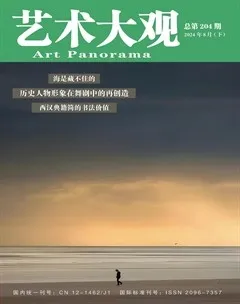《我的阿勒泰》:藝術(shù)化的影像民族志
摘 要:電視劇《我的阿勒泰》在2024年夏季爆火,這部電視劇重新梳理了散文原著的脈絡(luò),用高品質(zhì)、高標(biāo)準(zhǔn)地制作水準(zhǔn),風(fēng)格化的表達方式成功將民族風(fēng)情帶入大眾視野,是文化、地域、藝術(shù)的完美結(jié)合。這部電視劇不論是影片拍攝,還是劇情設(shè)計,都很好地運用了影視人類學(xué)的理論與技巧,具有深厚的人類學(xué)研究色彩。《我的阿勒泰》大獲成功,不僅見證了我國新西部片的發(fā)展,更是影視人類學(xué)現(xiàn)代化的重要嘗試。
關(guān)鍵詞:《我的阿勒泰》;影像民族志;散文改編
中圖分類號:J905 文獻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2096-7357(2024)24-00-03
電視劇《我的阿勒泰》改編自新疆作家李娟的同名散文集。該劇于2024年4月7日在法國戛納舉行全球首映,并入圍最佳長劇集競賽單元,成為首部入圍戛納電視劇節(jié)主競賽的長篇華語劇集。4月25日,《我的阿勒泰》在北京國際電影節(jié)舉行亞洲首映并獲得廣泛好評,各大電影節(jié)的成功讓這部劇還未上映就攢足了流量和熱度。5月7日,央視一套黃金檔和愛奇藝微劇場同步播出8集短劇《我的阿勒泰》,該劇一經(jīng)上映火遍了各大互聯(lián)網(wǎng)平臺,27萬人在豆瓣打出了8.9分的高分,觀眾稱其為一部華語電視劇中難得的“細(xì)糠”。《我的阿勒泰》將民族風(fēng)情帶入大眾視野,深入客觀地將民族風(fēng)俗習(xí)慣融入電視劇中的每一個細(xì)節(jié),真實又美好的風(fēng)格打動著每一位銀幕前的觀眾,是一部藝術(shù)化了的影像民族志。
一、影視劇的創(chuàng)作風(fēng)格
不同的創(chuàng)作者有著不同的風(fēng)格,《我的阿勒泰》帶給觀眾的是輕松、幽默的敘事和油畫般質(zhì)感的畫面,給人治愈、曠野、美和自由的享受。美輪美奐的背后是畫面構(gòu)圖、燈光氛圍、后期調(diào)色缺一不可的默契配合。《我的阿勒泰》前期拍攝采用4K分辨率,原生HDR高動態(tài)范圍,杜比全景聲等先進技術(shù),將阿勒泰的美景最大可能地展現(xiàn)在觀眾面前。電視劇在構(gòu)圖中也別出心裁,2.35:1的畫幅讓這部劇“電影感”十足。構(gòu)圖常用的三分法構(gòu)圖、對角線構(gòu)圖、對稱構(gòu)圖等手法配合著恰到好處的畫面,讓觀眾切身感受到帶有不同情緒的鏡頭語言。劇中有諸多細(xì)致入微的細(xì)節(jié)可以看出劇組的別出心裁,例如,文秀與托肯和庫蘭一同走路參加舞會這一劇情中,有一段三人相互做伴走路嬉戲的鏡頭配色十分考究:三人的著裝是紅、白、藍這一經(jīng)典又具視覺沖擊力和藝術(shù)美感的色彩組合,給人一種靈動之美。再如電視劇大量運用散文原著的文化符號,如對日常生活中器物的形象命名,絲布棉布料被稱為“塑料的”、相思鳥香煙是“小鳥牌香煙”、木耳被喚作“喀啦(黑色)蘑菇”、瓶子為手雷形狀的白酒被叫作“砰砰”、孔雀被稱為“大尾巴漂亮鳥”[1]。電視劇在拍攝過程中采用跟焦員手動對焦,讓觀眾似乎進行了一次與導(dǎo)演的面對面對話。這種電影級別的高標(biāo)準(zhǔn)制作和豐富的細(xì)節(jié)設(shè)計為這部劇的風(fēng)格化夯實了基礎(chǔ)。
“自由”是這部劇給人的第一印象,不論是畫面還是劇情抑或者是角色的臺詞都充滿了舒緩和松弛。可事實上《我的阿勒泰》并不是第一部營造遠離城市田園牧歌的作品,市場上追尋“詩和遠方”的詩歌、小說、民謠數(shù)不勝數(shù)。《我的阿勒泰》中漢族同哈薩克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題材才是吸引眼球的內(nèi)核所在,劇中以張鳳俠一家移民到新疆阿勒泰彩虹布拉克開小賣部為背景,有很多對民族飲食文化(干奶酪、包爾沙克、葡萄干兒、杏干兒、馓子、塔爾米、馕塊兒),豐富多彩的民間文化如阿肯彈唱會、叼羊、賽馬、馴鷹,還有哈薩克傳統(tǒng)婚禮、宰羊等儀式文化的展示[1]。目前市面上很難找出同《我的阿勒泰》影響力相當(dāng)?shù)拿褡孱}材影視作品了,民族題材的低熱度和敏感性讓很多創(chuàng)作者看不到賣點。
同時,這部劇是我國西部題材影視作品擺脫傳統(tǒng)二元對立敘事的重要嘗試。人們印象中的西部是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的無人荒漠,是脫離道德和法律約束的“法外之地”,這是因為,在電影的市場化進程中,隨著商業(yè)屬性被不斷強調(diào),西部空間形象作為一個已經(jīng)在一系列作品中大獲成功并與觀眾達成默契的影像符號被率先挪用,成為很多類型電影構(gòu)建主題的捷徑[2]。例如,《天下無賊》《無人區(qū)》《可可西里》等,這些傳統(tǒng)的西部題材作品都給西部打上了標(biāo)簽,似乎俠肝義膽才是西部本色。不僅僅是中國西部片,美國西部片的起源就更早了,美國西部片是美國電影最古老的樣式之一,從20世紀(jì)初的《火車大劫案》,到20世紀(jì)60年代的《荒野大鏢客》,再到近代的《與狼共舞》等,天才導(dǎo)演們利用無盡想象締造了無數(shù)經(jīng)典。西部牛仔的形象早已深深烙印在全世界觀眾的腦海中。筆者認(rèn)為,中美兩國西部片的興起具有深厚的時代背景,西部片歌頌的堅韌不拔與勇于探索、見義勇為的精神都與兩國對西部開發(fā)的時代背景緊密契合。作為一個特殊的電影類型,西部電影的空間意識具有深厚的闡釋向度,但在長期與社會進程同步演進的創(chuàng)作嘗試中,西部意象都或多或少被定格為一種“工具化”的表述,被動地折射著不同時期的主流社會心態(tài),或是承載著沉重的歷史反思的包袱,或是在某些時候淪為創(chuàng)作者對國際聲譽渴望的代價[2]。而近幾年來,新的西部題材的作品走出了傳統(tǒng)套路,利用西部的旖旎風(fēng)光探討新的主題逐步走進大眾視野,如2022年李睿珺導(dǎo)演的《隱入塵煙》等,《我的阿勒泰》更是新西部地區(qū)題材作品的一個里程碑,一改人們對中國西部的刻板印象,到阿勒泰旅游的游客成倍增長。
二、從散文到影視劇的重構(gòu)
有許多優(yōu)秀的影視作品都是由文本改編而來的,如四大名著均有對應(yīng)的影視作品,而且都有不同版本的翻拍。再如《活著》《河邊的錯誤》《茶館》《霸王別姬》等諸多文學(xué)作品都被翻拍成了電影,還有《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繁華》等也被翻拍成了電視劇。有些翻拍講究真實,達到最真實的還原就是翻拍得好,稍有改動即破壞了平衡;有些翻拍則需要導(dǎo)演二次創(chuàng)作,以達到符合拍攝的目的。《我的阿勒泰》顯然屬于后者,散文講究形散而神不散的氣韻很難在影視劇中展現(xiàn)出來,于是導(dǎo)演滕叢叢和編劇彭奕寧在電視劇的改編中揚長避短,既理順了故事劇情又保留了原著風(fēng)格。根據(jù)達林·哈琴、西沃恩·奧弗琳《改編理論》中的觀點,改編不僅是對原作內(nèi)容的重現(xiàn),更是對原作意義的再創(chuàng)造[3]。在電視劇中,導(dǎo)演將原著中的張鳳霞改名作張鳳俠,為李文秀的超人媽媽張鳳俠增加了幾分灑脫和豁達。再如,原著中只言片語草草帶過的圖滾在電視劇中成為為女性自由獨立不懈斗爭的托肯,導(dǎo)演為托肯“加戲”,強調(diào)了女性話語,直指當(dāng)今社會性別平等問題,幽默又獨立的托肯面對孩子和丈夫二選一的困境時頑強斗爭,不僅給全劇帶來很多笑點,也感染了現(xiàn)實中的很多女性,成為很多觀眾最喜歡的角色之一。
導(dǎo)演對影視劇的重構(gòu)為觀眾帶來了更加豐富的人物關(guān)系和更加鮮活的人物,滕叢叢說:“每一個人物都是鮮活的,這是我作為導(dǎo)演覺得最驕傲的一點。”的確,想要讓每個人物都活靈活現(xiàn)并非易事,很多鴻篇巨制恐怕都無法保證每個人物都是鮮活的。這一點讓《我的阿勒泰》這部8集迷你劇變得更加難能可貴,這也是這部電視劇可以被稱為精品的重要原因。每一個鮮活的人物給了觀眾不必喜歡主角的權(quán)力,觀眾可以喜歡劇中的任何一個有血有肉的角色,劇中的所有故事情節(jié)也不是圍繞著主角設(shè)計的。當(dāng)“主角光環(huán)”不復(fù)存在,劇情也就更加跌宕起伏,引人入勝、貼近現(xiàn)實。
鬼才導(dǎo)演昆汀·塔倫蒂諾有一個經(jīng)典的比喻,他將觀眾的注意力比作一根橡皮筋,矛盾與沖突就是扯動橡皮筋的雙手,如果將橡皮筋輕輕一拽就放手觀眾會覺得無趣,但若將橡皮筋拉太緊橡皮筋就會斷掉,期待已久的觀眾太久看不到結(jié)果會失去耐心。所以將橡皮筋拉伸得恰到好處是每個講故事的人必備的技能。正是《我的阿勒泰》拒絕“烏托邦”幻境的現(xiàn)實感,讓劇中充滿了矛盾與沖突,時時刻刻牽動著觀眾的神經(jīng),也反映導(dǎo)演對事件的觀察。劇中的主要矛盾有兩個:一個是李文秀一家的外來移民與哈薩克族原住民之間的沖突;另一個是作為古老游牧民族的哈薩克族在面臨現(xiàn)代化中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沖突。首先,哈薩克族與漢族的矛盾源于兩者之間大相徑庭的生活習(xí)俗,作為游牧民族的哈薩克族將馬匹、駱駝視為朋友,在哈薩克語中如果想要表達親密,父母常常對自己的孩子們說:“你真是我的小駱駝、小馬駒。”所以,當(dāng)哈薩克族人的馬死后,他們會將馬頭掛在每天必經(jīng)之路的樹上,以表達思念;哈薩克族在洗衣服時會將衣服、褲子分開洗,而不是跟漢族一樣將衣服、褲子一起放進洗衣機。其次,在時代潮流中任何一個都會遇到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矛盾,而較為保守的哈薩克族所面臨的問題更加尖銳,更加棘手。巴太在馬場是最優(yōu)秀的馴馬師,巴太去青島進修的路上安檢不允許攜帶刀具,巴太果斷選擇放棄乘車;巴太的父親蘇力坦是全劇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沖突的焦點,哈薩克族佩戴獵槍和養(yǎng)隼的習(xí)俗在劇中成為兩個意象。村主任阿依別克響應(yīng)號召來收繳蘇力坦的獵槍,蘇力坦自己保留了一把,那把藏起來的獵槍好似蘇力坦的寫照,雖然有攻擊力但很少能拿出來,拿獵槍救了李文秀母女后蘇力坦似乎更迷茫了,明明自己寶刀未老是放牧打獵的一把好手,可為什么兒子巴太和兒媳婦托肯都不愿繼承自己的事業(yè)。最后,蘇力坦在不解中選擇了妥協(xié),同意兒子巴太回馬場,同意托肯帶著孩子改嫁,自己賣掉一半牛羊孤獨堅持。
三、《我的阿勒泰》影像民族志價值分析
導(dǎo)演滕叢叢在采訪中談道:“從散文到影視劇改編最大的難點就在于建立人物關(guān)系。要建立人物關(guān)系就要采風(fēng),就是田野調(diào)查。”電視劇《我的阿勒泰》拍攝歷時將近6個月,整個劇組在阿勒泰地區(qū)同吃同住同勞動,受到哈薩克族歌舞的感染,劇組的每位成員都會在晚飯后到后院載歌載舞。甚至在拍攝中,有很多群演就是哈薩克族本地人:演員阿麗瑪在劇中飾演托肯,劇中托肯的媽媽就是由阿麗瑪母親飾演的,托肯爸爸由阿麗瑪舅舅飾演。《我的阿勒泰》不僅展現(xiàn)的是哈薩克族真實的生活場景,演員也有阿勒泰本地居民。劇組在拍攝期間也算是進行了一次對阿勒泰的田野調(diào)查。
在這部電視劇里,李文秀好似愛麗絲夢游仙境的主角愛麗絲,帶著觀眾們來到彩虹布拉克,轉(zhuǎn)移夏牧場,結(jié)識托肯、阿依別克、巴太、庫蘭等村民,做了一場去愛、去感受、去受傷的夢。小賣部是一個觀察哈薩克族生活的窗口,也是一個多民族交流的場域,李文秀在小賣部觀察、記錄、同哈薩克小伙相識相愛,做了一次扎扎實實的田野調(diào)查。電視劇中的每一個鏡頭、每一個特寫、每一個精心設(shè)計的細(xì)節(jié)背后都是劇組成員真實觀察,用心展現(xiàn)的成果。《我的阿勒泰》不論布光、色彩還是聲音都展現(xiàn)了業(yè)內(nèi)頂尖水準(zhǔn),給人舒緩、清新、自然之美,是一部藝術(shù)化的影像民族志。
四、結(jié)束語
我國的影視人類學(xué)是從被觀察者起步的,早在1869年,英國攝影師約翰·湯姆森來到中國,以皇家地理學(xué)會會員身份,開始了中國與東南亞攝影之旅,并在四年后出版照片集《中國與中國人影像》。日本研究者鳥居龍藏于1896年至1899年在中國臺灣高山族調(diào)查,1905年開始在中國貴州、云南、湖南、四川一帶進行少數(shù)民族調(diào)查,他在調(diào)查期間用相機進行記錄,留下了當(dāng)時中國少數(shù)民族的體貌特征[4]。隨后,國內(nèi)學(xué)者如孫明經(jīng)、莊學(xué)本等也紛紛扛起攝影機來到祖國大江南北拍攝考察。1985年,時任國際影視人類學(xué)委員會主席的加拿大蒙特利爾大學(xué)森·巴列克西教授把“影視人類學(xué)”這一學(xué)科名稱介紹到中國后,中國的影視人類學(xué)就開始進入了快速發(fā)展的時期。此后,我國一些研究機構(gòu)和高校紛紛成立影視人類學(xué)研究機構(gòu)。這些研究機構(gòu)幾十年來不斷積累經(jīng)驗,一邊收集我國少數(shù)民族影像資料,一邊為中國影視人類學(xué)尋找出路。到了現(xiàn)代,在科技飛速進步與我國經(jīng)濟飛騰的背景下,便攜、高效的數(shù)碼照相機在市場上普及開來,拍攝成為一件越來越容易的事情,我們甚至可以看到被調(diào)查對象自己拿起手機記錄自己的生活。電視劇《我的阿勒泰》的出現(xiàn),更是把影像民族志搬上了銀幕,成功將民族習(xí)俗帶入大眾視野,讓人們了解并熟悉了哈薩克族,是影視人類學(xué)現(xiàn)代化的一次重要嘗試。
參考文獻:
[1]鄒贊.跨媒介靈韻轉(zhuǎn)移、共同體微觀敘事與牧歌美升華——評電視劇《我的阿勒泰》[J].中國文藝評論,2024(07):91-103+128.
[2]徐雅寧,張馨天.中國西部電影空間塑造的轉(zhuǎn)向及文化意涵[J].電影文學(xué),2023(01):36-41.
[3]宋瑞.從文字到影像:《我的阿勒泰》敘事創(chuàng)新與藝術(shù)重構(gòu)[J].當(dāng)代電視,2024(07):59-65.
[4]熊迅.影視人類學(xué)的脈絡(luò)、路徑和前瞻[J].民族藝術(shù),2023(02):76-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