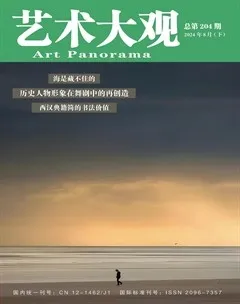單幅漫畫“電影感”的生成路徑與審美價值
摘 要:本文以凡悲魯單幅漫畫作品《戰天斗地》為例,探析媒介融合視域下單幅漫畫作品“電影感”的具體所指,即二維空間下敘事時空的生成,并在此基礎上從創作與觀看的角度出發,解析單幅漫畫“電影感”的生成路徑,即“時間空間化”與“空間時間化”的過程,進而基于視覺運動與審美范式在當代技術人文視閾下的轉變,闡述單幅漫畫在中國乃至世界文化范疇下的審美價值。
關鍵詞:單幅漫畫;視覺敘事;時間空間化;空間時間化;中國審美
中圖分類號:J9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7357(2024)24-00-03
當前對于漫畫“電影感”的探討,其聚焦的對象多為多幅或連環漫畫。區別于多幅或連環漫畫所試圖傳達的“電影感”,單幅漫畫無法借助格與格之間的畫面關系,以類似電影分鏡頭的方式直觀呈現情節的演化過程,而僅用一個繪制生成的瞬間定格,既彰顯時間序列上圍繞這一瞬間所產生的前后延宕,又描摹空間結構中物象與人像的組合中所隱含的動勢與情勢,以此來實現對特定主題、人物關系與敘事脈絡的隱喻。正如《拉奧孔》中所描述的:“繪畫在它的同時并列的構圖中,只能運用動作中的某一瞬間,所以就要選擇最富于孕育性的那一瞬間,使得前前后后都可以從這一瞬間中得到最清楚的理解。”因而論單幅漫畫的“電影感”,其核心所指或許可被理解為二維空間下敘事時空的生成。正如《漫畫原來要這樣看:藝術形式再進化》一書的作者史科特·麥克勞德所闡述的:“我們需學習從空間的角度去感知時間。”一般,在單幅漫畫中,創作者所攫取的決定性瞬間需具備某種運動之勢,在不同視覺單元間,借助視覺符號、構圖、光影、色彩等方式形成不同運動之勢間的沖突與平衡,在這里,沖突與平衡作為過程性的存在,“勢”作為銜接不同狀態間的過渡性存在,均為靜態的、造型的、空間的單幅漫畫賦予了時間的向度。這一特征與愛森斯坦對電影中單個鏡頭中蒙太奇存在的闡述有著相通之處,愛森斯坦在《蒙太奇論》中寫道:“單個鏡頭本身具有的運動性結構及要素構成,即運動的痕跡。”可見電影與漫畫盡管在表現形式上大有不同,但在視覺語言的應用規律上有著巧妙的契合,對單幅漫畫“電影感”的研究,可在直觀的視覺空間結構之外,從人物與環境的互動關系中探索動勢與情勢的發現、發生與發展,即“敘事時間空間化”的生成路徑,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思考將繪畫藝術、造型藝術、材料藝術等整合進二度空間的過程中,電影的蒙太奇創作思維何以實現“跨界”的應用,最終從時空建構的角度思考敘事與表意機制的形成過程。本文擬以在2024年意大利達·芬奇國際藝術節藝術文化類/繪畫單元獲獎的中國單幅漫畫作品《戰天斗地》為例,解析電影蒙太奇思維下時間空間化、空間時間化的生成路徑。
一、空間的時間化
“空間時間化”是將空間的靜態形式納入時間的動態過程中,體現萬事萬物的變動過程和衍變軌跡。中國樸素唯物主義思想的集大成者王夫之在《周易外傳》對于空間向時間轉化的理解為:“天地之可大,天地之可久也。久也持大,大以成久。若其讓天地之大,則終不及天地久也。”空間意義的“大”與時間意義的“久”相互關聯,“大以成久”所講的便是空間向時間的轉化,而“終不及天地久”則進一步說明在中國古典哲學的時空觀念中,時間因其自身綿延不斷的性質,相對于空間而言具備一定的超越性。而在西方哲學理論中,綿延作為柏格森哲學的核心概念,常被一些自然主義畫論用來闡釋印象主義[1]。柏格森認為,存在兩種分別對應物理時間與心理時間的綿延:“一種通過空間來表現……一種同時的、并置的、秩序的、定量區分的關于程度差異的外在多樣性,即一種數字式的、間斷的、現實的多樣性;另一種是連續的、融合的、組織的、異質的、定性區分的關于性質差異的內在多樣性,即一種虛擬的、不間斷的、不能還原為數目的多樣性。”可見,綿延雖然作為描述時間性的哲學概念,其對于程度差異外在多樣性的探討仍以空間的現實存在為基礎。
(一)符號的選取:母題的編碼和解碼
單幅漫畫中符號意義的生成既離不開創作者基于特定一個或一組母題意象的主觀創造,又需要借由觀者發揮其自身的主體性,對畫面中的圖像符號進行帶有其自身所屬歷史文化語境下集體認識痕跡的解碼。于單幅漫畫創作者而言,當不同的母題意象被創造性地按照一定的結構重組,規約性的符號意義在碰撞中往往具備衍生相應主題情節的潛能,主題情節是發展性的,靜態的符號由此獲得超越決定性瞬間的表意空間,獲得時間化的意義。以凡悲魯單幅漫畫作品《戰天斗地》為例,釘耙和耕犁、酒杯與酒壺在構圖上形成微妙的左右對稱關系,釘耙與耕犁作為勞動者勤勤懇懇、重視腳踏實地的道德品質的象征,酒壺與酒杯所象征的是享樂者渾渾噩噩、沉迷感官體驗的頹唐狀態的象征,兩組符號間形成頗具諷刺意味的對比,也正是在對比的過程中,觀者對三個角色的形象逐漸產生更為豐富的理解——臉頰的紅暈是醉酒的表征,配合對體態與身形的刻畫,得以理解對于三個角色而言,所謂“戰天斗地”的創造性勞動僅為空談,眼前唾手可得的感官之樂才是本質。
(二)視線的指引:平移與縱深的運動
從視線運動的層面剖析觀畫與觀影的區別,需要綜合考量媒介的物質形態與媒介所處的空間環境兩大因素。物質形態方面,單幅繪畫對“決定性瞬間”的刻畫是靜態的、空間的,電影則以一系列相互關聯、自成體系的瞬間牽引觀者的視線進入特定敘事時空;空間環境方面,單幅繪畫往往以平面紙媒印刷或置于公共空間展覽,其意義的讀解需要觀者主觀能動地將注意力集中,而電影在銀幕之上、“黑匣子”之中播映,空間環境與物質形態共同實現電影時空與現實時空的間離。在觀看以單幅漫畫為代表的繪畫作品時,對視線運動的考量既發生在畫面的橫縱空間內,由創作者借助構圖、量感、透視、色彩等實現對觀者視線暗示性的牽引,同時又發生在畫面之外,即在靜觀中將所視之物象與外部環境、個體經驗、主觀想象之間自發形成身心一體系統感知的過程中。以凡悲魯《戰天斗地》為例,居中構圖與大面積留白的設計營造“遠觀”的視覺效果,通過打破透視關系的介入,將被遠觀的瞬間懸置于虛無的時空中,一方面牽引觀者的視點聚焦于畫面主體之上,同時又將作者的心懷由可見導向虛無,由物象導向心象,很大程度上貼合中華民族在藝術感知上對寧靜致遠的追求與向往。從畫面上“看見某物”到將畫面上的所視“看作某物”,“凝視”讓觀者在“無”中填充自身的社會經驗與文化想象,形成對漫畫主題的主觀理解,實現視覺對嶄新之物的構造,有效調動觀看者的主體性、能動性與積極性,架構從視覺感知到觀念建構的橋梁。
(三)局部的拼貼:時間差的主觀創造
將不同時刻的景象置于對同一個決定性瞬間的刻畫中,這一瞬間作為系統,其局部之間的錯位及整體與局部的關系往往能夠呈現出類似于電影剪輯中時序拼貼、時空交錯的觀感。阿比·瓦爾堡(Aby Warburg)在其著名的《記憶女神圖集》中對跨越時空的圖像母題展開蒙太奇式的重組;中國繪畫對“重屏”的妙用更是凸顯了對時刻與時序、真實與虛幻的哲思。再如周文矩《重屏會棋圖》中“畫中見畫三重鋪”的巧思,棋局對弈、臥榻休憩、圍屏山水形成縱深的視覺層次,重屏的設計將三個各自獨立、自稱體系的時間點銜接于一處,伴隨著視點的移動,畫作所呈現的寓意也隨之發生轉變。在當代單幅漫畫創作中,將不同時間點上的情境以空間的形式進行拼貼、嵌套,一定程度上作為“時間空間化”的表現手法,使作品得以呈現突破現實時空下認知規律的觀感,賦予其多維的闡釋空間。在凡悲魯《戰天斗地》中,這一時間差體現于光影的設計。釘耙和耕犁的影子朝向右側,其所存在的時刻下,太陽的位置當位于畫面左側,也就是空間方位中的西方。但人影則位于三個角色的正下方,因而在角色所處的時刻,太陽的位置應當位于畫面的正中,也就是空間方位中的上方。角色手持釘耙和耕犁,卻又似乎與其不存在于同一時間,仿佛握在手里,與軀體高度重疊的酒壺與酒杯才是與其處于同一時空下,畫作的諷刺意味由此得以強化。
二、時間的空間化
《“時間空間化”概念溯源和美學探究》一文從東西方理論角度進行概念溯源,作者主張西方的“時間空間化”,指以現代社會技術空間、虛擬空間和權力空間為代表的人工空間對自然狀態下時間的改造和重塑,潛移默化地改變人們對待時間的態度與方法;而中國的“時間空間化”則傾向于對自然景觀與四時之序的討論,經歷“時間推演出空間”“時間演變成空間”“時間讓位于空間”三個階段而形成“時間空間化”的結果,其所指向的更多傾向于空間在時間向度,伴隨時間運行的過程與節奏所彰顯出的生命“綿延、活潑和創化之象”。[2]中國本土單幅漫畫創作“時間空間化”的路徑在很大程度上呼應了東方宇宙觀、時空觀的內核,一方面借對動勢的刻畫提取畫面主體最具生命活力的瞬間,另一方面則通過對主體與環境互動關系進行充盈詩意的描摹,融入作者在特定環境下對特定主體的具身感知與理解,凸顯單幅漫畫作品靈韻的不可復制性。
(一)動勢:對時間的提取
前文提及對于單幅漫畫“電影感”的考量需要看其是否做到“選擇最富于孕育性的那一瞬間”。在流動的時間與敘事中攫取“最具孕育性的瞬間”,并為時間意義的瞬間賦予視覺化、空間化的表現,需要創作者在這一瞬間借助特定畫面元素與表現手法完成某種生命活力的傾注,讓“前前后后都可以從這一瞬間中得到最清楚的理解”。這里的“生命活力”,在中國傳統哲學、美學觀念中多寓于畫面的“勢”中。物理學意義的“勢”,或稱“勢能”指“儲存于一個系統內的,渴望釋放或者轉化為其他形式的能量”。繪畫中的“勢”則更傾向于指畫面給觀者在直覺上留下的印象,是物象在空間所呈現的一種大的輪廓和大輪廓所呈現的某種活動的態43c2d2b9637f54bbe11029e1b5b29c9a勢或某種情緒的傾向。六朝時期繪畫理論家謝赫則在繪畫“六法”中明確提出“經營位置”的理念,宋代畫家郭熙在《林泉高致》中主張“真山水之巖石,遠望之以取其勢,近看之取其質”,進一步通過“質”與“勢”的辯證關系探討中國畫審美的構成。清代學者王船山在《姜齋詩話》中則主張畫者應做到“咫尺有萬里之勢”,即借助“勢”的傾注,在畫的過程中完成對現實時空參照的重塑,融入創作者對主體與環境的主觀感知。在現當代單幅漫畫創作中,對于“勢”的塑造則已然超越了遠觀之下構圖方法的范疇,而進一步深入畫面的局部,從物與物、物與景的互動關系中定格形變、傾斜、墜落等動勢發生的瞬間,并通過視線傳遞、手勢指引、色彩選擇、材料應用等方法將動勢在觀感上加以強化,為“最具孕育性的瞬間”賦予層次更為豐富的戲劇性。以凡悲魯《戰天斗地》為例,創作者在表現三個醉酒大漢的狀態時,通過“勢”的巧妙運用為畫面注入動感——在構圖上,創作者通過左右兩側的釘耙和耕犁在縱向上圈定了畫面主體的所在范圍,而橫向上卻僅以虛白之中的“影”暗示地面的位置,使畫面主體在橫向上沒有實體的面作為重力的承接,營造一種片刻的懸停,暗示這一秒的穩態或許在下一刻便將垂直墜落、分崩離析,在形式上巧妙呼應著敘事的諷刺意味;在繪制上,畫面左右兩側的角色均在體態上有朝向中間傾倒的動勢,握住生產工具的手位于中段偏下方的位置,營造一種岌岌可危的脫力感,中間角色體型略大,繪制用色較實、較深,形成一種承力之勢。因而觀者既可以感受到醉酒大漢“幾欲傾倒”的動勢,同時還能對動勢之間的作用力獲得較為直觀的感知。
(二)靈韻:對時間的詩化
在中國古代詩學中,“時間空間化”往往意味著“自然空間對于時間流逝的物象性呈現,它有典型的藝術性傾向,表達了‘剎那即永恒’的理解”。[2]借由自然空間的萬物生長的節律性、規律性與生命活力,審美主體的頓悟既關乎物理空間內朝向縱深、高遠天地之際的追尋,又關乎心理空間內對于自我的回歸,即《文心雕龍·物色》中所講的“目既往還,心亦吐納,情往似贈,興來如答”。這一創作傳統延續至今,在當代單幅漫畫創作中,通過創造性地呈現某一時刻環境與主體的狀態,創作者多傾向于以隱晦的、詩意的方式傳達這一時刻所處的時間流內畫面主體的客觀感受與情緒體驗。以凡悲魯《戰天斗地》為例,這一距離體現在對“田野勞作”概念化的理解,一面將田野勞作將人與自然串聯于一處,把人的行為置于萬物生長的自然節律下進行觀照,同時通過將自然環境以留白的方式進行處理,通過在直感上模糊環境以突出主體,實現心理層面對自我的回歸并試圖與觀者產生心理上的共鳴,以追求時間維度與空間維度、視覺向度與心理向度的辯證統一。
三、結束語
單幅漫畫“電影感”生成于二維空間中對時間向度的表現,在蒙太奇思維的跨界應用中轉化為時間空間化、空間時間化的創作路徑,最終的落點既關乎對數字影像時代大眾視覺運動慣性與審美范式變化的回應,呈現傳統平面藝術創作在當代技術與人文視閾下的“破局”之勢,又關乎在快餐文化盛行的讀圖時代,藝術創作相對于社會現實的距離與回應,“電影感”最終強調的并非僅限于審美維度與觀看體驗的豐富度,而更在于視覺敘事與觀念表意潛能的延展性。以《戰天斗地》為代表的強調電影感創作思維的中國單幅漫畫在國際視野備受關注,一定程度上可作為中國傳統文化在當代影像創作思維影響下的轉型嘗試,對于當代漫畫創作而言具備較強的參考價值。
參考文獻:
[1][美]邁耶·夏皮羅.繪畫中的世界觀:藝術與社會[M].高薪,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20.
[2]田宏宇,孫宏新.“時間空間化”概念溯源和美學探究[J].淮南師范學院學報,2022(06):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