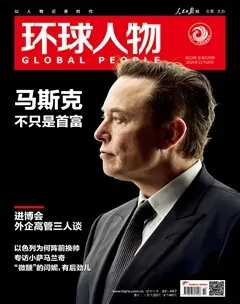三年磨一“箭”

11月12日,第十五屆中國航展在廣東珠海拉開帷幕。47個國家和地區的1000多家企業齊聚于此,中國航天領域的“大國重器”扎堆亮相,包括首次展出的嫦娥六號探測器、長征八號甲運載火箭、長征十二號系列運載火箭等重磅模型展品。
對布向偉來說,看到長征系列運載火箭無比親切,因為他曾擔任長征十一號火箭(以下簡稱“長十一”)的結構總體設計師。在此之后,他與人聯合創立了民營火箭公司東方空間,開始用市場化的方式書寫另一種航天故事。
“我們公司的‘引力一號’火箭在今年初首飛成功后,我還是第一次參加航展。”布向偉對《環球人物》記者說。
這次,布向偉是帶著火箭、發動機、空天信息裝備等眾多產品前來參會的,不僅為了展示實力,更是為了合作交流。“我希望中國航天事業進一步擴大社會影響力,中國商業航天產業能健康、有序、快速地發展。”
有驚無險的海上發射
布向偉提到的“引力一號”是東方空間自主研制的火箭。今年1月11日,“引力一號”在山東海陽附近海域發射升空,將3顆衛星送入預定軌道,創下全球最大固體運載火箭發射等多項紀錄。
這次發射可謂有驚無險。發射當天,原本預報的好天氣沒有如期而至,前一晚開始刮風,當天一早下起了雨夾雪。負責值夜班的技術人員不放心,隔一會就出去看一下現場情況,幾乎整晚沒睡覺,好在火箭防護罩經受住了天氣考驗。

因為是在海上發射,風浪問題變得十分重要。與天氣相似,發射當日的風浪比預報大得多,海面下也暗流涌動,發射船顛簸比較劇烈,給工作人員的撤離帶來了一定麻煩。
“當時在發射船上有十幾個人,發射前半小時之內,所有人都要跳到撤離船上。因為風浪大,撤離船上下晃動,人在跳的時候一不小心就會掉下去。我在大屏幕上看著他們一個一個跳過去,特別揪心,尤其是最后一名同事,做了幾次準備都沒成,他怕耽誤發射,最終找到機會勇敢地一躍,終于跳上了撤離船。”布向偉回憶道。
“3、2、1,點火!”隨著指揮員的口令,4臺發動機噴射出巨大的火焰,大團的煙霧翻卷上涌,遠遠望去,在空中形成了一個心形。
“說實話,我們之前沒想到會出來那么多煙霧。我和眾多嘉賓坐在指揮中心觀看發射,一開始只能看到煙霧、聽到聲音,卻看不到火箭升空。”布向偉說,那一刻全場鴉雀無聲。
“我真是出了一身的冷汗,旁邊一位領導跟我說,不會出問題了吧?但我覺得不是,因為火箭爆炸的聲音是完全不一樣的。又過了四五秒鐘,我們看到火箭從煙霧里沖出來了。原來什么故障也沒有發生,只是煙霧太大,把火箭擋住了。”指揮中心瞬間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
當指揮員宣布發射成功后,現場所有人都激動不已,不少研發人員熱淚盈眶,副總設計師黃帥更是抱住布向偉流下了淚水。
“我們在戶外還設立了一個觀看現場,很多航天迷購票前來,還有不少媒體也在那邊。當我們過去跟他們會合時,聯合創始人魏凱接受了媒體采訪,一邊說一邊哭,差點成了網紅。”布向偉笑道。
商業火箭的邏輯
大家之所以這樣激動,是因為整個過程太不容易了,用布向偉的話說,“真是一把辛酸淚”。
2020年6月,布向偉與合伙人一起注冊成立了東方空間(山東)科技有限公司,8月正式開張運營。當時,他面臨兩個問題:一是業內同行已經有發射成功的案例了,技術人員更愿意去一家有成功經驗的民營火箭公司,而不愿意來初創公司;二是疫情對大家的工作生活沖擊較大,大部分人更愿意待在一個相對穩定的環境中,所以招聘員工就變得很難。布向偉想方設法招來的30個人,幾乎沒有研究火箭出身的,都是來自一些相關領域。但他覺得問題不大,“我們可以自己培養專業人才”。
2021年3月,“引力一號”正式立項研制,同年12月轉入初樣階段,2023年10月轉入試樣階段。在這個過程中,不斷有新人加入,隊伍逐漸擴大到200人。
“每當我們做出一些成績,比如助推器分離實驗做成了、發動機試車完成了,同行們看到你確實有實力,就愿意來了。”
布向偉說,公司成立以來,聚焦的就是兩大核心問題:運載火箭的能力與發射場的能力。
“引力一號”總高度30米,相比于外觀修長的“長十一”,它的外觀像個“胖墩兒”——起飛重量405噸,是“長十一”的7倍左右;4臺發動機提供了600噸的起飛推力,是“長十一”的5倍左右。
“為了適應海上發射,讓重心更穩定,我們在設計之初考慮用捆綁方式,降低火箭高度、增加外擴,用小型火箭的‘身高’實現中型火箭的運載能力。”布向偉說。
整個2023年,團隊成員的平均出差時間在半年以上。從大年初三開始,有人去零部件加工廠驗收,有人去發射場做試驗,元宵節、端午節、中秋節都是在出差中度過的。布向偉則從2023年9月就到了發射點——東方航天港,這是中國首個海上發射母港,位于山東煙臺市下轄的海陽市。
商業火箭發射要在可控范圍內降低成本,換句話說,既要安全可靠,又要性價比高。比如在發射地點的選擇上,沿海地區要比內陸地區有更大的優勢。
“如果在內陸地區修建發射場,周邊起碼幾公里之內都得是無人區,但在海上發射就不存在這個問題,建設成本更低。”布向偉說。


在垂直狀態使用階段,為了使火箭不受風霜雨雪的侵蝕,必須有配套的保護設施,通常需要花費數千萬元建設勤務設施。布向偉團隊另辟蹊徑,決定用充氣防護罩把火箭包起來。
這種防護罩類似兒童游樂場的充氣城堡,分成左右兩半,合到一起就像給火箭穿了一件衣服。起飛前解鎖,兩邊各自倒下去,放掉氣可以卷起來收走,成本只要幾十萬元。
“刻在航天人骨子里的精神”
今年40歲的布向偉,是航天領域的一名“老兵”。他出生于河南洛陽,2003年考入哈爾濱工業大學航天學院,“當時覺得這個專業比較好,懵懵懂懂就來了”。
入學沒幾天,學校便組織集體觀看神舟五號飛船發射。看到楊利偉完成中國首次載人航天飛行任務時,布向偉很受觸動,“這是我的入門第一課”。
本科4年,布向偉除了上課就是泡在圖書館里學習,成績十分優秀。畢業時,他被保送到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攻讀碩士研究生,2010年畢業后就留在研究院工作,接到的第一個任務是研發“長十一”的火工品系統。
火工品通俗地說就是爆炸物,在航天領域的應用廣泛。但布向偉是學飛行器設計出身,之前沒有接觸過火工品。
“那段時間壓力很大,只能從頭開始,找各種書籍研究。我自學了半年左右,就開始負責項目論證,又過了半年,開始做具體的設計工作。”布向偉回憶道,“在這個過程中,負責‘傳、幫、帶’的呂鋼老師對我影響很大。他不僅技術厲害,也特別勤奮,每天加班到最晚的經常是我們兩個人。”
當時,布向偉在單位對面租了房子,每天早上7點多到辦公室,晚上10點、11點下班,周六日也基本上泡在單位。這種狀態持續了兩三年。

“咱們國家之所以在航天領域不怵別的國家,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有大量工程師是這種狀態。其實單位沒有強制要求,但大家都有一種使命感。中國載人航天精神是4個特別: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斗、特別能攻關、特別能奉獻。這不僅是口號,更是從無數人的工作實踐中提煉出來的,是刻在航天人骨子里的精神。”
2015年,“長十一”發射成功后,布向偉的工作重心由總體設計轉向市場化工作。到2019年,他幾乎把市場上的商業衛星公司跑遍了,主要是幫對方做衛星發射方案。
“我感覺市場需求非常大,但國內的火箭運力無法滿足,于是有了創業的想法。”布向偉說,“當時東方航天港剛剛成立,正在尋找投資對象,就給了我們5000萬元的天使投資。”
近年來,在國家政策的支持下,民營航天公司大量涌現。從2020年開始,中國商業航天投資進入了高峰期。布向偉認為,目前國內市場的競爭已經提前進入白熱化。
“外國同行一般要經營很多年,才能給出一個相對較低的發射價格,比如2萬元人民幣/公斤,但中國公司太拼了,剛創業就必須給出較低報價,哪怕前兩年都是虧錢在干,也要爭得一席之地。”布向偉說,“中國人才多,又勤勞,很快就能把市場價格打下去。但因為美國對我們搞航天封鎖,中國的商業火箭公司現在走不出去,如果能到國際上競爭,我相信所有的中國企業都能迅速成長起來。”
布向偉坦言,商業航天的整體回報是比較可觀的。一方面,行業的發展帶來了公司估值的提升;另一方面,發射活動的輻射帶動效應也非常大,比如各類制造業、服務業、科普教育、旅游等相關產業和地方經濟的發展。
目前,東方空間正在研發可重復使用的“引力二號”火箭,其運載能力將比“引力一號”提升3倍多。布向偉的理想是實現“航班化”發射,讓火箭能重復使用10次、20次,后續成本就很低了。“現在我們國內商業發射的成本還相對較高,隨著發射次數的增加以及技術的不斷迭代進步,未來盈利預期很強。‘引力一號’的首飛成功只是第一步,我們計劃用8至10年時間,把公司建成世界一流的民營航天企業。”
編輯陳佳莉/美編 苑立榮/編審 張建魁
布向偉
1984出生于河南洛陽,獲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士、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碩士學位,曾任長征十一號火箭結構總體設計師。現任東方空間聯合創始人、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