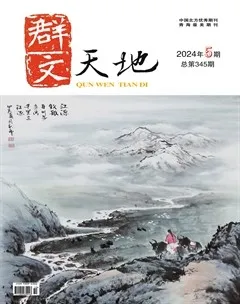藏漢翻譯規范化勢在必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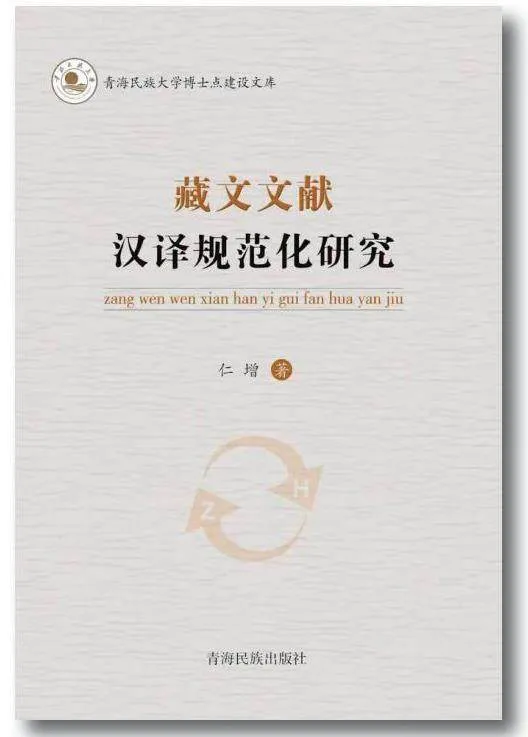

青海民族大學教授仁增先生的專著《藏文文獻漢譯規范化研究》一書,于2021年由青海民族出版社出版。該書出版之后,引起了許多學者及翻譯專業人士的高度關注,受到省內外相關藏學家、翻譯家、中青年翻譯骨干和部分在讀研究生的廣泛稱贊。
著名藏學家、翻譯家祁順來先生為本書作序,對該書給予了高度評價。青海省政協原副主席、著名藏學家和翻譯家蒲文成先生(已故)曾多次在自己的文章和專著中對仁增教授的翻譯研究水準和孜孜不倦的教學態度不惜美譽贊賞。
眾所周知,翻譯是一種實現不同語言文字之間相互溝通交流的方式,能讓使用不同語言的民族通過翻譯來實現溝通交流。翻譯的具體形式有很多,如口譯、筆譯、機器翻譯等,但目前,翻譯仍然以口譯和文字翻譯兩種形式為主。
對于一個國家而言,翻譯應該是實現政治、經濟的發展目標,促進各民族文化傳播,搭建和諧友誼的金橋,也是人們在不斷交往交流交融中必不可少的一門技術。因此,如何研究分析與提高翻譯水準也成了擺在翻譯家、各民族學者面前的重要問題。
祁順來先生在本書序言中寫道:“這部學術專著是作者長期博覽眾采,深入思考,多方探究的產物,是作者學術認知的積淀,多年心血的結晶。體現出一個有抱負、有志向學者的學術自覺、學術責任和學術擔當。”雖然語言不多,卻全面而又深刻地詮釋了本書作者的學術境界、學術造詣和學術責任。
該書的出版發行,無疑將會對藏漢翻譯規范化理論的提升與完善,推動藏漢翻譯的全面發展,提高藏漢翻譯水準等方面產生巨大推動作用。
此書總共有10章,277頁,27萬字。主要學術內容包括:第一章重點闡述了本選題的社會背景、研究目的、學術意義、研究現狀,以及相關理論基礎等基本內涵。與此同時,研究分析了本書的現實意義,作者認為專門研究藏文文獻漢譯規范化,進而推動藏漢翻譯事業,對促進漢藏文化交流,加強民族團結,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和親和力,增進文化認同,增強我國公共文化服務能力等方面,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該書解決的問題,主要是將專有名詞、格助虛詞、非格助虛詞、常位句、殊位句及藻飾詞等這些藏文文獻漢譯難點問題作為重點研究對象,借鑒國內外的翻譯規范理論,構建藏漢翻譯基本理論體系。從研究方法而言,主要采用多學科結合研究法、語法比較研究法、文化比較研究法、實地調查研究法等。本書的創新之處,在于通過全面回顧藏漢翻譯歷史,廣泛閱讀各種譯本,從構成語言的主要成分入手,首次對藏文文獻漢譯中出現的主要問題進行較全面且系統的梳理和歸納,從而較為清晰地闡述了藏漢翻譯的基本情況。另外,明確規定了藏漢翻譯的基本概念界定與研究思路等。第二章解析了藏文文獻漢譯現狀,回顧了藏漢翻譯經歷的崎嶇坎坷歷程,全面細致地闡釋了翻譯中存在的問題,對存在的突出問題解析得透徹到位,對錯譯、一名多譯和各地方言為主的譯文等舉例說明與解析,同時提出了譯文要規范統一、獨特明確的觀點。作者認為,雖然目前有不少藏漢翻譯研究文章,但大多數形似我國傳統文論,是對某一個翻譯問題、翻譯事件、翻譯活動或譯作譯品就事論事的思考和感慨,常以感悟、評點、隨感等形式出現,不追求定義的準確、邏輯的嚴密、方法的合理、論證的清晰和實證的支撐,因而缺乏科學性,更沒有從翻譯的學科特征出發, 運用語言學、語法學、修辭學、文藝學、文化學及美學等多學科知識建構一種既切合藏漢翻譯實際,又行之有效的具有普遍性和規律性的基本理論體系,以指導藏漢翻譯實踐,致使藏漢翻譯事業一直處于無理論指導、無規則可循、無方法可依的局面。第三章研究了藏語人名漢譯規范化的問題,提出了藏語人名漢譯的原則和方法,要求以音譯為準,且譯音要力求準確,避免使用方言詞與多音詞;翻譯用字要選常用字,忌用生僻字、貶義詞和生義詞等的具體觀點。另外,作者認為人名的譯寫是否正確統一,不僅會影響人們正常的交往交流和有效溝通,在具體的文獻翻譯中,更會關系到譯文的整體質量和文化價值。“人名翻譯,至關重要,一字之差,就會面目全非,因此理應受到譯界的重視”。第四章重點探討了藏語地名漢譯規范化問題,要求堅持藏語地名漢譯的原則和方法,不斷規范和統一地名漢語音譯及一名多譯中存在的亂象,尤其是提出了藏語地名語音統一與三大藏語方言區譯名的規范化問題,具有現實指導意義。同時認真闡釋了藏語地名與藏語人名一樣,除了經常出現在日常交流中,在藏文文獻中也被廣泛運用,起著重要作用。因此,可以說地名的譯寫是否準確統一,不但影響人們的相互交流,在具體的文獻翻譯中,更會關系到整個譯文的翻譯質量,甚至關系到史料的真實性與參考價值的問題。第五章解析了藏文書名漢譯規范化問題,重點闡明了藏文書名的取法、藏文書名的構成特征、藏文書名的翻譯方法等問題,提出了翻譯要精準、精確、精煉的要求,書名的翻譯方法主要采用直譯、略譯、改譯觀點。第六章解釋了藏語藻飾詞的含義及類型、藏語事物藻飾詞的特點、藻飾詞的翻譯方法等。重點提出了藏文藻飾詞的翻譯采取直譯、意譯及直譯與意譯結合并行的具體方法。作者認為藏語藻飾詞是一種特殊詞語, 它是在引進并借鑒梵文辭藻學的基礎上形成的。一般分事物藻飾詞和數字藻飾詞,前者數量多、范圍廣,主要有七種取名方式,在印藏文化中常被用于文學作品中,起修飾作用;后者數量較少,但有自己獨特的構成方式,在印度文化中它只被用于時輪歷和度量學中,但傳入中國涉藏地區后,逐漸納入辭藻學中,在各種體裁的文學作品中加以廣泛運用。第七章探討了藏文特殊文化詞漢譯規范化問題,分析了生態類特殊文化詞、物質類特殊文化詞、社會類特殊文化詞、宗教類特殊文化詞等的構成與翻譯技巧,提出了以音譯為主,適當加注的翻譯方法。作者的最終結論是:翻譯不僅是兩種語言之間的轉換,更是兩種文化之間的轉換。對一個譯者而言,熟悉兩種文化甚至比掌握兩種語言更重要,一個優秀的翻譯家尤其要熟悉其他民族的文化,準確理解所譯文獻的原意,根據需要靈活掌握翻譯方法。漢藏文化之間既有共性,又有差異。藏語文化中的生態類、物質類、社會類、宗教類、語言類的詞匯千差萬別,數量頗多,它們都是藏文化的特殊產物。翻譯這些富有文化內涵與藏民族特色的詞時,一定要深刻領會原義,謹慎處理。與此同時,作者談到,絕不能濫用譯法,更不能胡譯、亂譯,還要講究翻譯用字的規范和統一,使譯文準確傳遞信息,在保證譯文可讀性的基礎上,將原文的文化內涵和民族特色進行最大限度地體現,從而使翻譯真正成為漢藏文化交流的橋梁。第八章闡釋了藏文格助詞的漢譯規范化的重要性,分析了許多翻譯人員常常遇到的棘手問題。此章中重點研究和分析了藏文格助詞的分類和特征、藏文格助詞的翻譯方法等,提出了對譯和略譯的方法、要求。作者認為格助詞也叫格,是一種特殊的虛詞。藏文格助詞常用于核心句中,是核心句的重要語法標志,使用極為廣泛。因此,藏文各文法的書中,將其列為重要內容單獨講授和研究,藏文格助詞的用法成為藏文文法之一。第九章闡述了藏文格助詞與藏文非格助詞漢譯規范化與藏語語法之間的相互聯系與作用。作者著重解析了藏文非格助詞的分類和特征、藏文格助詞的漢譯方法,解釋了主要的非格助詞是針對格助詞而言的。包括飾集詞、待述詞、離合詞、終結詞、連詞、語氣詞、否定詞等詞的內涵。第十章重點研究與分析了藏文主語和賓語的譯法、藏文謂語的譯法、藏文定語的譯法、藏文狀語和補語的譯法等。作者的結論是,主謂賓、定狀補是構成藏漢句子的主要成分, 也是藏漢語言的共性所在,并且大部分能對譯,只有賓語、狀語、補語因受語境及譯者所選句式等影響,偶爾會出現不對譯的情況。不過藏漢句子各成分在排列次序、所處位置以及表現形式上卻有差異,對此譯者要予以重視并求同存異,不能為求新異而使譯文語言生硬晦澀,影響了原義的準確表達或造成理解上的障礙。同時還要注意語境與翻譯的對應關系,即因語境不同而出現的譯法變異性的觀點。此章提出了翻譯基礎理論研究與現實社會使用詞句翻譯相結合的要點,研究成果顯著、觀點明確,具有很強的理論指導和實踐意義。
縱覽全書,該書的學術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較以往的翻譯研究成果而言,藏譯漢的研究專著和論文較多,但是藏文文獻漢譯規范化研究成果卻寥寥無幾,且藏譯漢規范是多數藏族翻譯人員面臨的棘手問題和難以突破的瓶頸。本書的出版發行,可謂是填補了沒有藏譯漢規范研究專著的空白。該書重點探討和分析了藏文文獻漢譯中存在的疑惑與難點問題,提出了解決問題的新方法與新觀點,同時分析了藏族著名作品的漢譯成果讀者少、未能廣泛流傳的原因。作者認為主要原因還是翻譯不規范和名詞術語不統一造成的。因此,作者的觀點是譯文的規范與統一是重中之重,勢在必行。只要在藏譯漢的規范和完善上下功夫,就能夠翻譯出走向全國乃至世界的好作品。
第二,日常翻譯中,因涉藏地區的人名、地名、書名等翻譯較混亂,導致出現了許多不應該出現的問題,尤其是在牧區常常發生的草山糾紛,集中體現了藏譯漢的地名、人名混亂等問題。存在這些問題的主要原因有:一是地方方言與普通話之間存在差別;二是三大藏語方言區與漢語發音不統一;三是漢藏翻譯人員的能力水平存在差別,以及對原文的理解、表達水平不一致且翻譯方式不一致,這三種問題產生的根源無疑是因為翻譯不規范。作者還提出了以往一些不規范的翻譯,影響了藏族文化的有效傳播和漢藏文化的深度交流,以及公共文化事業的健康發展,也提出了解決的具體要點。另外,書中充分論證或闡釋了翻譯中“信、達、雅”的內涵及理論指導意義,通過理論結合實際提出了人名、地名、書名要以音譯為主,同時使用意譯和合譯的觀點。此外,書中還列舉并提出了其他語法詞、文學作品等以意譯為主的要求。這些翻譯方法的提出,對今后翻譯工作的規范與名詞術語的統一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第三,在探討原來漢譯中存在的問題及原因時,作者結合了大量的名詞術語錯譯和多譯的亂象,以漢藏對照表格的形式進行說明,這些說明很有啟發和借鑒作用。比如,用漢藏對照表對贊普及王子的名稱、王妃的名稱、吐蕃臣相的名稱,還有歷代學者、喇嘛、官員等的名稱,進行比較研究,指出了一名多譯或錯譯的實際問題,提出必須規范統一的意見。其中一名多譯的現象十分嚴重,盡管人名是音譯的,可是應用了大量的不一致的同音字,造成一名多譯的后果。作者提出結論性的觀點:藏語地名反映藏民族某一個地區及某一個歷史階段的地貌特征、物產、經濟、歷史、生活范圍、歷史變遷以及宗教信仰等文化內涵。它在藏漢翻譯時最常見,數量僅次于人名。因此,其翻譯的準確統一與否,不僅影響人們的相互交流,在文獻翻譯中,更會影響到譯文的整體質量,甚至還會影響到漢語的規范問題。翻譯多地一名時,要注意用字的規范,不能隨意翻譯而造成同名多譯,更要考察地名淵源,不能割斷其歷史文化關系。所依原文語音應以藏語書面讀音為準,不能以三大藏語方言區各方言為主,只有這樣才能使大部分譯名得以統一。這段解讀非常重要,分析了人名、地名翻譯中存在的突出矛盾或問題,同時提出了解決問題的方法。另外,為了更好地掌握翻譯的重要內涵,作者應用了大量的案例,使用標準規范的句詞說明問題,很有說服力和現實指導意義。
第四,該書中的藏文藻飾詞漢譯難度較大,而且詞匯量大,在翻譯中存在較多的分歧。本書作者對藏文藻飾詞漢譯提出了直譯、意譯、直譯與意譯結合并行,以及改譯或略譯等四種方法。藻飾詞多數用于文學作品的修辭方面,若要掌握藏文藻飾詞很不容易,一種事物有多種名稱,譬如太陽、月亮、星星、大地、雪山、蓮花、獅子、老虎等的藻飾詞多者可達二十余種,少則六七種,何況翻譯的難度非同一般。對這些疑難問題,作者采取理論結合實際的方式進行了探討與分析,提出了對這些翻譯方法要根據具體內容和語境來恰當、靈活地使用,各有側重,不能固定化和絕對化的具體要求,這也可謂是在藏漢翻譯研究方面取得的新突破。
第五,該書應用的資料翔實可靠,多數資料是從歷代藏文文獻和實際調查研究中得到的。參考文獻中既有1300多年的翻譯文獻資料,又有藏傳佛教后弘期以后的經文、格言、道歌、故事的翻譯資料,還有歷代著名學者的翻譯作品和當代作家的翻譯作品。縱觀文獻資料,可謂搜集齊全、資料珍貴,很有參考價值。加之作者長期處在翻譯研究和教學工作的第一線,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因此,該書成為廣大翻譯工作者和研究人員,以及廣大學生不可多得的翻譯教科書。
第六,該書運用翻譯學等多學科知識和理論,對其進行研究,建立了基本的指導性理論體系。該書框架結構合理,研究方法新穎、學術規范、內容豐富、論據充分、論點突出有力、語言流暢到位,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和使用價值。從中不難看出,作者雖然是從小學習本民族語言成長起來的一位藏族學者,但他始終堅持學習鉆研漢語及普通話,進步很快,如今,他已經具備應用漢語書寫專著的水平。此翻譯研究專著的出版,足以證明了他的漢語書寫能力,同時也向社會和翻譯工作者奉獻了一部專業知識較強的書籍,確實難能可貴。
上述評介僅僅是總結與提煉書中的主要學術價值或基本特色,涉獵還不夠全面深入、廣泛涵延,有許多方面還未嗅探通達,因此,我呼吁相關同仁們不妨通讀原著,潛心思悟,一定會從中汲取豐富的營養,促使我們成長進步。
總之,該書把藏文文獻漢譯規范化的問題分析透徹、表述清晰,很有學術價值。但是,我們還不能滿足于現狀,我們肩負的擔子越來越重,尤其是藏漢翻譯,仍然任重而道遠。目前,我們眼見的只是社會科學部分詞匯的翻譯成果,還有大量自然科學的詞匯翻譯等待我們去探索研究,而且各行各業每天還在不斷出現新的名詞術語。因此,我們需要加倍努力,辛勤工作,培養大量的翻譯優秀人才,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每個翻譯工作者的力量和才智。
(作者簡介:角巴東主,男,青海省文史研究館館員,青海民大藏學院碩士生導師,研究員。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
(本文照片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