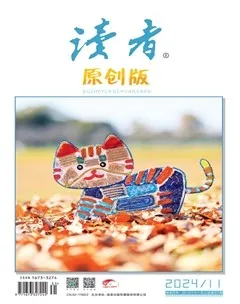一牙西瓜
我經歷的最熱的夏天,是1987年。那一年我18歲,職高剛畢業,在一家建筑公司打零工,為一處新工地架臨時輸電線。
新工地其實還是一片田,連圍墻都還沒打,一望無際的稻子在陽光的照耀下,刺得人眼暈。只有一排水泥桿子從遠處的村子逶迤而來,在我們為它們拉上電線之前,它們像一個個孤獨的釘子,嵌在金黃的田野之中。
我和祥兵、老五三個人一組。老五比我們早來三個月,算是“老工人”;祥兵和我是同學。我們本是學家電修理的,但縣城沒有那么多修理店能容納下突如其來的新師傅們,畢業之后,我們就一起來到建筑公司。雖然從沒架過線,但這個年紀的大男孩兒,誰沒爬過樹?幾天下來,我們爬得比老師傅都快。也正是這個原因,田壩中間最難架線的幾根桿子,交到了我們手中。
天藍得一絲云都沒有,太陽像個熊熊燃燒的火球,紋絲不動地掛在天上,谷子地上面,一點風都沒有。
本來,我們像所有建筑工地一樣,早晨7點開工,干到10點多就休息;等到下午六七點鐘,太陽不那么辣了,再干到天黑,可以直接避開日頭的煎熬。
但問題是,我們這里是新工地,離城幾里地,最近的村子也在一公里之外,周圍連一個瓜棚、一棵樹都沒有。老五和祥兵的家在離城更遠的鄉下,不想來回折騰,他們一致決定,長痛不如短痛,咬咬牙,一口氣整完再說。我沒辦法,只有少數服從多數,奉陪到底。
我們三個沖向了各自的崗位。老五上桿子,祥兵負責往上吊配件,我負責把松散的零件和螺絲組合到一起。
我們很默契地干著。眼里一旦有了活兒,就沒有太陽,只覺得身上不斷癢癢地有汗水滲出,從頭上到脖子再到胸口,先是水珠,再是衣服濕透,然后衣服和褲子上就曬出白花花的鹽。
中午時,我們各自吃了自己帶來的飯。天太熱,食物被太陽烤得很燙,而且有一股怪怪的味兒,我們都怕吃壞別人的肚子沒有互相分享。事實上,我們連看一眼別人飯菜的欲望都沒有。我們坐成一排,默默地吃著。整個世界,只聽得見谷穗和陽光磨擦的細響。我們的頭上,只有電線桿子隨著陽光移動不斷變小的那一線小小的陰影,那是這個世界能給我們的僅有的庇護。
那時,老五剛剛失戀,把父母起的名字“小勇”改成了“飛云”,以此宣示自己擺脫命運的決心;祥兵說等賺到本錢,就跟他舅舅去賣布,一丈可以賺二尺,是一個不錯的營生。
平時吃飯,他倆一左一右,把女朋友和布,塞滿我的耳朵。但那天,他們異常安靜。可能是太陽過于熾烈,把說話的愿望都曬蔫了。我們殘存不多的意識里,只有一個最簡單的字:水!
那時每次出門,老媽都會給我脖子上掛一個軍用壺,裝些涼白開或糖水。水壺之前長久沒用,有一股難聞的腐味,所以,我也不常喝。但那天,在陽光的作用下,這一壺霉水莫名地變成了楊枝甘露,午飯一過,就點滴不剩了。老五和祥兵用罐頭瓶做的茶杯,也大致如此。
這時,我們面前有兩條路。一條是收工去找水喝,這樣不僅來回奔波,還有可能晚幾個小時收工;另一條則是抓緊時間,加快進度,三下五除二把活干完,沖回家抱水狂飲。
我們都選了后者。那時我們不知道有中暑、脫水、熱射病之類的說法,也不懂得保護自己,覺得任何防護都是膽小的表現。
于是,又開始熱火朝天地干了起來。老五上桿,祥兵拖滑輪,我擰螺絲,現場一片叮叮當當。
不知過了多久,我們眼前的風景變得越來越黑。老五說:“不行,我得下來,渴死了,就是喝口秧田里的水也行!”—快要秋收的季節他還說秧田水,可見這家伙已昏了頭!
祥兵說:“這陣兒要是有根冰糕,5元錢我也買!”—這家伙也昏了頭,忘了我們一天的工資是1.4元,而街上的冰糕是5分錢一根。一向摳門的他都這樣說,可見確實頂不住了。
這時,從遠處的機耕道上晃晃悠悠飄來一輛自行車,車座上沒人,叮叮當當,由遠及近,到跟前才看清,騎車的是個七八歲的小男孩兒,腳不夠長,故而以側掛的形式吊在車上,我們小時候也常這么騎。
小男孩兒沖我們喊:“喂,吃不吃西瓜?”
這簡直是廢話。
“多少錢一牙?”我和祥兵幾乎同時喊出來。
“不要錢!”小孩皮膚黑黑的,腦門上的汗反射著陽光,他用力擺著手,還搖了搖頭,“是我奶奶讓我送給你們吃的!”
這莫名的天降福利,讓我們懷疑是不是太陽太烈,產生了幻覺。
那孩子已老練地架好車,把車把上的一個小桶取了下來。桶里有三牙西瓜,泡在水中。
小孩說:“奶奶讓我給你們加兩瓢井水,可以保涼,你們也可以喝,干凈的!”
西瓜表面已有點暖軟,中心卻是冰涼而爽脆的。一大口咬下去,甜甜的汁水在口舌之間爆開,向鼻腔、喉嚨奔涌開來。那又甜又涼的汁,讓我從喉嚨管一直爽到胃里。吃完,把瓜皮往額頭、脖子和四肢一涂,灼痛感頓時化為一片清涼。
桶里的水一滴不剩,全下了我們的肚子。
把桶還給小孩時,我們三個把口袋里所有的錢都掏了出來塞給小孩。小孩擺手:“不能要,奶奶說不能要,就不能要!”
扔進桶里,硬塞給他。
他接過桶,把錢倒在地上,飛快地推上車,猴子一樣躥上去,斜掛著跑很遠,才沖我們喊:“不能要錢,要了錢,老天爺就不保佑爸爸了!”說完,就叮叮當當地消失在一片淚光之中。
那一牙西瓜,讓我們干涸的淚腺,重新恢復了功能。
時隔多年,我一直在想,小孩子臨走的那句話是啥意思?是他爸爸也和我們一樣在外打工,老奶奶善待我們,希望他兒子也能遇上好心人嗎?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不得而知。
一晃37年就過去了,當年那片菜地早已變成一家上市企業的廠房,但我每次經過那里,都會想起那個火熱的夏天和那一牙西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