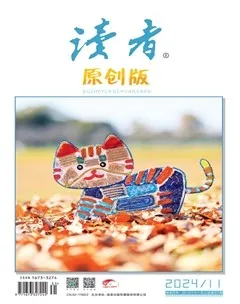身體知道答案
我的左臉有一塊斑。去年一年,我起碼處理過三次,處理手段包括超皮秒、光子嫩膚、服中藥等。如今,斑是變淡了,卻無法根除。出門前,我將粉底、遮瑕、修容高光一一上齊,仔細拍打,仍隱約可見。有時,我對著鏡子不免氣餒,但我不能持續焦慮,因為這斑,便是因焦慮而來。
一年多前,我從一座城市搬回另一座城市。我需要在一個月內完成買房、遷移戶口、孩子轉學的任務;兩個月內,搬完家。等一切塵埃落定,我才有時間細致端詳自己,發現我的唇角長著泡,臉上有痘,痘消除了,痘印還在,痘印漸深,變成了斑。
我去醫院皮膚科看醫生。幾年前,我工作壓力大時也曾爆過痘,在頻繁看臉的過程中,我和醫生成為朋友。醫生見到我,脫口而出:“你現在怎么像個黃蘋果?”她說的是我的皮膚,也是我的氣色、狀態。說黃蘋果是客氣了,確切地說,是放了很多天,皮已出現皺褶的黃蘋果。開藥,安排治療,醫生叮囑我:“放輕松,你這都是急的,焦慮反映在臉上。”
可是我在做事時,明明有條不紊、按部就班,自認為心平氣和、指揮若定啊。
“但是你的身體知道答案,你以為你的極限不止于此。可身體說,你太焦慮了。而你的情緒、你的壓力總要有一個出口,總會在某個地方展現。”醫生像哲學家,也像心理咨詢師。
身體知道答案。
我想起我的大學同學華。
我和華本科讀的是師范類專業。畢業后,優秀的華順理成章地成為省內一所示范高中的老師。我們是在畢業三周年的聚會上再相遇的。令我吃驚的是,僅僅三年,華胖了,或者說有些腫脹;眾人聊天時,華的反應總顯得慢半拍,問她點兒什么,她需要湊過來,把左耳朝向提出問題的人,還一再要求:“你再說一遍,我沒聽清。”
“華,你的耳朵怎么了?”終于有人按捺不住好奇。“你再說一遍,我沒聽清。”華又湊過去,她的動作說明我們的猜測沒錯。所有人對視一眼。
此時,華的男朋友、同是同學的陳推門進來。一番問詢,一番關心,一番嘆息,再一番解釋。
原來,一向優秀、順遂的華,這一年經歷了此生從未有過的坎坷。一年前,華所在的中學接到重要任務,要準備一節歷史課本劇公開課。沒有現成的教材、劇本,一切從頭做起。教研組長王老師,一位一直以來慈眉善目、對華很友好的大姐,對華說:“咱們一起干吧,我負責協調,你負責內容。公開課時,我先上場介紹,學生們自主表演,課上完,你去謝幕,咱倆完美展示,默契合作。”華答應了。此后,華的辛勞無須贅言。挑選學生,設計劇情,撰寫劇本,帶領學生從零基礎開始排練,一遍遍磨課,聽意見,推翻,重建,再推翻,再重建,直至確定最終版。公開課的日子來到,華和王老師均盛裝出席。
課程形式新穎,吸引了領導和同事的注意。課程以學生表演為主,老師只在開場介紹和最后的總結環節出現。王老師對華說:“我年紀比你大,資歷比你老,我先上;你留著壓軸。”華不疑有他。課程以“昭君出塞”為主題,臺詞風趣幽默,學生演員們配合默契,表演熟練。一看就知道,輔導老師和學生都下過狠功夫。以道具為例,王昭君的頭飾、衣服、琵琶,無一不是華自小商品批發市場親自挑選、購得,王昭君額頭的流蘇飾物,是華一點點用膠水粘起來的手工作業……
40分鐘很快過去,掌聲雷動。即將謝幕時,華正準備登場,卻被王老師攔住。王老師一個箭步登上臺,如課開始時一樣,她感謝觀眾,感謝臺上的小演員。華坐在臺下,震驚、震動,不可置信。她想沖上臺,但禮貌、教養不允許她這么做:今后還要在學校工作,教育局、學校的領導,以及同事,還有校外來觀摩的老師會怎么看她?他們會覺得她冒失、沖動、莽撞,而因此造成的后果,她承擔不起。此外,華其實還抱著一絲希望,希望王老師會想起她、提到她,會邀請她一起致謝、鞠躬。可是沒有。下課了,眾人魚貫而出,王老師像剛舉行完婚禮的新人,站在教室門口,微笑、致謝。華在一旁盯著她,王老師碰到她的眼神,躲開了,但神色自若,像什么都沒發生。
華鼓起勇氣上前,她想問責,話說出口,口氣卻是軟的:“王老師,有空時,我們溝通下,關于……”人未散完,當著他們,王老師一把拉住華,摟著她的肩膀,顯得親熱:“小華老師,這次公開課的效果出乎我意料,真得感謝你啊!前段時間,我教研任務太重,你盯過兩次排練,我一定要請你吃頓大餐!”王老師直接抹殺了華在公開課中與她的合伙人身份,只是“幫忙”“兩次”“盯過”,只值一頓“大餐”。華扭頭就走,邊走邊滾下淚來。
父母安慰華,說想必王老師日后見到她會感到羞慚,作為教研組長,以后有什么機會會給華。男朋友持反對意見,他要為華出頭,向教育局舉報,被華攔住:“我畢竟是個新人。我有證據嗎?這點事兒,我越不計較,越云淡風輕,越顯得我格局大。”
華正常上班,正常上課,沒有人能看出她的心事。王老師和她打招呼,她冷漠而保持距離。她掩藏得很好,告訴自己吃一塹長一智,打落牙齒和血吞,算了。誰知,公開課后的第十天,華在講臺上點學生回答問題時,學生回的話,她聽不見了。
去醫院檢查,應激性耳聾。在不在乎,計不計較,創傷有多大,華說了不算,身體說了算。她不能教學,遂請假休息,經過一個學期的調養,才逐漸趨常,可是仍然有些遲鈍。
身體知道答案。
我坐在醫院的長椅上,等代煎的中藥。我刷手機,看到一則微信朋友圈消息。一個熟人說,閉關至少三個月,閑事勿擾。理由是,他得了帶狀皰疹。
熟人以業務強、能扛事聞名圈內。不管發生什么事,他都用“這事好辦,我來辦”來緩解下屬、合作方的慌亂、緊張。比如前不久,他在異地籌辦一場演出,廣告打出去了,票賣完了,臨時出現情況,演出不能在線下如期進行。他鎮定自若,退票、道歉,把線下的演出搬到線上,據說,不但沒賠,還賺了—賺了錢,賺了名聲、口碑,堪稱“隨機應變經典案例”。
我打了個電話給熟人,問他的情況。“我當時以為沒事,事情一件一件處理,辦法換了一個又一個。驚險又圓滿地解決后,我回京,身上沒力氣,持續低燒,疼,成簇的丘皰疹和水皰長成片。醫生說,我是急的。”
身體知道答案。再淡定的人,演技再高明,偽裝得再好,別人以為在你那兒不是事兒,有時你自己都覺得不是事兒,但身體不會騙你,它會發出警報,提醒你,警告你,幫你記錄你受過的重創,你經歷的坎坷,你于無聲處聽過的驚雷,留下的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