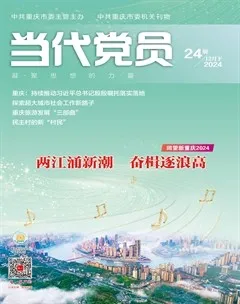恢復高考:“我們”見證



1977年12月9日、10日,重慶市舉行恢復高考后的首次文化考試,首批報考大學的7萬余名考生在全市13個區縣參加文化考試。
魯善坤,男,1977年高考考生,曾任重慶第一中學校校長等職;
戴偉,男,1977年高考考生,曾任長江師范學院院長等職;
黃良,男,1977年高考考生,曾任教于重慶師范大學文學院;
陳立厚,男,1977年高考考生,曾任教于成都大學教育科學學院;
龍莉莉,女,1977年高考考生,曾任教于重慶大學原城市建設與環境工程學院;
徐鳴,男,1977年時任重慶市經委教育處處長,負責高考招生錄取工作;
龔其昌,男,重慶南開中學高1977屆5班班主任、政治老師,所帶班級這一年高考錄取率為7%,高于全國平均錄取率。
1977年12月9日、10日,重慶市舉行恢復高考后的首次文化考試。首批報考大學的7萬余名考生,在全市13個區縣參加文化考試。考生、教師、招考工作者……對于每一位參與者來說,這兩天的經歷,注定成為一生難忘的記憶。
隨著高考恢復,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社會風氣重新形成,這一重大舉措改變的不僅僅是個人的命運,也是整個國家的命運。
一聲“春雷”
1977年10月21日,國務院批轉教育部《關于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正式恢復高等學校招生統一考試制度。這一消息,在那個沒有網絡的時代,以驚人的速度迅猛傳播。秋冬時節,“恢復高考”的消息如春雷般振奮人心。
1977年高考考生、曾任重慶第一中學校校長的魯善坤,當時已是沙坪壩區新橋小學校的一名英語老師。得知恢復高考的消息后,魯善坤在激動之余也擔心自己是否符合報考條件。直到看到高考須知,確定自己滿足報考條件時,魯善坤一顆懸著的心才終于放了下來。
1977年高考考生、當年已經27歲的戴偉,從收音機里聽到“恢復高考”的消息后,受到親友的鼓勵,決定參加考試。和魯善坤一樣,作為一名老師,戴偉在當時的江津地區雙鳳完全小學任教。戴偉的妻子也是一名老師,而且已有身孕。他們的兒子于1977年11月2日出生,妻子默默承擔著生活的壓力,支持戴偉專心備考。
因“恢復高考”消息而振奮的不僅僅是考生。時任重慶市經委教育處處長、負責招生錄取工作的徐鳴,得知消息后,和幾個同事高興得擊掌相慶。從事招生工作多年,他們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重大舉措將給國家帶來大量人才,是一件事關國家強盛、民族復興的大事!
徐鳴記得,重慶市招生考試辦公室正式接到高考招生任務后,市里分管教育的領導就開始積極布置并開會強調“任務重,時間緊”。當時,大家的第一反應都是:事關國家人才培養,保證完成任務!
有備而來
常言道,機會總是垂青有準備的人。對于1977年的高考考生來說,有準備意味著有一定的文化基礎和過人的毅力,以及些許機緣巧合。從1977年10月21日新華社正式發布“恢復高考”的消息,到12月9日開考,備考時間不足兩個月,備考壓力可想而知。
1977年,32歲的黃良已是一名父親。他曾是重慶南開中學1965屆畢業生。參加1977年高考前,他在大巴山度過了7年知青歲月,然后又在重慶電機廠當了5年工人。當時,他的月收入是38.5元加40斤糧票,這在當時是個不錯的收入。很少有人知道,黃良其實為這場高考,已經準備了12年。高中畢業后,無論是在大巴山的山野中,還是在電機廠車間昏暗的燈光下,他從未放棄過對書本和知識的追求。
時隔40多年,黃良回憶說,之所以那12年他能堅持讀書“充電”,是因為他腦海中始終有一個堅定的信念:國家和民族復興的希望終會回到強大的教育以及對知識人才的足夠尊重上。
與其他考生相比,南開中學、重慶一中等學校的考生算是幸運兒。因為學校的老師們更為關注國家在科教領域的新動向,消息也比較靈通,對恢復高考有一個預判。
南開中學高1977屆5班班主任、政治老師龔其昌記得,學校于當年9月就啟動高考生的復習教學。重慶一中也是在當年9月就著手學生復習備考工作。當年,龔其昌除了帶自己班的學生,還為大量其他考生補習。當時,南開中學在圖書館辦了一個復習班,聽課的包括往屆畢業生以及工人等。此外,龔其昌還被學校指派到西南醫院為備考的醫生、護士上課。那時,龔其昌的月工資是53元,沒有任何額外報酬。
“我們心中想的,都是如何幫助這些孩子完成自己的夢想。”時隔40多年,龔其昌依然認為自己當年的付出非常值得。
眾生“趕考”
失眠,是1977年高考考生后來回憶那場考試時,頻繁提到的一個詞。
1977年高考考生、后考入重慶師范學院(今重慶師范大學)數學系的陳立厚,在高考前一晚失眠了。想到自己高中畢業11年后,還有機會踏進考場,他的心情萬分激動,通宵難眠。
陳立厚是1966屆高中畢業生。恢復高考這一年,陳立厚正在四川省彭縣(今四川省彭州市)九尺中學教書,擔任數學老師和班主任。備考期間,他白天處理班級事務,夜晚批改學生作業,只有晚上10點至12點的兩個小時用來復習。還未完成一輪系統復習,高考的鈴聲就已經敲響。
1977年12月9日清晨,失眠了一夜的陳立厚起床后,洗了一把冷水臉。他深覺機會難得,再疲憊也得搏一把,精神又重新亢奮起來。結果證明,他的斗志戰勝了失眠的影響,各科發揮都比較平穩,強項數學甚至考了98分!
黃良從住所到考場要走一個多小時,他對高考那兩天的第一印象是冷,冷得僵手僵腳,一件老棉襖根本無法抵擋寒風,最初下筆都不太順暢,得哈氣暖手。上午和下午都有考試,中午他用兩個饅頭充饑,然后在考場外找了一個避風的地方休息看書。
1977年高考考生、重慶大學退休教授龍莉莉,因為住所離考場遠,在考試前一天上午,她就背著被子,乘了3個多小時汽車趕往考場。幾間廢棄的教室被當作考生們的臨時宿舍。晚上,考生們擠在臨時宿舍里,把各自帶的被子鋪在稻草上席地而臥,不知不覺就聊到了次日凌晨4點。
考政治時,龍莉莉靈感爆發,居然寫了滿滿8頁紙!揮鋤頭的手抓筆桿子,絲毫不馬虎,寫得暢快淋漓。監考老師看龍莉莉總是找她續紙,索性站到她旁邊發紙。
在考生緊張赴考之際,招考工作人員也在以另一種方式“趕考”。考試前一天,徐鳴冒著雨到江北考場檢查工作。檢查的主要內容是,考場是否達標,路途是否安全,交通是否便利……只為將考場不利條件降到最低。
考試前,考卷由重慶市公安局派出專人專車押運,醫院派出醫生負責應對考生身體方面的意外情況。當時,市招考辦還有一條內部工作準則:對每個考生都要笑容相待,不要給予他們壓力!大家最不想看到的,就是開考30分鐘后考生未能到場。
同頻共振
1977年參加完高考,錄取結果還沒出,戴偉就在日記里寫下這樣一段話:“一定要為祖國爭光,一定要為人民作貢獻!考得起,就要認認真真讀書,為國家作貢獻;考不起,就好好教自己的學生和孩子,讓他們有更好的生活。”
1977年12月30日,戴偉收到去體檢的消息——這意味著考上了。那個傍晚,他跑了20多里山路,來到在復興公社完全小學任教的妻子面前,喜極而泣。1978年3月2日,戴偉拿到了西南師范學院(今西南大學)的錄取通知書。
1978年3月,全國科學大會舉行,“科學的春天”激蕩全國人民心田。也是在這個3月,一份份錄取通知書,送到了那些在1977年高考中成功突圍的考生手里。一件是國家大事,一件是人生大事,在“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主旋律中同頻共振。
1978年3月14日,陳立厚踏進了重慶師范學院的校門,這一天是他31歲生日。那時的高校,缺設備、缺教師、缺教材……唯一不缺的,就是教師的敬業精神和學生的學習熱情。每天下午課外活動時間,教室里依舊座無虛席,系領導想把大家勸出教室:“這樣學習怎么行呢?把身體搞垮了,來日方長啊!大家要注意休息!”
即便是7月底的酷暑中,教室里既無空調也無電風扇,同學們也會堅持上課。降溫的辦法很簡單,腳泡在盆里,頭頂濕毛巾。他們還要求系里給大班單獨開選修課,甚至在畢業前半個月還在上選修課。同學們不遺余力地學習,只有一個念頭:要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
盡管在1977年高考中“上岸”的是極少數人,但隨著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價值觀和社會風氣重新形成,隨著科學春天來臨、改革大幕開啟,青年成長成才的機會越來越公平、廣泛,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所需的人才基礎得以奠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