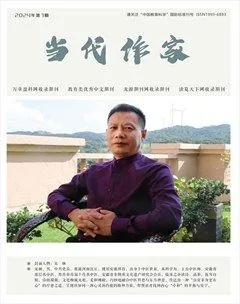羅余作

我家的“人世間”故事|老屋不老
作者/ 羅余作( 江西)
老屋累了, 父母也都累了。但是老屋不老, 它伴隨著父母親經(jīng)受的風(fēng)雨,讓我們永遠(yuǎn)記下了父母親的一生。老屋,雖說完成了它的使命,但父母親的氣息尚在。這給每逢歸來的子孫總能找到回家的感覺。
老屋不老的時(shí)候,母親給它拾掇得干凈利落, 井井有條。一年四季,農(nóng)家風(fēng)景別致。春天,屋前院子里的桃樹、石榴、棗子、桔橙、桑葚… …總會(huì)給老屋花香。燕子在廳堂喳喳喜鬧,雞鴨貓狗隨我們走動(dòng)。夏日的傍晚,灶屋里升起青色的炊煙,那些糙米皮谷、蘿卜青菜,在母親的侍弄下,總會(huì)飄逸出誘人的香味。秋天,清風(fēng)在老屋的瓦楞上咝咝流唱,時(shí)時(shí)飄來院外的果香。冬天,一場雪,就把老屋飄進(jìn)了一個(gè)童話的國。寒冷的晚上,一家人圍在火爐邊烤火聊天。父親時(shí)兒教演算盤、吹吹喇叭(嗩吶) 、拉拉二胡,時(shí)兒訓(xùn)練我們運(yùn)用笙、鈸、木魚、鑼、小鼓、碰鐘樂器。
每逢夏日掌燈時(shí)分, 勞作了一天的家人聚在屋前院內(nèi)一張小小的飯桌上享受著兩三個(gè)鄉(xiāng)間小菜。飯后, 父親點(diǎn)上煙, 搖著蒲扇, 給我們講那些永遠(yuǎn)動(dòng)聽的故事: 牛郎織女、嫦娥奔月、寶蓮燈、共產(chǎn)黨、紅軍、土改、抗美援朝、三年改造、人民公社,還有家鄉(xiāng)那些坡池橋水等名字的由來。童年的心境,在夏日夜晚的院落里, 盛滿了一湖如水的月華。聞著泥土的氣息, 聽著故事, 在這所貧寒而溫馨的農(nóng)家院落里, 我們?nèi)諠u長大。
老屋成了我心目中的神殿。父母親健在時(shí),家境雖然貧寒,但充滿快樂。后來,我們雖說跳出了農(nóng)門,讀了大學(xué),在城里有了工作安了家,可總不忘回家看看。只要灶里還有閃爍火光,就是我們心靈最幸福的歸所。
老屋與共和國同歲。1997年春天,母親鼓起勇氣說,老屋前后土墻快不行了。看得出,母親透出多年的痛楚。父親早在1985年就離開了我們。倘若父親健在,他會(huì)對(duì)這等事深思熟慮實(shí)施周全。父親是個(gè)能人, 從前, 無論社隊(duì)里什么大事經(jīng)他料理, 便會(huì)卓有成效。
聽了母親的話, 我這才關(guān)注老屋。老屋也似乎更顯沉靜, 前后土墻流離凹陷, 窗子像經(jīng)久失眠老人深陷的眼睛。一件件漆色斑駁的古舊家具, 廳堂寶壁字畫和東西滿墻張貼的我們讀書獲得的獎(jiǎng)狀已黯然失色。此時(shí),燕子回飛, 幾只麻雀瑟瑟地站在屋頂上, 在斜陽里,無聲眺望著這片令人心顫的殷紅。我想, 倘若老屋拆除改新了, 這些麻雀, 還有明春歸來的燕子,它們是否還能記憶曾經(jīng)那個(gè)溫暖不變的家呢?
我一寸一寸,苦苦尋覓……面對(duì)老屋舊墻、里屋和臺(tái)上牌位, 又透思了好一陣。老屋墻上, 仍掛著一串紅辣椒。窗臺(tái)上, 還有幾個(gè)干葫蘆和絲瓜。這里是父母哺育我成長的地方,它曾經(jīng)帶給我們童年的夢(mèng)幻和樂趣。
1999年,世紀(jì)輪回。春節(jié)提出改造老屋的設(shè)想在老母的再三催促下,終于在1 0 月底拉開了序幕。經(jīng)過清基、建造、飾面、竣工, 歷時(shí)4個(gè)月, 總算成就了這跨世紀(jì)的工程,滿足了一家老小的一大心愿。
如今,面對(duì)父母基業(yè)上改建的新屋,老屋的影子還在我們的心頭縈繞,因?yàn)樗俏覀兩谒归L于斯的福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