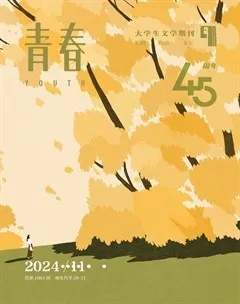享受寫作,享受漢語,享受屬于自己的故鄉
金倜:興化“畢飛宇工作室”在國內文學界已頗有名聲,成立至今已經走過十年歷程。支撐起工作室的有兩大內容,一是“小說沙龍”,二是“廣場書屋”,前者為活動,后者是陣地。不管是“小說沙龍”還是“廣場書屋”,都贏得了普遍贊譽,形成較好的社會影響。為此,請您說說對這十年的感受和評價。
畢飛宇:是的,工作室今年十周年了,這十年我們經歷了許多快樂的時光。“小說沙龍”這一部分,我們發現了很多好作品,提升了興化作者的整體實力,現在的興化作者可不是十年前了,能力上有了很大的提升。實際上,“小說沙龍”的影響力早就超出了興化,這是我特別滿意的事情。“廣場書屋”這一塊,它事實上已經成了老城區的小型圖書館,很多孩子在這里讀書,很多父母也在這里讀書,我要感謝興化的中小學老師們,是他們的義務勞動保證了書屋的常態。
金倜:是的,“小說沙龍”北上天津、東進上海、西到成都,在這些大都市的高等學府引起轟動,熱愛創作的大學生們踴躍參與。在跟他們的交談中,他們都表示這樣的文學活動會影響自己一輩子。每逢假期,我們常常遇到慕名參觀“畢飛宇工作室”的大學生。至于“廣場書屋”,真的要好好感謝您,當初是您提議建一個書屋,有領導提出就叫“畢飛宇書屋”,您表示不妥。工作室位于文化氣息濃厚的儒學廣場,門前有“父子科第”的牌坊,不如就叫“廣場書屋”。更要感謝您的是,您為書屋募集到三萬多冊圖書,從中國出版集團到作家個體,大家紛紛捐出高質量的圖書。從此,興化市民和孩子們就多了一個書香去處。
畢飛宇:能為家鄉做貢獻,我很高興。
金倜:“畢飛宇工作室”鬧中取靜,已經成為學生、老師和家長們雙休日的首選。讀書、寫作、聽講座,而閑談時大家更關心的是——畢老師有沒有回來?工作室當然會越辦越好,更何況地方上十分重視這個文化窗口的建設。您對此有規劃框架嗎?您能經常回家看看嗎?
畢飛宇:正如你知道的,在我成為江蘇作協的主席之前,我每年起碼要回去四次,我喜歡一群人圍繞在一起暢所欲言的生活。但我沒有規劃框架,我所渴望的是看到很多的熱愛,熱愛是不需要計劃的。利用這個機會,我也想表達一下我的感謝,工作室有今天的局面,我要感謝劉春龍、龐余亮、你還有郭亞群,沒有你們,工作室不可能是這樣。
金倜:我一直覺得《孤島》跟您之后的作品不太一樣。這也是您的處女作,記得我和龐余亮在興化老圖書館的閱覽室翻閱《花城》(1991年第1期),一打開就看到了畢飛宇的名字,看到了《孤島》。我們很失態,聲音陡然高了八度:畢飛宇的小說!我們畢飛宇的小說!我們的同學!當時有看報紙的老者咕咕噥噥嫌我們吵,但也有年輕人湊過來看。近視眼的龐余亮恨不得把臉埋進字里行間去。這還不夠,我又跑到您家里,告訴您父親,畢飛宇是小說家了,在大刊物發表了很長的小說!老爺子一定已經讀過,平淡又難掩愉悅地說,嗯!像個歷史學家了。文學界對您的獲獎作品討論得比較多,我想請您跟老家的文學愛好者們聊聊《孤島》。
畢飛宇:《孤島》寫于20世紀80年代的最后一個夏天,嚴格地說,是初夏。在此一年之前,我似乎有一個預感,我的寫作應該從“孤島”開始。我做了一些準備,大量閱讀揚中縣(今揚中市)的一些史料。老實說,我對那個史料的真實性是有懷疑的,它偏于傳奇性和戲劇性,但是,這沒關系,我也不是真的去做歷史研究。我認為這是一篇不恰當的作品,我的雄心太大了,而我當時的能力與我的雄心并不匹配。這是可以理解的,那不是一個安分的時刻,我太想表達了,過分的表達欲望讓我的處女作顯得焦躁不安。我很珍惜我的處女作,它確認了我后來的軌跡,即使后來我成了一個文本意識很濃的作家,“發言”的欲望也沒有絲毫降低。我喜歡這樣,我就是想“發言”,它保證了我作品的“勢”,哪怕是極小的題材,我也希望我的作品可以保持那種“勢”。
金倜:您不止一次談過《孤島》的編輯朱燕玲老師,總是心懷感激,那次“小說沙龍”走進上海大學,我也有幸見到了朱老師。您跟家鄉的文學愛好者談談《花城》和朱老師吧。
畢飛宇:我寫過一篇關于《花城》編輯朱燕玲的文章,她是我處女作的責任編輯。是朱燕玲老師從一大堆的自然來稿中替我把《孤島》發表出來,我一生都感謝她。無論未來的讀者如何看待《孤島》,以它作為我文學人生的起點,都是一件令我自豪的事情。早期,在我還是“文青”的時候,一直都在給他們投稿。那時候,我對《花城》有一個判斷,它更前衛,它更容易接受年輕人。《花城》到現在都有這個特點,有些時候會走得比較遠。那時候只有《花城》愿意發我的小說。那可不是現在,作家主要和出版社打交道,那時作品主要在刊物上發表,一個年輕人想在期刊上得到一次機會并不容易。1990年前后,文學的熱度一下子下去了,年輕人的機會更少了。
金倜:不記得在哪個場合,您說您一沒有姓氏,二沒有故鄉。有人當真,而我知道這是您的語言風格,一如您的小說機智而深刻。不管是《哺乳期的女人》《地球上的王家莊》《武松打虎》,還是長篇小說《平原》,明眼人都知道您在寫作的過程中,潛意識里始終有故鄉的影子,所以我想請您說說關于故鄉,關于故鄉與您創作相關的話題。
畢飛宇:我確實沒有故鄉,我出生在大營陸楊,那只是我父母下放的地方,沒有任何血緣關系,當然不能說是故鄉。故鄉是有硬標準的,我為我沒有故鄉感到遺憾。這樣的遺憾一般人是很難理解的,它會讓人早熟,早熟從來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沒有故鄉,故鄉就會構成我的偏執,當然,你不能說我對興化的鄉村不了解,事實上,我很了解,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對蘇北鄉村的描寫就會很扎實。我愛那一片土地,我愿意把它看成我的故鄉,然而,太遺憾了,我沒有故鄉,我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土地的客人,我從來沒有主人的感覺。
金倜:《文學的故鄉》系列紀錄片在央視播出后,引起巨大反響,而我們最感興趣的自然是關于您的那一集。隨著鏡頭轉換、畫面更迭,以及旁白和您的現身說法,我們窺見了您人生的沿途秘密。在其后的訪談中您也說過:“我沒有故鄉,那個地方和我沒有任何血親關系。如果你們從紀錄片里看到我有情緒上的反應,那不是‘近鄉情更怯’,跟那個沒有任何關系,它是別的。”那究竟是什么呢?
畢飛宇:這個話題比較大。實際上,我在拍那個片子的時候,完全處在一個具體的情緒里,當時究竟是什么樣的狀況?用紀錄片導演張同道先生的話說,拍紀錄片有點像在海邊撿貝殼,能不能撿到,不在于勤快還是不勤快,而在于去的時機——在海浪把貝殼帶來的時候把它撿回來,去得早了或晚了,都撿不到。我們不是在創造一個東西,我們是在撿拾。
金倜:張導顯然是撿到了,我記得您回到童年生活過的地方,您的情緒鼓脹而不事修飾,我們看到了您的淚水。張導曾說,一開始您并不想回來拍童年,而是找一個相似——其實是似是而非的地方,走個過場,但您很快就改變了主意,決定回到闊別三十多年的地方。這個改變應該是一剎那的事,其中緣由是什么?
畢飛宇:拍回楊家莊這個段落之前,我們一直在糾結,要不要回去。我的意思是算了,這次就不去了。他也不能非逼著我回去不可,于是,我們就找了一個跟我記憶中的村莊很像的地方,也就是你所說的似是而非的地方,準備在那里拍攝。但當真正要拍我回村莊去講述的時候,我在那座陌生村子里走了不到一圈,一路無言,到一個巷口后,我陡然覺得不對,一回頭,說,不拍了,還是要回到楊家莊。要說緣由也沒什么可說的,我已經三十多年沒回過楊家莊,上次回去的時候還在上大學。
金倜:在紀錄片里我們看到,您已經找不著路了,不知道原來的房子在哪兒,一路打聽。當您本能地做出一個充滿情緒的動作時,我們知道,您找到了自己出生的地方。有人覺得,拍電視這可能是事先設計好了的。
畢飛宇:絕對不是設計。如果三十年后和這個地點的相遇都是設計好的,我想當時的感情也就出不來了。拍這集紀錄片,不是為了去表達某一個作家在某一個地點有什么樣的情緒反應,有情緒反應更好,但目的不在此。
楊家小學是我1964年出生的地方,當年我的父親很不堪,母親也很不堪,就在那個地方把我們養大。它和我沒有血緣關系,跟我的父親也沒有血緣關系,是命運讓我的父母在那兒生下我。這跟一般意義上的回鄉,跟對故鄉的情感、思念都沒有關系。某種程度上來講,隨著歷史的變化,父母離開,我也離開,切割了。那個地方和我沒有任何關系,不想再要它了。所以,我最早提出的方案是替代品。但在路邊走了幾步以后,我內心生發了一個道德問題。導演打算去拍一下我的童年時光,觀眾也不知道那個地方到底是不是我的出生地,但我走來走去總覺得不對,內心有一個聲音在告訴自己——它不真。
金倜:怎么理解“它不真”?
畢飛宇:“不真”就是假,對我來說,面對個人的過往,我知道回去之后有可能發生什么,但即便如此,“不真”在那個剎那,也是不能被接受的。我不能忍受,因為我在另一個村子走動的時候,導演和鏡頭跟著我走,我們的老同學龐余亮也在旁邊,這就存在一個必然結果——無論走路還是說話,我都得表演。表演和“不真”是因果關系,即便有時候還能接受“不真”,但對當事人來講,表演自己還是很困難的。
這還是一個潛在的道德問題。跟我們通常意義上的道德可能不一樣,它是一個對自己如何交代的問題。而我覺得作為小說家,這個問題是致命的。你可以在這兒撒謊、不真、表演,你可以把這種“不真”和“表演”帶到生命的任何部分,最后你整個人生很可能都是假的。說起來有點大,挺沉重,但它很真實。忠實于自己的歷史,忠實于自己兩只腳的步行動態,忠實于自己跟人說話時的目光交流,不僅對作家重要,對我們每個在生活現場的人來說都至關重要。
金倜:我是讀《生于1964》知道了評論家李敬澤的,記得我那天給您打了個無聊的電話,就說了一句:這人寫得真好。后來,我去南京看您,居然見到了“寫得真好”的“真神”,一起逛古城墻,我就是個跟班聽眾。記得你們談南方和北方的楊樹之異同,旁若無人,腔調就是一名小說家和一名評論家的對話。扯這個話題,我就是想聽您說說作家與評論家的關系。
畢飛宇:作家和評論家的關系,東西方很不一樣。在我們中國,作家和評論家的關系相對比較緊密,西方則要疏離得多。哪一種更好呢?我個人還是喜歡保持與評論家的對話關系,當然,作品的質量得夠。小說家是低頭走路的人,評論家相反,他們習慣于擁有更加開闊的視野。如果一個作家的心臟比較大,不懼怕批評,不擔心被否定,我覺得小說家可以從評論家那里獲益良多。
你見過李敬澤,我要說和李敬澤認識對我很重要。1994年,我在《作家》發了一個短篇,叫《枸杞子》,李敬澤在《人民文學》轉載了,這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這樣的事情大概也只有李敬澤做得出來。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很普通的,就是在路邊的小飯店吃了一頓飯,是吃飽肚子的那種性質,也說了一些閑話,我估計我們彼此都沒有留下什么特殊的印象。那時候山東有一份報紙,叫《作家報》,有一天,我讀到了李敬澤的文章,這一讀嚇了我一跳,那文章寫得,太帥了。也就是從那個時候起,李敬澤開始了他的評論家生涯。我要說,李敬澤這個人是很另類的,在文學圈內,許多人對自己都有一個錯覺,覺得自己才華出眾,李敬澤他剛好相反,在很長時間內,他似乎并不了解自己,他不知道自己擁有怎樣的才華。這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這個也許和他的出生與成長有關,他遇見的牛人太多了,他沒拿自己當回事。也許和他很年輕的時候就做文學編輯有關,他只看得見別人的閃爍,就是看不見自己。
我們碰面的次數并不多,遇上了總要巴山夜雨。我們討論文學,每一次都像學術研討那樣,我們的討論很有質量,涉及面非常廣,同時也很深入。他對我的影響是巨大的,無論是學養還是美學上的趣味,我都很信任他。信任有多種多樣,但對藝術家而言,美學趣味上的信任極其艱難。
金倜:高山流水,果然令人肅然起敬,好生羨慕呀。
畢飛宇:關于人生,我始終有一個認識,批評到哪一步,友誼就到哪一步。
金倜:其實我們的小說沙龍作品討論就是一場面對面的文學批評,記得您在畢飛宇工作室的留言是:在這里,善意的,真誠的,尖銳的。我覺得這是我們工作室特別好的“家風”。有一期小說沙龍火藥味很濃,之后就緩和了好多,您對此怎么看?
畢飛宇:其實,批評和批評很不一樣,有些批評就是文學批評,我覺得這樣的批評很美學,很高尚,如果是打著文學批評的幌子在那里做市儈式的批評,我自然也很不喜歡。這兩種批評是很好區分的。在我們的小說沙龍里,我很鼓勵批評,這不僅存在一個文學的認識問題,某種程度上,它也提升了反批評的能力。文學是離不開批評的,我不認為小說家都必須具備批評家的能力,但是,如果一個小說家具備了,我覺得是好事。
金倜:文學批評不是吵架,要本著善良和真誠,這樣一來才暖心。
畢飛宇:對,價值尺度是一個極為要緊的東西,沒有價值尺度,你的批評就是罵街,沒有價值尺度,你的愛就是花癡。
金倜:《蘇北少年“堂吉訶德”》應該屬于兒童文學范疇。而您好像很少寫兒童文學,還有就是您的散文作品也不多。其實您的許多隨筆都很精彩,《沿途的秘密》就是明證,您能不能跟我們說說個中緣由。
畢飛宇:關于散文寫作,我曾經表達過自己的觀點。我認為散文是個可怕的東西,寫散文需要暴露自己,但人都有保護自己的愿望,所以,寫散文要放棄虛構,更要控制好情緒,掌握好節奏。散文不能僵化,不能虛假,否則,人不死散文會死的。在更多的時候,文學創作總是逼近了生活的質地,逼近了生活的秘密,逼近了生活理想的時候,綻放出開懷的笑聲。我不在乎題材,我也不在乎體類,我能確定的就是我在寫,通過你的審美趣味,讓你的書寫充滿魅力,這就是書寫的樂趣和秘密。我對我的寫作有要求,你要問我個中緣由,這個緣由就是要求。
金倜:關于《蘇北少年“堂吉訶德”》,您跟老家的孩子們分享一下您的想法吧。
畢飛宇:這本書的內容很簡單,就是一個鄉下孩子的普通經歷,我們都曾經歷過。如果說這本書還有一點意義,那就是我童年和少年的背景。我直面的不是宏觀的描述,也不是大數據時代的數據化分析,而是最基礎的東西,無法回避的東西,也就是日常生活的呈現,一個孩子在小村莊里的吃喝拉撒。這也是我一貫的做法——我不太選用大材料,即使是宏偉的建筑,我也喜歡用小材料一點一點地往上壘。我不敢說我就是一個誠實的人,但是,我朝著誠實的方向努力。在這本書里,誠實是第一位的東西,它不是道德,而是方法論。
農村生活沒有多了不起,我本人并不稀罕。現在的孩子不了解傳統的農業文明和農業社會,這不算什么損失,但是,孩子們和大自然脫離開來了,與大自然失去了切膚的關系,只剩下網絡里的知識,概念和詞匯,這個損失是比較大的,也許一輩子都無法彌補。對一個孩子來說,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有兩樣,一是冥想,二是做白日夢。這牽涉到一個人精神上的寬度和深度。從小就熱愛冥想的人,長大之后他的精神面積和體積是不一樣的。還有一個就是表達的欲望。你可以害羞,可以不愛說話,但是,表達的方式有多種,你還可以寫,可以畫,可以彈,可以唱,甚至你還可以撒潑打滾。對一個孩子來說,表達的欲望不一定符合規范,這個可以慢慢糾正,但我們不能把表達的欲望給扼殺了。在我看來,無論你將來做什么,童年最珍貴的東西就是冥想和表達。心野了,人生的開篇就有意思了。
金倜:在畢飛宇工作室小說沙龍的討論中,您說讀書是寫作的媽媽,說明了讀書的重要性。我覺得讀書是門技術活,并不是所有人都會讀書,讀了《小說課》,我就認為自己不會讀書。您對《故鄉》《項鏈》這些選入中學課本的名篇解讀,好多人都有醍醐灌頂的感覺。事實上《小說課》也的確贏得了巨大的成功,由此我想請您談談讀書與寫作的關系,給家鄉的文學愛好者提些建議。
畢飛宇:你開玩笑,你怎么可能不會讀書?我實在不能算一個會讀書的人,但是我熱愛,我讀書并沒有多么強烈的求知欲望,我享受的感覺更強烈一些。這個好不好呢?我覺得要看,如果我是學者,我這個讀書的方式很可能要出大問題的。我是一個寫作的人,如何貼著作者去讀,如何透過文字去捕捉作者,這是我的樂趣所在。我是不是真的逮到作者了呢?我也不知道。我感受到了閱讀的自由與開放,感受到了閱讀的樸素和神秘,這就可以讓我的這一生擁有了一個隱秘的維度,這是很令人愉快的。
我認為《小說課》的價值在于,它填補了我們的一個空白,那就是理論與實踐之間的縫隙。做理論的人往往自己不實踐,做實踐的往往不重視理論。因為命運的安排,我在一把年紀的時候走到了這個縫隙的中間,就在這個縫隙里頭吐了一點絲——《小說課》就是一個寫作多年的人具備了一點理論素養,在實踐和理論之間結了一個蜘蛛網,這是一個比較符合實際的說法。
再回到讀書這個話題上。生活積累對一個作家來說是最為寶貴的財富,這是一個文學的基本常識,這句話一定不會錯。但是,如果你熱愛文學,生活的積累上如果有欠缺,那你就需要花更多的力氣去閱讀。我就是那種生活閱歷不夠通過閱讀而支撐起職業生涯的人,我可以,別人也可以。我個人認為,多讀書,對延長寫作生命是有好處的,你可以寫得更長久。
金倜:網上搜索一下可以查詢到很多“畢飛宇名言語錄”,是的,您的機智和幽默已成共識,您的語言是您的作品的獨特標識,討論您的小說語言,是一個很大很專業的知識話題。我想請您降維一下,給家鄉的小說寫作者,就小說語言說說自己的心得,諸如方言的使用、表達的區域性。
畢飛宇:我們的寫作是在現代漢語的框架下完成的,我們使用的其實是普通話,從這個意義上說,方言寫作往往靠不住。當然,有的時候,為了強化地域特征,我們會使用一些方言元素,注意,是元素。我在寫“王家莊”系列的時候曾經這樣做過。不少興化的老鄉就此有了一個印象,會寫方言就可以寫小說了,這是巨大的誤解。我在使用方言的時候有一個原則,不用注。換句話說,我要考量的,我使用的方言和普通話大致上可以置換。可以這樣說,伴隨著電視時代的來臨,所謂的區域特征它的價值會打很大的折扣,而在手機時代,可能還要進一步打折。老實說,現在的孩子即使處在偏遠的地區,哪怕他的普通話沒那么標準,但是,他的思維已經是普通話的思維了。我不看好方言寫作,但愿我是錯的。
金倜:“普通話思維”應該又是畢氏語錄。您的小說語言在當代文壇獨樹一幟,您能對自己用漢語搭建的世界,說幾個很具體的主張嗎?
畢飛宇:不管能不能搭建自己的世界,我就是誠實,說真話。雖然我做的是虛構的工作,但我要求自己誠實。誠實既是道德問題,也是美學問題。一個人在什么時候最有魅力?說自己話的時候最有魅力。當你為了趨同,放棄自己的語言,用別人的語言,它一定是不美的,人生一定是丑陋的。人生可以很美好,這個美好就是我建立了一套語言,這套語言滋養了我,我和我的語言之間共生共長。
金倜:還有一個與語言相關聯的話題。您的作品《寫字》是一篇精致的短制,我們都很喜歡。我能不能把您所記錄的少年時光,解讀為您的少年文學夢?
畢飛宇:當然。我的少年時代是在蘇北農村度過的,我父母是鄉村教師,那時候我最愛干的事情就是拿著鐵釘在操場和土墻上胡亂地書寫。我書寫的愿望是那樣地蓬勃,許多字都不會寫,村子里卻到處都是我的字,當然還有句子,具體的內容記不得了,只記得我受到了父親的訓斥,他擔心我寫出什么不好的東西。我的父親是因為語言倒霉的,所以,他對我的語言表達始終保持著高度的警覺。可我的書寫像野草一樣,他哪里攔得住?到了高中我就開始投稿,當然,那時我就發現要寫作很難,寫作其實就是抗爭。1983年,我的寫作終于有了陽光——我開始寫詩,成了揚州師范學院的校園詩人,帶著一幫師兄和師姐,我們辦詩社,還出詩刊,刊物的名字叫《流螢》,這份刊物到現在都在。真正意義上的寫作,也就是想做小說家的寫作,始于1987年的秋天,那時候我大學畢業了,知道自己成不了詩人,想踏踏實實地做一個小說家。
寫作對我的幫助是無與倫比的。首先是改變了對語言的認知。我所接受的教育是這樣的——語言是工具。然而寫作讓我知道了語言不是工具,是本質。所謂對自己的精神負責,就是對自己的語言負責,反過來也一樣。一個小說家擁有語言,就是擁有生命。從這個意義上說,與其說我在使用語言寫作,不如說寫作是在捍衛我所使用的語言。
金倜:語言不是工具,它是本質。語言與寫作的關系原來就這么單純。
畢飛宇:嗯,語言對人的控制力很強,在三句話之內就能體現出來,表面上是我們在使用語言,實際上是語言在使用我們,甚至是語言在控制我們。而且,時代的變化首先落實在語言上,從根本上說,人類的活動其實就是語言的活動,“三句話不離本行”,這個本行就是一個人的文化特征。
金倜:談一個落俗套的話題,在您從年輕走向成熟的過程中,對您影響比較大的人或者書是什么?
畢飛宇:對我影響大的不是書,而是父親。從我會說話開始,還沒識字,沒開始讀書,基本的價值觀就有了。我父親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被送到興化的鄉下去勞動,之后我在那兒出生。我父親對我的教育非常少,因為他太孤獨了,在他眼里,我又是一個比較早慧的孩子,所以他三十多歲的時候,我們兩人經常傍晚從村子里面走到村子外面,走在田埂上聊天。我七八歲就成了父親談話的對象,而不是教育的對象。他對我價值觀的確立很早就開始了,就是要說實話。
金倜:能夠如此平等甚至是尊重自己的孩子的父親,在我們的生活中極少,更何況在那樣的年代。我可不可以將這種親情關系理解為精神上的師徒和精神之傳承?
畢飛宇:是的。人民文學出版社成立七十周年的時候,我給他們錄了個視頻,其中也談到我的父親。我說我的母親是一個很普通的母親,我的父親也是一個很普通的父親,跟你們的父母都一樣,但是在我的心目當中,我的父親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偉大的人。我為什么說這個話?因為1987年,我二十三歲,大學畢業,有兩個可能,一個是到外面去,另一個是回到興化工作。我知道父親是在興化的縣城被很多人整,然后被送到鄉下去的,那時候整他的人都在興化縣城的汪洋大海里。有一天我跟我父親聊天,我說當年整你的那些人究竟是誰,名字都可以報出來。他說你要知道那些干嗎?這件事就過去了。等我年過五十再回憶起來的時候,感慨很多。他是一個了不起的男人。如果我的父親把那些名字一個個告訴我,說實話,以我當時的性格,回到興化以后,也許會一個個修理他們。換句話說,我的人生將會在仇恨和復仇當中尋求快感。但因為我的父親沒有跟我講,我也不知道是誰整了他,就這么過去了,所以我沒有仇恨,也沒有復仇,我在做我喜歡的事情。
金倜:作為成功的小說家,您能和家鄉的文學愛好者們分享一下自己的工作方法或者思維工具嗎?
畢飛宇:這個話題我只能籠統地說。在我二十多歲的時候,更依賴于激情,坐在寫字臺面前,把更多的時間放在那兒醞釀醞釀情緒。當情緒到了一定地步,你的文字會變得激越。我覺得非常激越的文字有它特殊的美,它汪洋,它澎湃,它具有無窮的渲染能力,我早期的作品就是這樣。大概三十歲出頭的時候,我的閱讀發生變化,突然開始喜歡英國小說,然后我自己的小說也要求準確,這個路子一直延續到現在。當我把一個東西確定下來,在某一個部分我可能要醞釀一下,但從整體上來講,我要求我的作品準確。準確是一個結果,如何準確?就是誠實。
金倜:我在網上搜索到一張表,關于您的獲獎作品一覽表,看了很振奮,我知道的獎您都拿了。其實我個人認為,您的《青衣》也是完美而通靈的好小說(《青衣》獲《小說月報》第九屆百花獎中篇小說獎),還有《平原》。有人拿《活著》類比賽珍珠的《大地》,我以為《平原》跟《大地》是一樣光芒萬丈的作品,那么相通。這樣一來,評獎就是件總有遺珠之憾的事情。
最后我想請您談談《歡迎來到人間》,這同樣是一部迥異于您之前所有作品的存在,并由此指點一下家鄉的文學愛好者們,寫作者應該如何審視生活,如何融入生活,如何突破自己?
畢飛宇:我寫《歡迎來到人間》其實不是突如其來的事,它一直在那里,只不過我沒有來得及完成它,你總要一部一部地寫。在我寫完《平原》之后不久,“歡迎”就已經是我計劃之內的事了。我不可能永遠抓住“歷史”不放,我也不可能永遠抓住“鄉村”不放。進入當下的都市,我一直在做這樣的準備。我十一歲就離開鄉村了,就我的積累而言,寫鄉村其實更難,我有什么理由忽視都市呢?當然,如何寫出一個外科醫生,對我來說并不容易。除了學習,我也沒有什么特異功能。附帶說一句,我在醫院學習的時候,遇到的第一個腎移植的患者就來自興化,她是一位女士,夜里做的移植,第二天一大早,我陪主刀醫生去查房,她已經醒過來了,床下的尿袋是血紅色的。以我當時的醫學知識,我知道,這是一個好兆頭,被移植的腎臟已經開始代謝了,也就是說,它活了。查房醫生問:“感覺怎么樣?”那位幸運的女士說:“好得兇呢!”她一開口我就知道她是興化人了,我當時的感覺有點說不上來,可以說很激動,可我激動什么呢?對吧,我也不能瞎激動。你看,生活就是這樣,你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就會充滿了對它的愛,無緣無故的,也可以說,有根有據的。在我看來,一個作家是不需要刻意去融入生活的,因為生活每一天都渴望融入你,只要你有足夠的溫度和足夠的愛。我至今記得這個感人至深的畫面,那是2006年5月的一個早上,八點多鐘。當然,我沒有刻意去留意她的姓名,我在這里祝這位女士好運,我希望她永遠幸福。
金倜:畢飛宇工作室走過了十年的路,“小說沙龍”和“廣場書屋”已經成為興化文化建設閃亮的窗口。由您領銜,受您影響,小城興化還先后舉行了王家新、歐陽江河、西川等當代著名詩人的專題詩歌朗誦會,請來了當代頗具影響力的美國作家和法國劇作家為興化駐城作家。在這樣的氛圍里,受文學之神的感召,本土文學愛好者更是熱情高漲,“興化文學現象”已經成為當代中國文學界的專有名詞,最后請您對興化文學說一句話。
畢飛宇:我就希望興化的作家們能更充分地享受寫作,享受漢語,享受屬于自己的故鄉。
作者簡介
畢飛宇,1964年生,江蘇興化人。1987年畢業于揚州師范學院中文系(今揚州大學文學院)。現為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江蘇省作家協會主席、南京大學特聘教授、江蘇文學院院長。著有《畢飛宇文集》(四卷本)、《畢飛宇作品集》(七卷本)、《畢飛宇文集》(九卷本),長篇小說《上海往事》《平原》《推拿》《玉米》,演講錄《小說課》,等等。《哺乳期的女人》獲第一屆魯迅文學獎,《玉米》獲第三屆魯迅文學獎、第三屆英仕曼亞洲文學獎,《推拿》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平原》獲法國《世界報》文學獎。2017年,畢飛宇獲法蘭西文學藝術騎士勛章。
金倜,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興化市作家協會主席,作品入選《江蘇百年新詩選》《揚子江十年新詩選》等多種選本,出版詩集《傾訴》《慢慢彎曲》《跫音》。
責任編輯 孫海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