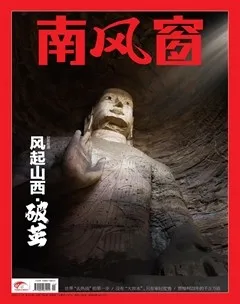《風流一代》,賈樟柯22年的千言萬語

賈樟柯工作室的門口擺著一張他年輕時的照片。他站在一個衛生間里,穿一件黑色大衣,雙手插兜,頭微微抬起,漫不經心地看向鏡頭,年輕,好看,獨立,有態度。
邁入工作室,我見到的中年賈樟柯。他穿黑色西裝,牛仔褲,比想象中瘦;戴一副墨鏡,眼神隱藏在墨色的鏡片后面,令人難以看清。
門內門外,差不多就是《風流一代》的時間跨度。
這是在《江湖兒女》6年之后,賈樟柯最新的一部劇情長片。5月,《風流一代》入圍戛納電影節主競賽單元,11月22日,這部電影將在全國公映。
賈樟柯一直在對時代進行忠實的記錄,并且持之以恒地關注著個體與時代之間的張力。經過“故鄉三部曲”(《小武》《站臺》《任逍遙》)之后,他將目光轉向經濟飛速發展時期的游民現象和底層群體(《世界》《三峽好人》《天注定》)。
從2015年開始,他對時代的描摹進入更寬廣的階段,《山河故人》《江湖兒女》《風流一代》都在更漫長的編年體中展開敘事。
然而對賈樟柯來說,《風流一代》更為特殊,因為它更私人,“貫穿影片的情感曲線是我的切身感受——這就是我所經歷的——但我相信這也是中國人相通的情感”。
故事仍然在我們熟悉的女主角——趙濤飾演的巧巧身上展開。2002年的大同,巧巧的男友斌哥決定出門闖蕩,隨后,巧巧踏上尋找他的旅程,斌哥則在經濟浪潮中沉浮。2022年,他們回到大同,在故鄉重逢。
在敘事之外,這部電影要比賈樟柯過去的劇情片更為松散,它使用了大量過往素材,完成片段的蒙太奇組接,全景式地展現時代變遷中人們的娛樂和交往,同時聚焦于個體的迷茫與失落。
記者進入工作室后,他提出請求:我要抽一支小煙,你不介意吧?
抽雪茄,是賈樟柯一個廣為人知的愛好。他用一把小小的火槍燃起雪茄,在墨鏡與煙霧的雙重隔閡下,這位以電影觀察中國社會近30年的導演,似乎更顯得復雜。
但可能背后那個的真相很簡單。
賈樟柯說:“追根到底,這部電影講述一個女性和一個男性,在20多年的時間里,怎樣在巨大的時代浪潮面前生活。”
持數字攝影機的人
有一個著名的“電影眼睛”理論,來自蘇聯導演吉加·維爾托夫。他將攝影機從乏味的攝影棚里解放至城市的大街上,去“偶遇”凡常的生活,用新的視覺語言“闡釋一個你所不認識的世界”。1993年,汾陽小子賈樟柯考上了北京電影學院的電影理論專業。這使得他有機會比較系統地了解電影史,“這樣你今后的許多努力就不會白白地浪費”。1997年,他拍攝了自己的第一部劇情長片《小武》,一舉成名。
在電影學院學習的理論知識,顯然還在繼續影響著賈樟柯。2001年,已經完成了兩部長片作品的賈樟柯,感到有一點“不過癮”媒介不斷變化,但是在電影院里,我們才能聚眾、共鳴、在一起。他想用一種更為即興的辦法,向制作可控的、工業化的標準電影發起反叛,再度復活早期電影里那種“像荒草一樣”的生命力。
賈樟柯有一種很深的感覺:“一個時代要告別了。”他想,到了為那個必然逝去的時代做一次總結的時候。這次,他給這部影片起了新的名字:《風流一代》。
賈樟柯帶上攝影機,記錄當時一切新鮮的經歷和感受。他和自己的電影伙伴、經常合作的演員,一起去到他們喜歡的城市,去“遭遇”變化,在有趣的空間里,即興地做出反應、編寫情節。他給這個項目起了最初的名字:《持數字攝影機的人》。
在他的預想中,這個項目可能會拍兩三年,但拍著拍著,他發現自己停不下來了,“沒有停止的理由”。
在拍攝其他影片的同時,他斷斷續續地繼續著這項保存時代影像的工作。影像質料也在不斷變化,35mm膠片、16mm膠片、佳能相機,“手邊有什么都拿來去拍”。最初的項目名字不再成立,但是素材跟時間一樣,積累了下來。
2020年疫情暴發的時候,賈樟柯還在安撫同事的情緒,“咱們就繼續寫劇本,兩三個月之后,一切就都正常了”。他經歷過非典,“春天暴發,到夏天就毫無征兆地結束了”。但過了半年多,賈樟柯覺得有點不對。
封閉的生活當時正在緩慢塑形,整個世界暫停至近乎靜態。不過,科技發展絲毫沒有停下腳步。“生物工程、人工智能、無人駕駛,以前人們談論起這些東西,就像說起一部科幻電影,但是現在你看到,它們真的要來了。”
賈樟柯有一種很深的感覺:“一個時代要告別了。”他想,到了為那個必然逝去的時代做一次總結的時候。這次,他給這部影片起了新的名字:《風流一代》。
這是賈樟柯迄今為止最激進也最隨性的一次影像嘗試。他自由地在過去積累的龐大素材庫里選擇片段,用標志性的時代金曲,將一段又一段記憶黏合在一起。“我覺得這個電影很像當代藝術里的混合材料,通過片段之間的不同質感、曲線、力度,以其混雜性來強調美感。”
蒙太奇,一種將不同鏡頭組接在一起的理論,是電影的基石,也是賈樟柯觀察和重述過去20余年時代變遷的方法,與此同時,它對觀眾而言構成一種游歷和體驗,隨攝影機平滑地越過時間的表面,我們會抵達時代的核心:人在變遷的浪潮里,保持活下去的努力。這部電影的英文片名最終被確定為《Caught by the Tides》。
2006年,電影的女主角巧巧,在奉節的一個茶館里看到一部與機器人有關的科幻電影,她露出微笑。2022年,她在自己工作的超市與一個機器人有一段對話。賈樟柯這樣解釋這個情節:“我們的一只腳還留在過去,另一只腳已經邁進新的時代。這個時刻可能很短暫,但是它很迷人。”
巧巧的情感之旅旅行,漫游,即興。這是賈樟柯談到《風流一代》時反復提到的關鍵詞。
今年5月的戛納電影節上,《風流一代》是唯一一部入圍主競賽單元的華語片。在戛納,賈樟柯曾說,這部電影是趙濤(巧巧)帶領觀眾進行的一次情感之旅,電影分成三個章節:2001年的大同,2006年的奉節,2022年的珠海/大同。李竺斌飾演的斌哥要出去闖一闖,他離開了山西,踏進那個狂飆突進的時代。隨后,巧巧踏上尋找他的路程,2022年,他們在故鄉重逢,已經是20余年時光盡逝。
盡管《風流一代》是一部“告別”的作品,但是賈樟柯相信,這個故事不能在過去素材中止的地方結束,“如果要漫游的話,我們的人生也是一次游歷”。
在處理2001年和2002年的影像素材時,賈樟柯常常被“電影的神性”打動。逝去的時代將一些碎片殘存于我們的腦海,而電影將這些碎片背后的記憶幾乎完整地帶回到他的工作臺,在剪輯過程中,“我總為記憶復活而震撼”。
《風流一代》的開場是一段中年女性唱歌的紀錄片,“我都忘了有那首歌了”,但是人們唱了它,賈樟柯拍了下來,那首歌就還存在。
那場戲里,最令賈樟柯感到震撼的,是墻上的招貼廣告,“旭日升冰茶”,代言它的那兩個明星,叫楚奇楚童。
他停下來問我:“你知道他們嗎?”
我一臉茫然。他并不失落,而是似乎再度陷入了回憶:“在我們年輕的時候,他們這個組合就像今天的TFBOYS。”
跟旭日升冰茶一樣消失在人們生活當中的,還有夏利汽車。如果不是因為這些素材,賈樟柯也已經忘了,20多年前的北京滿街都跑著夏利。“我一看到那車就特別有感覺,因為我大學畢業那一天,我們聚會有同學喝多了,我們把他扶上一輛夏利出租車去了北醫三院。”
他對486電腦的情結,則來源于他的第一臺私人電腦。“那時候還是學生,買不起品牌機,就托一個清華的同學去中關村給我買一個鍵盤,買一個主機,買一個顯示器,組裝在一起,能用,能上網,覺得特別開心。”
在剪輯過往素材的過程中,賈樟柯一直想要追問,我們的時代在變化中,是否遺失了一些值得留住的東西?
對物件的印象,往往跟具體的人和故事聯系在一起,影像的碎片里是整個時代的生活風貌。賈樟柯知道大家常常評價他的電影里充滿了意象和符號,他反駁說:“其實那并不是刻意的符號,都是順手拍下來的,你之所以覺得那是符號,是因為它太強烈了。”
強烈如一顆記憶核彈。它們曾真實存在于那個時代,當它在你面前復現,會引爆一種情感沖擊。
在記憶被引爆的同時,回顧這些素材,也讓賈樟柯產生了一種反思,或者說困惑:為什么,我們沒有過去的熱情了?
“那時候人為什么那么興奮?”賈樟柯像是在對自己提問。他對準雪茄點了一下火,在椅子上換了一個姿勢。
“他們比現在的人們自由,行動力更強,甘于冒險,要去一個陌生地方,甩手就去了,他要做什么,你也不知道,反正他就生存下來了。”
過去的東西不一定全是好的,但是一定有一些珍貴的東西,“它是我們能找回來的,或者能幫助我們理解今天出現了什么問題”。
他特別喜歡電影開頭的那段紀錄影像里,那些中年女性豐富的肢體語言,聽歌的時候你靠著我我倚著你,唱歌的時候你推我我搡你,“人和人之間有一種容納度”。“現在的大廠里,還會有這種場面嗎?”賈樟柯想知道。
人與人的界限感,在過去的時代是被渴望之物,因為界限意味著文明和現代,現在我們無疑獲得了它,但同時也丟失了親密。在剪輯過往素材的過程中,賈樟柯一直想要追問,我們的時代在變化中,是否遺失了一些值得留住的東西?
他選擇不說,希望觀眾沉浸地感受。
于是《風流一代》之后,很多人都問過賈樟柯這個問題:為什么這部電影會如此沉默?
在戛納,賈樟柯解釋,這是因為在這段時間里,他有太多的話想說卻又無從說起。
片中,趙濤飾演的巧巧沒有一句臺詞,更多的時候,她只使用表情進行表意。但有趣的是,很多人看完電影都沒有發現這一點,我告訴賈樟柯影片到2/3我才發現巧巧沒有說過一句話,他有點興奮地告訴我,制片人看完電影都沒發現巧巧沒有臺詞,“他說這太棒了”。
賈樟柯并非一開始就想做一個“默片”,當他發現巧巧的不言更有力量時,他剪去了前2/3的素材里女主角所有的臺詞。在電影中,他甚至復興了字幕卡的傳統,用黑底白字來標示那些重要的臺詞和語言。既然這對他來說更像一次當代藝術的嘗試,他想要進一步,“解放我們的視聽”。當電影“說”的東西盡可能少的時候,我們的視覺和聽覺會變得更敏感。
無言的沉默與一聲“哈”
2022年,從重慶飛往珠海的飛機上,人們戴著口罩。衰老而不復青春沖勁的男主角斌哥,緩慢地從座位上站起,胸前掛著他的智能手機,就像他的第二張臉,第二個身份。
在三峽參與過經濟發展熱潮的斌哥去珠海尋找過去的哥們,他或許懷著東山再起的心情而來,卻在那里他遭遇了一個難以追趕和理解的“流量時代”。
青年演員周游飾演的經紀人與抖音網紅下六興哥,在這個片段里成為了流量的代言人。他們用手機拍攝歌舞和廣告,下六興哥與其說在表達,更像在被擺布。然而,在前2/3的紀錄影像里,普通人的娛樂生活,無論是唱歌還是蹦迪,都充滿了自由的生命力。
下六興哥是現實生活中真實存在的網紅。賈樟柯一開始是在朋友圈里看到有人轉發他唱歌跳舞,“我看了好傷感,我看他的年齡,感覺他就像《站臺》里的年輕人老了”。資料顯示,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下六興哥曾是當地歌舞團的主唱,90年代中期因生活變故受到精神打擊,他靠唱歌活了下來。
斌哥看到這一切,沉默地回到了大同。“他與時代脫節了,另一方面他還保留著一點保守的驕傲。驕傲這個東西本來就容易保守,但這種驕傲也是我理解和欣賞的。”
賈樟柯相信自己是一個擁抱新事物的人,但是他又保持謹慎。“這種復雜的態度,是因為我覺得時代的潮流是人不可抗拒的。比如大家都說我們已經進入一個碎片化的時代,對于習慣于傳統閱讀的人來說他會不適應,但是如果你了解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的采集方式,你會感到這種碎片化是一種必然。”
在2022年珠海和大同的段落里,賈樟柯編寫了一段新的故事,為故事中的男女主角尋求一個立腳于當下的結局。他使用了VR攝影機,在這段故事開場的時候,以一種新的視覺經驗提示觀眾,在2006年與2022年之間,我們經歷了一個巨大而深刻的時間跳躍。
理解變與不變的同時,保持人性,這是賈樟柯的辦法,“你不可以用情緒抵觸它,沒有意義”。
這位長期在作品中關注人際情感交流的導演,在電影的當代部分,寫出了一段極為傷感的“溝通”。
機器人問:“您今天心情怎么樣?對不起,我看不清您的表情。”
下六興哥是現實生活中真實存在的網紅。賈樟柯一開始是在朋友圈里看到有人轉發他唱歌跳舞,“我看了好傷感,我看他的年齡,感覺他就像《站臺》里的年輕人老了”。
巧巧摘下口罩。
機器人:“您好像有點傷心。特蕾莎修女說,當你愛到痛時,痛就會消失,只剩下愛。”
巧巧低下頭笑了。
機器人:“馬克·吐溫說,人類有一件真正有效的武器,那就是笑。”
巧巧忍住眼淚,又笑了一次。
賈樟柯不認為《風流一代》是悲傷的,他說《山河故人》是自己最悲傷的一部電影,而《風流一代》并不想講傷感,而是要講堅韌。
劇本寫到巧巧與斌哥在大雪紛飛中分別就結束了。但在大同勘景的時候,賈樟柯有次突然聽到遠處傳來“夸夸”的腳步聲。“我一回頭看到一群人在跑步,他們身上還戴著安全燈。”他被這個場景感染了,決定讓巧巧匯入人群,劇情再次延伸。
于是,2022年的大同,沉默的底層女性巧巧有一個習慣,就是在超市下班后每天去夜跑。她要強壯起來,好好活下去。
賈樟柯提起自己見過一位民國女性的書法,只有四個字卻震撼了他:“聽天由命。”這是巧巧這個人物身上真正的底色,在過去的20余年里,她一直如此。她接受社會的變化,接受愛情的離去,接受人與人在時代的擠壓中必然的分離,接受在一個像科幻片一樣嶄新的時代,與機器人交心。
至于她在人群里發出了她的第一句臺詞、也是全片最后一個聲音,一聲“哈!”—那是趙濤的創造。“她不是沒有話說,只是不說。千言萬語,五味雜陳。”
在過去的一次采訪中,賈樟柯曾說:“不知為什么,關于電影的交談往往容易使人陷入傷感。”在采訪結尾,我似乎也感受到了這種情緒。與社會一同變化的,還有電影。賈樟柯已經在用VR拍電影了,他也在故事里提到了這個令懷有“保守的驕傲”的人們感到無所適從的短視頻時代。但他仍然對電影懷有信心,媒介不斷變化,但是在電影院里,我們才能聚眾、共鳴、在一起。
被雪茄的煙霧包圍起來的導演看起來稍顯孤獨。但他渴望交流,也相信我們需要交流,這樣我們才能知道并且記住,屬于我們每個人的這22年,是如何被講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