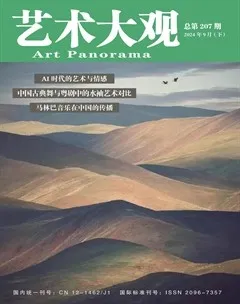古鎮戲事

我的家鄉是一座古鎮,歲月蝕刻的深巷里,吹糖人、捏面人的師傅吆喝著,賣彩球和冰糖葫蘆的小攤販招攬著,還有琳瑯滿目的各種貨鋪小攤,更是引人流連。但最熱鬧的,還要數古鎮的戲事。
記憶中,每逢鄉親們過大年或農閑時,鄉戲就一場接一場地開始上演了。古鎮街中心有一處戲園子,來看戲的人一撥撥往這趕,像趕集趕年會一般熱鬧。小孩子不懂戲,自然不知其中奧妙,卻比大人還興奮,哪兒熱鬧就往哪兒鉆,把戲園子當成了開心的樂園。那時我是個小戲迷,雖猜不透這長袍闊袖演繹的善惡冷暖,但也是逢戲必看。哪天有一場沒看到,就像癟了的氣球一樣打不起精神來。
戲園子里看戲的人爆滿,一排排簡易座位上人影晃動,空氣里涌動著看不見的熱流。老爺爺、老奶奶、小媳婦、壯如牛的莊稼漢,還有跑前竄后的小頑童,讓戲園子成了人聲鼎沸的熱鬧窩,古鎮的鄉土民風和逸聞趣事,在這里釀得更醇厚了。
棒鼓“咚、咚、咚”幾聲脆響,臺上三陣鑼鼓敲過,戲要開演了。垂幕一拉開,臺下唰地一片寂然,戲園子轉眼成了安靜有序的講堂,一雙雙眼睛聚焦于舞臺之上,戲客都屏住了神,亂哄哄左沖右突的頑童也一下子散進了席間。鄉親們賞戲的好時光,說來就來了。
戲臺上,長袖甩成了旋風,高幫靴踏出一陣煙。小丫鬟著一身花衣衫,邁著碎步走來。耿直的黑臉暴怒無常,打著轉兒“喳喳”地叫個不停。倜儻的書生是另一副模樣,扇子一劃,像掠過一縷春風。演員一個個走進角色里,戲臺像是穿越時空向觀眾走來,演員觀眾近在咫尺,卻又隔世般遙遠。前臺西征,烈馬騰空,武將操戈,戰旗舞起西風。又是陣前嘶吼,跟斗翻卷,擂鼓震天,酣戰卷起塵煙。演員一頭鉆進戲里,一場場戰事湮沒了,忽又從歷史的隧道中跑出來。觀眾十米觀景,一眼卻看到千里之外,看過北宋,看過南陳,看穿了世間美丑和丹心豪情。
古鎮戲臺上,我一場接一場地看戲,《楊家將》《花木蘭》《精忠報國》《將相和》,還有《西廂記》《霸王別姬》《桃花扇》和《大鬧天宮》。這些雖是上演在小鎮舞臺上的鄉戲,卻自有天然野趣之美,如一粒粒自然天成的小小珍珠,深埋在我孩提時代的記憶中。古鎮的鄉戲,有的豪情滿懷、震撼人心,有的則千回百轉、曲折離奇,有的凄婉悲切,有的惹笑逗趣。《楊家將》中,楊門三代英勇殺敵、保家衛國,一門忠烈經久傳誦。《花木蘭》中,巾幗英雄忠孝節義、代父從軍,巾幗事跡可贊可歌。《精忠報國》中,岳飛忠心耿耿、氣貫長虹,令人無不動容涕下。《將相和》中,藺相如不與大將廉頗爭功,雖受辱而不怒,傳為千古佳話。《秦香蓮》中,陳世美為一己榮華,拋妻棄子,遭人唾棄。這些名戲上演時,演員個個使出了本事,有的唱腔圓潤甜美,有的則悲悲切切、聲淚俱下,生生把臺下唱出一片唏噓,還有的聲音輕柔尖細,高亢處又如百靈高飛。熱鬧的鄉戲,時而把鄉親們唱得豪氣滿懷,時而又掩面抹淚。它唱鬧了歲月,唱濃了鄉韻,唱淳了古鎮。
戲散,窄斜的小道上,三五成群的鄉親仍沒從戲中走出來,一位老奶奶扯著嗓門道,這秦檜咋就這樣禍害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