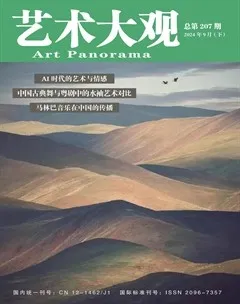從楚劇《萬里茶道》看戲曲音樂創(chuàng)新

摘 要:楚劇音樂在不斷發(fā)展的過程中,注重傳承和創(chuàng)新的結(jié)合。近年來,楚劇在挖掘和傳承傳統(tǒng)的基礎(chǔ)上,積極探索與現(xiàn)代藝術(shù)的融合,嘗試融入流行音樂元素,涌現(xiàn)出了許多優(yōu)美動聽、感人至深的優(yōu)秀作品,深受觀眾喜愛,推動了楚劇音樂的發(fā)展。《萬里茶道》作為近年來原創(chuàng)的重點劇目之一,積極推進楚劇音樂的發(fā)展創(chuàng)新,得到了專家和觀眾的廣泛好評。楚劇音樂的創(chuàng)新不僅要強化劇種意識,注重發(fā)展與時俱進,還要吸收并借鑒其他藝術(shù)的優(yōu)長之處。
關(guān)鍵詞:戲曲;音樂;楚劇;傳承;創(chuàng)新
中圖分類號:J61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7357(2024)27-00-03
一、創(chuàng)新需要深植戲曲之根
中國傳統(tǒng)戲曲,是一種歷史悠久而又風(fēng)貌獨特的戲劇藝術(shù)形式,是以文學(xué)劇本為主體,以表演為中心,融歌、舞、劇為一體,包括唱、念、做、打的綜合性藝術(shù),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一枝獨特的奇花,其淵源可溯至先秦的樂舞和俳優(yōu),與古希臘的悲喜劇、印度的梵劇并列,稱為世界三大古老的戲劇文化。
中國戲曲從它的萌芽狀態(tài)開始,便一直有音樂伴隨。戲曲音樂是戲曲藝術(shù)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地位極為重要,與劇本、表演、舞臺美術(shù)等藝術(shù)手段相結(jié)合,從而集中地表現(xiàn)戲劇內(nèi)容,是區(qū)別不同劇種的主要標志。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國戲曲似乎可被稱為音樂戲劇。但是它有唱卻不同于歌劇,有舞也不同于舞劇,有對白又不等同于話劇。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結(jié)合各地方言演唱,形成各劇種的不同風(fēng)格韻味。盡管不同的劇種,有時會上演著同一劇本,劇情、場次、角色、唱詞完全一樣,但人們總不會把京劇聽成豫劇,也不會分不清哪里在唱越劇,哪里在唱評劇。方言和音樂,雖都是區(qū)別劇種的標志,但起著主導(dǎo)作用和關(guān)鍵作用的,仍然要數(shù)音樂。因為在同一地區(qū)內(nèi),不同劇種之間,所使用的語言是一致的,而音樂卻各具特色,可能是腔系有別,劇種相異,甚至伴奏樂器、音階、音調(diào)、旋法、唱法、音樂結(jié)構(gòu)形式等方面均有明顯差別。例如,北京一帶流行的劇種有京劇、評劇、曲劇及河北梆子等,曲種有單弦、京韻大鼓、西河大鼓、梅花大鼓、京東大鼓和北京琴書等,真可說是諸腔雜陳,百花競放。
戲曲音樂包括聲樂部分的唱腔和念白,器樂部分的伴奏和開場、過場音樂。戲曲器樂是戲曲伴奏、開場、過場音樂等器樂的總稱。經(jīng)過幾百年的實踐和創(chuàng)造,形成了中國戲曲器樂的獨特形式和表現(xiàn)手法。它是為劇本主題的體現(xiàn),戲劇矛盾的開展,人物性格的塑造,思想感情的抒發(fā)和舞臺氣氛的渲染等服務(wù)的,與唱、做、念、打有密切聯(lián)系。
戲曲樂隊分為文場和武場兩部分。文場指管弦樂器部分,武場指打擊樂器部分,統(tǒng)稱為文武場。文場除為唱腔伴奏外,并演奏器樂曲牌、過門等過場音樂。常用的樂器有京胡、板胡、二胡、墜胡、琵琶、月琴、三弦、揚琴、笛、笙、海笛、嗩吶等。在不同的腔調(diào)和劇種的唱腔中,由于文場所使用的主奏樂器以及其他樂器的不同組合而形成各腔調(diào)和劇種唱腔的音樂特色。如皮黃系統(tǒng)的劇種用京胡,梆子系統(tǒng)的劇種多用板胡,昆腔用笛子,越劇、錫劇用二胡和琵琶等為主奏樂器。武場的鑼鼓點,除配合身段表演外,還具有表現(xiàn)人物的思想情緒,烘托舞臺氣氛,有機地協(xié)調(diào)統(tǒng)一“唱、念、做、打”等表演手段的作用。武場以鼓板為領(lǐng)奏樂器,并以不同類型的鼓、板、大鑼、小鑼、鐃鈸構(gòu)成主體,有時加用其他打擊樂器,如堂鼓、星子、云鑼等。由于所用打擊樂器不同,也構(gòu)成各劇種的不同音樂特色[1]。
戲曲音樂創(chuàng)新就是要不忘初心,明確發(fā)展之源,深植戲曲之根,為取得創(chuàng)新實效筑牢堅實基礎(chǔ)。
二、創(chuàng)新需要傳承劇種之基
楚劇是湖南、湖北地區(qū)具有廣泛影響的地方劇種,是國家級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之一。舊稱哦呵腔、黃孝花鼓戲、西路花鼓戲,是湖南流行的哦呵腔與湖北省武漢市黃陂區(qū)、孝感市一帶的山歌、道情、竹馬、高蹺及民間說唱等的融合,在1880—1890年間流入黃陂、孝感一帶,形成西路花鼓。1902年左右進入漢口,1923年加入胡琴伴奏,逐漸取代接腔(幫腔)。1926年定名楚劇,距今已有一百五十余年的歷史。
楚劇音樂融合了多種藝術(shù)形式,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其唱腔豐富多樣,包括高腔、悲腔四平、仙腔、迓腔、打鑼腔等,每種唱腔都有其獨特的風(fēng)格和表現(xiàn)力。同時,楚劇還十分注重音樂伴奏,伴奏樂器包括京胡、二胡、三弦、月琴、琵琶等,這些樂器在演奏中相互配合,為唱腔提供豐富的和聲和節(jié)奏支持。
方言和音樂,雖都是區(qū)別劇種的標志,但起著主導(dǎo)作用和關(guān)鍵作用的,仍然要數(shù)音樂。楚劇是湖北人民的鄉(xiāng)音,它通俗易懂,深受湖北群眾喜愛。楚劇姓“楚”,楚劇音樂要保持自身獨特風(fēng)味,是必須始終秉持的創(chuàng)作理念。一個劇種區(qū)別于其他藝術(shù)品類的重要標識就是自身的“獨特性”。“獨特性”是歷史積淀的結(jié)果,既受一方水土的孕育,又是表演者與觀眾在長期互動中做出的文化選擇,它代表了一個群體的審美心理與聽賞習(xí)慣,承載的是“地方性知識與經(jīng)驗”。因此,貫穿“劇種”意識、堅守劇種獨特性,是對地方文化的守護與維護,是保護戲曲文化多樣性的重要方式,也是警惕戲曲音樂流于“泛劇種化”的一種途徑。
隨著時代的發(fā)展,楚劇也要革新、要發(fā)展,這是毫無疑義的。但這是個復(fù)雜、細致的工作,不是用一兩個戲去轟動社會,也不能只是迎合一時風(fēng)尚,為了創(chuàng)新而創(chuàng)新,刻意標新立異,將劇種優(yōu)勢也“改”掉,會失去自身風(fēng)格特點,失去原有廣大觀眾。誠如根雕藝術(shù),樹根如果被斧劈刀砍,或放在車床上加工,那就不會有樹根的影子了,那還是根雕藝術(shù)嗎?楚劇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就是要增強劇種意識,通過真正的革新創(chuàng)作,讓它永葆生機活力,永遠能夠“活”在舞臺上,永遠深受廣大觀眾喜愛[2]。
《萬里茶道》不僅從劇情內(nèi)容上充分彰顯湖北地方特色,還充分發(fā)揮楚劇聲腔特色,保留楚劇傳統(tǒng)唱腔的風(fēng)格,濃郁的楚風(fēng)、楚韻、楚味,讓楚劇傳統(tǒng)觀眾感受到很親、很近,很享受,充分體現(xiàn)了地方劇種的重要意義。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堅持地方特色、夯實劇種之基的創(chuàng)新,才是楚劇音樂得以傳承之基,也是走向全國,甚至邁出國門的根本要義。
三、創(chuàng)新需要把握時代之要
隨著時代的發(fā)展,觀眾的審美需求在不斷變化。戲曲音樂的風(fēng)格和時代精神如何統(tǒng)一,如何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審美需要,是戲曲音樂研究中的一個十分重要的課題。中國戲曲的生命力,就在于它能夠與時俱進,堅持走革新之路,吸收新的元素,注入新的血液,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和觀眾欣賞水平的提高而變革、豐富自己。如果不顧時代的要求,脫離藝術(shù)所反映的客觀對象的制約,而去追求風(fēng)格,其結(jié)果必然和當代人們在生活中形成的“占主導(dǎo)地位的審美需要和審美理想”不相適應(yīng)。戲曲音樂的風(fēng)格,應(yīng)根據(jù)不同時代的社會背景、文化背景、審美理想等因素,而創(chuàng)新調(diào)整曲調(diào)旋法特點、句式結(jié)構(gòu)特點、發(fā)聲潤腔特點,以及樂隊編制和伴奏方法特點等。這些體現(xiàn)在同一時期的不同作曲者、演唱者的創(chuàng)作個性中,其中的共性,就是這一時期基本一致的風(fēng)格特點。它一旦得到觀眾的認可,就形成一種時尚。人們在創(chuàng)造活動中“一方面要標新立異,另一方面又要求統(tǒng)一于社會流行標準”。因此,它將在同代人或后代人中產(chǎn)生巨大的影響,成為新的藝術(shù)經(jīng)驗,成為新的傳統(tǒng)。當歷史進入一個新的時期,這些經(jīng)驗和傳統(tǒng)就成為這一時期繼承和發(fā)展的基礎(chǔ)。人們在此基礎(chǔ)上,又根據(jù)當代人的審美需要去發(fā)展、去創(chuàng)造,從而形成新的時代風(fēng)格……如此循環(huán)往復(fù),以致無窮[3]。
楚劇音樂的創(chuàng)新,積極適應(yīng)現(xiàn)代觀眾的審美需求,吸引更多的觀眾關(guān)注和喜愛楚劇。《萬里茶道》劇本為音樂提供了豐富的展現(xiàn)空間,如每場都有男女主人公的不同情感唱段,唱多說少。另外,每場開幕都有不同內(nèi)容的合唱,加上導(dǎo)演借用了歌劇方式,安排了大量的對白音樂、間奏和舞蹈音樂。
(一)戲曲語言音樂化
所謂語言音樂化,即按照字的聲調(diào)高低,隨著情感的變化,用流暢的音符連接,而形成一種優(yōu)美的旋律,給人以美感享受。楚劇唱腔,特別是女腔,語言性強,旋律性差,俗稱“報字腔”。《萬里茶道》中的各腔,均采用語言音樂化的方法,使唱腔旋律流暢自如,便于歌唱,聽來悅耳,克服“報字腔”的缺點。
(二)腔調(diào)旋律發(fā)展化
楚劇腔調(diào)幾乎無腔(這里的腔指甩腔或長腔),可是仙腔卻有著兩個固定不變的長腔,而且這兩句腔分別在兩個不同調(diào)式和調(diào)性上。《萬里茶道》第四場主人公玲瓏唱的仙腔,就是利用這兩個不同調(diào)式,在上下音區(qū)內(nèi)發(fā)展了兩個新的旋律層。當人物悲怨時唱“天孕地養(yǎng)如萬春”,唱腔在高音區(qū)環(huán)繞,發(fā)展微調(diào)式旋律,形成高音區(qū)旋律層;當人物沉思著“進城與不進城”的利害沖突時,唱腔轉(zhuǎn)入低音區(qū),商調(diào)式旋律在低音區(qū)迂回,形成低音區(qū)旋律層。兩個旋律層保持著仙腔調(diào)式和調(diào)性特征。由于音域的擴充,使唱腔旋律變化幅度大,形態(tài)色彩豐富。然而這些新的旋律均是以傳統(tǒng)仙腔音調(diào)為元素,借鑒西洋作曲技法而形成的,因此,怎么唱令人感覺還是仙腔。
第三場和第六場的女迓腔,在語言音樂化的基礎(chǔ)上,更重要的是深挖人物內(nèi)心世界,用各種不同的作曲技巧,來塑造人物形象和表現(xiàn)復(fù)雜的感情。創(chuàng)作實踐證明,人物感情表達得準確、深透,腔調(diào)旋律自然豐富多彩。
(三)楚劇板式創(chuàng)新化
第四場男女主人公激烈爭辯“進城與不進城”的道理時,在導(dǎo)演的啟發(fā)下,創(chuàng)造了一個“京板楚腔”的慢流水板與快流水板。所謂“京板楚腔”,即京劇的流水板型,用楚劇腔調(diào)演唱,效果很好,這個板式的輸入,豐富了楚劇板式變化,擴大了楚劇唱腔的表現(xiàn)范圍。
(四)唱腔色彩豐富化
觀眾經(jīng)常聽到的楚劇是迓腔和悲迓腔,因此他們以為這些腔才是楚劇。但是,在專業(yè)人員眼中這兩支腔用得太多(全劇反復(fù)唱),顯得唱腔色彩十分單調(diào)乏味。
實際上,楚劇聲腔很豐富,它擁有板腔、高腔、小調(diào)三類聲腔,而這三類聲腔又有各自不同的腔調(diào),如板腔包括男、女迓腔、仙腔、思兒、悲腔、西江月、四平、十枝梅、應(yīng)山腔。高腔曲牌有近百支,小調(diào)也有八十支左右。如果所有腔調(diào)都能有效發(fā)揮作用,那么楚劇音樂將會大放異彩。
《萬里茶道》的音樂布局,有意運用了楚劇的三類聲腔,以此來豐富唱腔色彩。如第一場兩位主人公唱腔,采用了富有小調(diào)色彩的應(yīng)山腔,使戲在歡悅的情景中拉開劇情序幕。第三、第四場又采用小調(diào)表現(xiàn)歡樂情緒。第三場表現(xiàn)玲瓏痛失葉天韜后的悲痛情感,在懷念二人年幼時兩小無猜的美好情境時,所唱大段唱腔采用了高腔曲牌梧桐雨。第四場是主人公玲瓏的核心唱段,采用了有著“楚劇反二簧”之稱的仙腔演唱。第五場葉天韜唱段和第六場玲瓏唱段均屬中心唱段,采用楚劇的主腔——迓腔演唱。第六場玲瓏的“三杯茶”唱段,則以女迓腔旋律為素材,借用分節(jié)歌體音樂形式,創(chuàng)作了一段別具風(fēng)格的唱腔,為全劇唱腔增添色彩,使全劇音樂旋律多姿,腔調(diào)豐富。
四、創(chuàng)新需要借鑒他山之玉
“縱向繼承橫向借鑒”是我國早就提出的文藝方針,縱向繼承與橫向借鑒的關(guān)系,應(yīng)該是在繼承的前提下去借鑒。也就是說,在傳統(tǒng)藝術(shù)無法表達下,則必須向其他藝術(shù)品種借鑒。《萬里茶道》每場開幕都有合唱,導(dǎo)演對這些合唱的處理,從意義到色彩均是不相同的。有寫“茶道漫漫”意境的男女聲合唱,有水上航行的船夫號子,有茶隊行走在高山上的山歌勞動號子,有地域風(fēng)情的女聲小合唱等。這些音樂形式戲曲是沒有的,必須借鑒歌劇寫作方法和尋找素材。另外,劇中大量的配樂寫作,為了旋律色彩統(tǒng)一,必須有一個主題,圍繞主題音樂變奏才行,這樣就不會雜亂無章。因此,學(xué)習(xí)西洋作曲方法,首先創(chuàng)立一個主題音樂,另向京劇樣板戲?qū)W習(xí),為劇中主人公創(chuàng)立一個形象音樂。在《萬里茶道》劇中,將主題音樂的旋律片段與人物形象音樂融會在一起,以此為動機,通過對動機的各種變奏,而形成了全劇各種不同情景的配樂。同時,為了與唱腔銜接自然,將人物形象音樂的后部分融進楚劇音調(diào)。這種方法能使全劇音樂色彩達到完美統(tǒng)一。
創(chuàng)新是藝術(shù)發(fā)展的生命力所在。在保持楚劇音樂風(fēng)格中,堅定走符合當代審美的“創(chuàng)新”之路,將不斷豐富楚劇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形式,推動楚劇藝術(shù)的傳承與發(fā)展,促進與其他藝術(shù)形式之間的交流與融合,推動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文化的交流與融合。
參考文獻:
[1]陳永,孟憲輝.中國民間音樂概論[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4.
[2]羅周,周淑蓮,傅江寧,等.楚劇《萬里茶道》[J].中國戲劇,2016(01):2.
[3]孫凡.荊楚音樂論:武漢音樂學(xué)院音樂學(xué)系教師論文選集[C].桂林: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23.
作者簡介:李紅梅(1977-),女,湖北武漢人,本科,從事琵琶演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