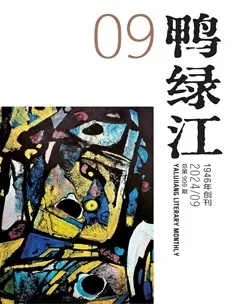遼河的濕地密碼
遼河以水為筆,在入海口處肆意揮毫,似依戀又似撒歡兒,似莊重又似隨意,在這片土地上信筆涂鴉,留下的筆道或粗或細,或深或淺,或長或短,或直或彎,每一彎都緊握大地,根根分明,條條相通,遠遠望去,像大地的葉脈,水韻靈動,蜿蜒綿延,又像水在大地上畫出的一幅幅畫,寫意豪邁,工筆精美。
這幅畫卷的主筆是遼河,東遼河和西遼河匯合后,一路奔行在下遼河平原,肆意揮毫。因為太過肆意,留給鄉村發揮的余地就顯得局促且不規則。于是,隨著遼河的筆道,一個個村莊就那樣隨意地橫亙在濕地和城市之間。在下遼河平原濕地,濕地、鄉村、城市雜亂地堆砌在一起,隨著世事變遷、歲月流轉,居然長在一起,成為默契融合、色彩瑰麗的圖畫。鄉村如城市的后花園,延展在濕地與城市之間,也如濕地卷起的彩色溝邊,把城市與濕地無縫連接。濕地是鄉村的最初表象,也是鄉村文明的最終載體;城市是鄉村發展的高端模式,也是與濕地共生的一種聚落。
水沿著一個個鄉村的草木、河流、田土、人家、房屋、街路流淌,留下一個個名稱、掌故、軼事、傳說。被遼河水網浸潤的鄉村有著不同的地理物產、精神內核、文化特質、質樸鄉情,沿著遼河留下的筆道,可以探尋這些村子的獨特密碼。生活印記在固態的形式下容易被保存,如古城、舊居、古道等,而水包容萬物,也融于萬物,水村生活的印記也易于被水洗滌、淹沒、消融,因而濕地鄉村不同于平原、丘陵、山地上的鄉村:后者或依托地利、得天獨厚,或分布錯落,樣貌俊秀,或傳承久遠、內外兼修,或臥虎藏龍、名人效應凸顯;或獨具特色,引人尋幽。而濕地鄉村雖不具備這樣的天時地利人和,但它們也有著鮮明的特征,或蘊含著神秘傳說,或承載著淳樸真情,或標志著地理物產,或傳遞著智慧胸襟等。它們不聲不響、不瘟不火卻內涵廣闊、氣度卓然。
遼河行至盤山縣古城子鎮,與渾河、太子河相遇,形成大名鼎鼎的三岔河。三河交匯,成為當地交通樞紐和戰略要地。相傳唐代貞觀年間,唐太宗親統六軍從洛陽出發東征高麗。行至三岔河,但見河寬水深,濁浪滔天,洶涌的大河攔住了去路。無橋無渡,數十萬大軍望河興嘆。雄才偉略的帝王,怎么能受困?唐太宗命先鋒大刀王君可在三日之內務必找到渡河之策,否則問斬。軍令如山!王君可接下軍令,緊鎖愁眉,前有大河攔路,后路泥濘不通,實在無計可施。王君可吃不香,睡不著,將至天明,才昏睡在軍中大帳內。剛睡著,就見河神進帳,對他說:“明日寅時,河中有渡橋,大軍可過河。”并叮囑過橋后切不可回頭看。王君可驚醒,急令探馬查看。第一批探馬回報說未見橋,王君可很生氣,立斬之。第二、第三批探馬也未見橋,均立斬之。待到第四批探馬去探時,天色已晚,探馬心想,實報無橋是死,謊報有橋也是死,不如謊報。于是謊報有橋出現于河面。王君可急忙報與唐太宗。李世民聞訊大喜,命大軍緊急渡河。當唐兵行至渡口時,果然看見一座黑黝黝的橋。唐太宗急命連夜渡河,并命令只許前進不許回頭看。大軍抵達彼岸后,斷后的王君可內心疑惑,黑黝黝的,到底是什么橋?他回頭一看,原來這橋竟是由螃蟹堆聚糾纏而成!等他看清的一剎那,一聲巨響,蟹橋塌陷,王君可連人帶馬掉入河中,被螃蟹啃食干凈。相傳,河蟹背上的硬殼,原本光滑無痕,被唐軍的馬蹄一踩,便留下了馬蹄的印跡。如果把河蟹的胃翻過來仔細看,里面還有王君可橫刀立馬的小小頭像。小時候頑皮,還多次翻找過王君可的形象。話說大刀王君可掉入三岔河,那把大刀橫劈而下,成為分水劍,把河水清濁分開。到如今,三岔河水仍一半清一半渾,傳說這是王君可的大刀落在這里的緣故。
美麗的民間傳說當然無從考證,只有三岔河幽幽流淌。三岔河是幸運的,有古城子來承載它的歡樂與哀愁。關于三岔河的千年風濤,終會湮滅在歷史的風塵中。在這里,水仿佛是另一種時間,把水下的一切變成歷史。
三岔河在古城子匯聚,充分交流之后,轉身打個旋兒,成就了一旁的小村青蓮泊。青蓮泊原名繞溝,為河水繞村而過的意思。因為出了一名關東才子李龍石,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小村繞溝,變身為充滿傳奇和文化味兒的青蓮泊。也在用河水講述著李龍石的傳奇。清朝末年,天災人禍頻仍,洪水漫天,兵戈不息。天下滔滔之際,關東才子李龍石以才氣動鄉關,二十二歲中舉,之后屢次赴京會試,因得罪權貴,鎩羽而歸。龍石公為人俠義,豪氣干云,常為民請命,發不平之鳴。一次偶然北上昌圖探親,得知懷德縣(今吉林省公主嶺市)出臺新令,將田賦翻了兩番,農民不堪重負,紛紛拋家舍業,遠走他鄉。他基于義憤,代鄉民擬狀向昌圖知府申訴。不料這懷德縣令的官位正是重金從知府手里買來的,他伸張正義不成,反被羅織罪名,報吏部褫去舉人名分,發配西北蕭關。差官李福感于龍石公為人,行至山海關時,毅然焚毀文書,將他釋放。龍石公只身亡命京師,藏匿在同年京官徐少云等家中。數年后左宗棠去世,他在友人舉薦下代五府六部十三科道草擬挽聯。其聯搜括世上人間美贊之詞,傾盡五湖四海哀悼之情,一時震動朝野,從而有機會面見刑部大員,陳訴冤獄,得以昭雪。回鄉后,龍石公籌辦“養園”學館,傳道授業,培育英才。當時遼河下游洪水肆虐,為根治水患,他向當局呈請開浚雙臺子河,獲得奉天衙門批準實施,將遼河主道導入雙臺子河。自此,遼河安瀾,無邊無際的遼澤洼地,變為魚米之鄉。崢嶸歲月俱已矣,文采風流今尚存。如今的青蓮泊伴著三岔河的濤聲走過一個個晨起日落,依然炊煙裊裊、楊柳依依。
遼河一路穿村過鎮,沿岸村莊多以水命名,如河沿、水庫、水岸、河南、溝北等。在水庫與河沿之間,小村駕掌寺如遼河一個閑筆,依傍遼河而蘇醒與睡眠。駕掌寺這個名字與水無關,卻是一個關乎河的故事。據傳,明末清初一年秋天,一場暴雨連降七天七夜,河水漫溢,房屋倒塌,一片汪洋。災民流離失所,衣食無著,乃至餓殍遍地。一位須發皆白的船老大偕子駕舟,循聲救人,將災民運至河沿唯一一處高坡地,把這船人安置登陸,又駛向茫茫天外。從清晨劃到深夜,又從深夜劃到清晨,一連三日,當他把最后一個人救上岸時,自己竟累死在船頭。水退之后,幸存者感其恩德,在高坡上為其立廟,因不知其姓名,取名為駕掌寺。因為當地人把駕船的艄公稱為“駕掌”。眾人在廟宇周圍定居,晨昏祭拜,并相約效法老駕掌,終生行善。潮漲潮落,日月更替。數百年之后,當國家民族遭逢大難,從小村駕掌寺走出的仁人義士,傳承老駕掌俠義精神,投身抗日,高舉義旗,把愛國的旗幟寫在大地上。
一路上沿著水的指引,駕掌寺全貌逐漸顯現出來。在蒼茫的天地間,白雪覆蓋的房舍、田宅,小村如淡墨勾勒的一葉扁舟,穩穩地停靠在遼河邊。百十戶人家的小村,整齊地排成隊列,和諧的配置,流暢的美感,最有名的畫家也描摹不出。畫面上,北方鄉村特有的尖頂瓦房坐北朝南,勾勒出地域特色。村前小橋橫臥,小河蜿蜒;村內院落圍墻,有序排列;村后沃野千里,直通天際,雪野與藍天交會在視野窮盡處,把這幅水墨畫引入無窮的意境。從外在看,小村的詩情畫意與別處的詩情畫意如出一轍,然而,若想融入這幅畫卷,還需要詳讀村落密碼,審慎做出抉擇。駕掌寺村的密碼索引是兩個關鍵詞:“老駕掌”與“俠義精神”。出來的時候,雪依然不緊不慢地下著,微微地隨風打著旋,漫無邊際地飛舞,好像一點兒也不急,有充足的時間來演繹這場舞蹈。經過雪的過濾,空氣格外清新。相比于春天的鮮活、夏天的潑辣、秋天的斑斕,遼河口的冬無疑是內斂、恬靜的。沒有了花的喧嚷、蟲的聒噪、雷的轟鳴,這里的冬單調,甚至是枯燥的,就如水墨畫中大片的留白,這留白雖不動聲色,又有獨特的韻味在其中,這韻味就是水墨的靈魂。駕掌寺這幅生動雋永的水墨畫,是以義字為靈魂,經過長期歲月的浸潤,終于長成遼河口人血脈深處的精神圖騰。
越臨近入海口,遼河越撒歡兒,水把岸浸潤得透透的,稻在河與海的滋養下,成片成片地生長。僅僅百余年,黃色的稻浪已經和綠色蘆葦蕩、紅色翅堿蓬一樣躋身遼河口濕地三原色。而榮興村據說是1928年張學良開辦的營田公司舊址。營田公司以抽水機引遼河水灌溉,開創了東北地區水稻生產機械化的先河。稻伴隨著水與泥,一點一點融進生活。不論是堿灘開荒,還是發展特色農業,人與稻,稻與人,都在相互改變,最后,稻走進人的日常生活,人把稻做成輕博物館,obDOXIseqKXueyebTxjoGQ==就叫“稻作人家”。榮興村里不用的老房子也沒閑著,做成“稻作人家”民宿,據說運營得還不錯。如今,越來越多的人回到這里,尋找、回憶、收集、集聚、固化,乃至升華。當年點亮稻作文明的人一茬茬老去,“稻作人家”依然立在那里。當人們體驗和重溫過后,回到各自的生活,稻作仍作為一種文化,深深刻入靈魂。
行文至此,我還想用一處關隘鎖住這一方水土,這處關隘就是赫赫有名的黑風關。當初的烽火狼煙已然不見,如今這里白墻黛瓦,屋舍儼然,稻田圍繞,水流潺潺,整個村子像一個沒有圍墻的公園。 信步小巷,房前屋后干凈整潔,院墻整齊劃一,行道樹挺拔蔥郁,花草連片覆蓋,路燈排排成行,整個村子綠樹環繞,花紅草綠,天藍水清,似一幅風光旖旎的畫卷。
這幅風光旖旎的畫卷在早先卻不是這樣,它是史上赫赫有名的黑風關,據傳是評書《隋唐演義》中“薛禮征東”的重要關隘。那里曾留下烽火鏖戰的英雄俠義,也留下毒煙、瘴氣、陷阱和“十二把飛刀”的傳奇。據傳,黑風關始建于隋末唐初,主城、東西南北延長各為一百二十丈,分設東西兩座拱形城門,城墻高三丈六尺,底部寬八丈,頂部寬三丈,兩側垛口林立。主城建筑面積為一萬四千四百平方尺,與東西兩座城門相連,又分別設有二丈八尺高的甕城,以備戰時應急之用。城內分設四條登城馬道,東西兩座城門頂部又分別設有城門樓、旗桿,內城可容納三千兵馬,東門外設有校軍場,城西有下水道,由城內流向南面的大海溝而流淌入海。
自唐朝以來,黑風關城憑著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及豐富的海洋資源,成為交通重要門戶,也成了兵家必爭之地!到了明代末年,這里更成為抵御清軍鐵騎的重要關口。一茬又一茬的刀兵鏖戰過后,黑風關沉寂下來,猶如一座死城。這時,有一戶關里的李姓人家,篳路藍縷,風餐露宿,來到黑風關城下。看到狼煙過后的一片死寂,大著膽子想進城定居,可抬頭看見城墻上的大炮,擔心軍隊回來惹出是非,就沒敢進城,定居在了城外。黑風關城北有一個打造刀槍兵器的鐵廠,城南有一座道觀,名叫圣清宮。這李姓人家為了與關里家人通信聯系,便以鐵廠為標志,給這里起了村名叫大鐵廠堡。后來,村名逐漸演變為大堡子村。
三百多年,滄海桑田,世事變遷,第一個來到這里的李姓人家一直沒有離開,他們耕讀傳家,用實際行動詮釋自己的家園夢。大堡子的文化帶著漁耕文化的內斂和自給自足的味道,也帶著移民文化的開放與包容的氣息。漫長的三百多年,村民把愿望、訴求寄托在道觀圣清宮里的諸神身上。圣清宮始建于清雍正年間,香火繁盛時為東北最大的道觀。后來圣清宮因年久失修,湮滅在歲月的風塵中。如今重修的道觀靜靜佇立在村中,綻放著歷史文化的光輝。其實,不論是黑風關、大鐵廠,還是圣清宮,都是大堡子歷史變遷的文化符號。這些文化符號穿越歷史,到如今還熠熠生輝。
走進大堡子,仍能感受到歷史文化的獨特內質。一進村,以廉政名言警句和《傳統二十四孝》《弟子規》及古詩詞為主要內容的文化墻,讓村子的文化味道一下子濃厚起來。別的村子該有的文化活動,這個村子一項不落,甚至夕陽下躍動的身影和晨起瑯瑯的讀書聲都和別的村子如出一轍。要不是每年都有人從全國各地特意尋訪,誰也不知道高出地面近一尺的土堆就是大名鼎鼎的黑風關。看著平平常常的黑風關舊址幾個大字,想著腳下這片土地發生的激斗鏖戰,再一次對這片人文厚土肅然起敬。從前世到今生,大堡子從烽火狼煙走到生態宜居,從篳路藍縷走到綠意盎然,遼河口人的家國夢,從來沒有如此舒展、溫潤。
遼河走筆,水村如畫,每幅畫都是新的。水村的年歲不在外貌,不像古城、古村、古道那樣長在臉上,也不像古樹、古橋、古畫那樣比歲月悠長,水村的年齡是長在心里,長在骨髓里。遼河一遍遍沖刷洗滌,沖刷大地,沖刷歲月,也沖刷遼河口人的心田;遼河流過城市,流過村莊,流過紅灘綠葦,最終流向遼河口人的心海。
作者簡介>>>>
曲子清,遼寧盤錦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遼寧省作家協會全委會委員,盤錦市文聯副主席。在省級以上報刊物發表文學作品百余萬字。代表作為“濕地三部曲”(《濕地錦年》《濕地繁花》《冰陷湖》)。
[責任編輯 胡海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