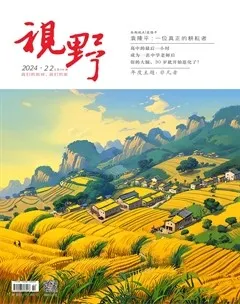外語特長生被保送之后

每年,全國有一千多名高中生獲得外語保送生的名額,提前收到國內各所頂尖高校語言類專業的錄取通知書。
為此,他們需要經過淘汰率極高的層層選拔。
和高中按成績分配的環境不同,在大學他們走入更為開放、自由的環境,如何走出應試的慣性,在迷茫中確立自我,成了很多人成長的陣痛。
迷茫地著陸大學校園
陳逸飛沒有想過,厭學這件事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高中階段,陳逸飛經過層層汰選,成為外語保送生,獲得了一所全國頂尖大學的保送資格。報選專業時,陳逸飛在一眾保送可選的外語專業中,選擇了蒙古語。這所學校的蒙古語專業四年招生一次,陳逸飛認定,現實生活中,這門語言應用場景較少,會讓報選它的人偏少,學校的招生名額又多,選擇蒙古語專業,可以有更高的幾率被清北錄取。
陳逸飛來自縣城,考上名校,不僅是他自己,也是整個家族對他的期待。
自小,靠著在學習、考試方面的靈氣,他從縣城的學校一步步考到省城的重點高中。在家鄉,他一直被大人們當做“別人家的孩子”夸贊。同樣,他憑借著在應試教育中善于學習、考試的優勢,通過外語保送生的選拔考試,在高考前獲得了國內頂尖高校的錄取名額。
每年1月,16所外國語高中都會走出一批學生,他們早早通過“外語保送”這條賽道,得到了高校的錄取通知。這個政策容納的高中畢業生很少,但從升學角度看性價比很高,入選后唯一的風險是,只能選擇外語專業,且讀書的四年不能轉出。
他們中的很多人,安然地過渡到大學的學習生活,但也有一小部分學生高中階段專注奔跑拼搏,進入大學后經歷了不適和迷茫。
曾經最適應繁復競爭規則的陳逸飛,在大學的曠野上,一下子開始感覺到焦慮。
經過一段時間大學學習之后,陳逸飛發現,自己很難在學習過程中產生對蒙古語言文化的興趣,借此形成學習的自驅力。
有幾次早晨上課前,幾個同學用新學的句子互相打招呼,他在旁邊看著,對練習這門新語言興趣寥寥。蒙古語的課堂上,同學們嘗試用蒙古語和老師交流的時候,陳逸飛大部分時間都坐在教室的角落保持沉默。他對這門語言印象最深的,是蒙古語發音部位在喉部,練習的時候,他時常會因為特殊的發音部位而感到喉嚨疼。
在這個過程中,陳逸飛逐漸找到了一部分確定的自我:對蒙古語真的不感興趣。由于入學時的承諾,他也難以通過轉專業,繼續探索自己真正想走的路。
起先,陳逸飛試著沿用高中刷題的策略,來應對大學的課程和考試,很快無功而返。用陳逸飛的話說,高中考的知識點固定、有限,而大學考試范圍靈活,以“解題”為導向的學習,在大學里再也難幫他在各科考試中獲得優秀成績。
學習方法失靈,逐漸讓他氣餒,進而不想面對課業。
陳逸飛在宿舍的時間開始變得很長。他花大量時間躺著刷搞笑視頻。有一陣子,陳逸飛感覺自己依賴上了手機,隨身沒帶手機,他就會感到焦慮不安。
他不愿意和周圍人談起發生在自己身上的這些不適,因為擔心別人很難理解,容易被當作無病呻吟對待。
“你都保送北大了,還在抱怨,是不是太不知足?”“別抱怨環境,是不是自己不夠努力?”這些話,第一時間浮現在他腦海里,連他自己都嫌棄自己的“嬌氣”。有一次,他在宿舍里聊起這些情緒,得到的回應是:“誰沒有點兒痛苦?”“忍忍就過去了。”
迷茫至極,他想過退學,但又承受不起推倒重來的風險。大一上學期,他去見了學校的心理咨詢師。詢問起退學的方案時,咨詢師提議他觀察一年再決定。在困頓中,他說服自己:時間很快,先拿到畢業證書再說。
類似事情,也在李思穎的大學生活里上演。
李思穎在2020年作為外語保送生,進入北京一所高校讀日語。
她發現,班上一些通過高考入學的同學,憑借興趣選擇專業,很快融入了大學課程的學習中。
有一位同學選擇日語專業,是為了配合自己的職業規劃。她喜歡游戲,曾經跟同學們說,未來要去游戲公司做出海工作。從她口中,李思穎聽說了很多沒見過的游戲。本質上,他們是從兩條路徑成長出來的孩子。從小,家里人就經常警告李思穎,不能打游戲,在他們眼中,游戲如洪水猛獸。讀小學六年級時,李思穎到朋友家偷偷注冊了《洛克王國》的賬號,和朋友玩了一個小時,就再也沒機會登錄那個賬號。
李思穎同專業的室友,是一名動漫愛好者,在宿舍看動畫時,時不時會跟讀幾句。她入學前就熟練掌握了日語五十音圖與基本的日常表達。李思穎也試著學著室友那樣看日劇,希望能啟發自己對日語的興趣。可看了三部,她發現自己只對劇情感興趣,過程中會不自覺地去看中文字幕,只好作罷。
日語音標50個,老師默認學生們已經提前自學過,開學一周時間就過渡到了課文,李思穎開始跟不上教學節奏。
按照要求,每周全班同學都要向助教背誦一篇日語課文,作為階段性檢測。同學們領到的第一篇課文是一則日記,總共不到三百字。當時李思穎五十音才剛記住一周,日語發音還很不熟練,日語假名像是繩子一樣繞在她的舌頭上,那結怎么也打不開。經過三小時一字一句的重復,李思穎已經口干舌燥,但文章背起來還是磕磕絆絆,達不到老師的要求。
嚴厲選拔的優勝者
無論是李思穎還是陳逸飛,作為曾經經過層層選拔得到外語保送生名額的孩子,某種程度上說,都是最適應應試教育汰選規則的“強者”。
陳逸飛收到北京這所頂尖大學錄取通知書時,河南在白雪皚皚的深冬中準備迎接春節。他的同年級同學還在準備高考。提前半年得到了通往中國頂尖學府的入場券,他心馳神往。
畢業后,陳逸飛很快會成為高中學弟、學妹們學習的榜樣。在他所就讀的外國語學校,每年高考出分后,學校會在校門上布置一排大紅色的表彰牌。在外語保送選拔和高考中成績優異的學生,名字連同考取的名校,被張貼在表彰墻上,成為勉勵下一屆高三學子的榜樣。
每年,學校被清北錄取的考生,走外語保送生渠道的約占三分之一,這也是學校引以為豪的范例。
外語保送上名校的底層邏輯,在于“學生少、名額多”。以今年為例,16所外國語高中共有不到1700名保送生,而高校招生有2000人;40余所招收保送生的大學中,985高校過半。對比之下,2023年全國高考985院校錄取概率還不到2%。
但要成為那1700個人,卻需要經過更加嚴格的汰選。
陳逸飛回憶,升入高三不到一個月,鄭外舉行了保送生資格入圍考試。在鄭外,每個班平均60個學生,想要入圍,成績基本需要排在班級前十。高二之后,陳逸飛的成績始終排在班級前五名,這次入圍考試他正常發揮,成功入圍。
拿到這張入場券后,陳逸飛和家人站在了是否選擇外語保送的岔路口。陳逸飛的家長有些猶豫。保送只能讀語言專業,而孩子選理科專業貌似更合適——文理分科時,陳逸飛的理科成績比文科高出100分。班主任是一個中年男人,面孔總是透著嚴肅。他主張陳逸飛走保送,在他看來這是學生沖刺清北的絕佳機會,如果逸飛能夠成功保送清北,班集體也能提前收獲一枚升學成果。最終,上名校的念頭還是占領了上風。
山東學生林佳,自進入濟南外國語學校就讀的一刻,就在心里放入了一張分數計算表。
在林佳所在的學校,選拔外語保送生,除了考試分數外,學生們通過課堂發言表現、學生會任職、宿舍內勤檢查表現、作文大賽獲獎等都能獲得一定加分。此外,在學校的短跑、長跑和跳遠、跳高考試也能積累分數。她回憶,那時候每一分一毫都要爭取獲得,因為在最后的評選上,0.1分之差,都可能讓她與推薦名額失之交臂。
為了在選拔中勝出,林佳要求自己每天繞操場跑三圈,訓練體能,而且每天只吃兩頓飯。在林佳看來,身體上的痛苦讓人保持警惕,而幸福和滿足感,則會讓人懈怠。
在李思穎的記憶里,獲得保送名額的過程,不比參加高考輕松。獲得學校的外語保送推薦名額后,學生們要輾轉各地,參加各大高校的保送資格考試。
決定保送后,雖然筆試只有語數英三科,但學校不會再安排全天的課程。她必須要在短時間內提升英語能力到專八水平,同時要擴大知識面緊跟時事,還有練習語言表達等等。
早上六點進班,李思穎會先背兩個小時英語單詞。之后抓緊做數學競賽題和江蘇高考英語卷,接著等著參加學校安排的模擬面試。進入面試場,李思穎總是感到惶恐。高校大多十分重視文學素養,語文老師問:“你最喜歡莎士比亞的四大悲劇的哪一部?”李思穎說是《哈姆雷特》。老師接著問原因,她只能沉默。她不想告訴老師,之所以選擇這部作品,是因為四個劇目中她只知道這一個名字。
學校為參與外語保送生選拔的學生準備了儀容儀表課。老師強調,女生要穿西裝裙,化一點淡妝;男生要穿西服褲,頭發要打理好。參加面試時,開門進入教室前要先環顧四周,對高校老師鞠躬后再入座。
劉若彤高中就讀于一所外國語學校。大學常常要求申請的保送生遞交個人陳述,這讓她最為困惑。指導老師透露,高校希望看到學生對外語專業的熱愛、外交方面的志向或者對外國文學的興趣。劉若彤不知道從何下筆。在學校讀書時她投入最多精力的地方是做題和考試,這三個方面的內容在她的生活里沒有來由,每每寫資料都無從下筆,但為了拿到保送錄取又必須完成寫作。
優秀的標準
當局者迷。
陳逸飛曾經質疑過,一直以來被家長和學校相信的“優秀”標準,是唯一的嗎?是不是除了競爭的排名,其實存在別的角度,只不過沒被他發現?
在高中,學校每天傍晚給學生一個小時時間吃晚飯、運動、整理內務。陳逸飛的班主任將進班時間調早了30分鐘,隔壁班還在喧鬧時,班上往往已經是一片安靜。前桌、同桌、后桌,周圍人手中的筆都像加了發條,唰唰寫題。
評價一個孩子是否優秀,維度是多元的,但在高中,沒有什么大人能解決陳逸飛內心的困惑。
高一學年的一個凌晨,陳逸飛在黑暗的宿舍里打燈背英語單詞,書上有一個詞是“enthusiasm”。“enthusiasm”,他重復,“熱情”“熱情”。日復一日的刷題生活,緊張的日程安排,讓他感覺“熱情”這個詞距離自己太過遙遠。他未曾產生過熱情,不知道那是什么,他只知道“熱情”用英語怎么說。
迷茫中,陳逸飛唯一能確定的意義是考上名牌大學。考上清北的目標,在高考大省河南是不可能被質疑的,他非常確定。
在大學,陳逸飛開始試著走出迷茫。他試著盡量不讓自己囿于本專業的學業,積極地從興趣愛好中尋找自我認可的抓手。
他加入體育類社團,和朋友們一起運動。每周的出行讓他覺得自己對生活仍然有著掌控,也體會到了運動本身帶來的快樂。最開始,他對待登山、攀巖和徒步也像對待一種任務,它們的終點同樣設定在一個固定的地方,他不自覺地想要更快地到達。回想起這些,陳逸飛感到,自己從小到大身上背負的東西太多了,而他不愿再那么累地活著,只想單純地過生活。
李思穎放棄了在日語上的努力。她得出自己不適合學習語言的結論,并堅信一定有適合自己的領域,只是沒被發現。一個月前,她通過朋友介紹找到一個占星師,第一個想知道的問題,是自己適合哪個行業。
作為過來人,保送進入南開大學英語系的許寧對保送生著陸大學校園的不適十分理解。她提供了另一種角度的感受。
“從一開始,我就知道我走外語保送這條路,要的是什么。”許寧說,入學前,她就知道自己很可能不適合外語系,也對英語及其文化學習不感興趣。她清楚自己需要的是一張入場券,帶自己進入大學,在象牙塔里去感受世間更多的知識,從中尋找自己的興趣,規劃適合自己的未來路徑。
許寧的想法,也代表了一部分外語保送生的情況。
從許寧的經驗來說,避開了是否喜歡外語專業的困惑,有了更明確的大學學習思路,并不意味著不迷茫。相反,隨著認知邊界的拓展,需要面對的迷茫和思考的問題會更多。
“到了大學,我的迷茫在于,確認自己不喜歡英文,這件事很簡單,但之后選擇什么呢?”為了解這道題,許寧花了四年時間去體驗,目前有了階段性的心得。
大一下學期,許寧選修了二十多門課,內容有經濟、法學、心理學和計算機,從不同專業的課程去感受自己的興趣所在。許寧印象最深的是一堂文學課,她讀到社會對自由意志的剝奪與勞動的異化,看到人們在資本家日復一日的剝削中逐漸喪失主體性,放棄尋找自我價值。她想,人能平靜快樂地活著,本身是不是就很難了呢?
根據大量選修課積累的感受,許寧后來選擇了雙修金融學專業。畢業后,又因為感受到人工智能領域的潮流,投身互聯網行業工作。目前,她計劃用在職場的前三年積累過硬的技能,再做人生的下一步打算。
“人生不僅僅是盡量做對的選擇,而是盡量把選擇變成對的,因為很多事沒有辦法規劃,隨時會有變化。”對她來說,比起做對題的能力,更長遠的,接受一切發生的心態和相應的應對能力,才是保障生存的重要技能。
如果要說給迷茫的保送生后輩提供什么建議,許寧可能會說:做好迎接自由的準備。
“在高中,一切軌道都有大人規劃好的,學生只需要埋頭趕路就好。做好每一道題,就能過上不錯的生活。但到了大學,擁有了自由,就需要做好擁有自由的準備。”許寧說,“我愿意為了什么努力,努力到什么程度?很多時候是我們自己需要思考、確定。并為自己的決定負責的。”
她提示,在大學可以通過修雙學位、修讀多元課程和發展課外興趣來認知自己的喜好和性格,尋找自己樂于置身其中的方向。
她有為自己做的選擇負責的勇氣。“我的選擇都是我自己做的,或者參考別人的建議后得出。我不認為現在的我有資格去責怪當時的我。我會盡量按照當時的邏輯,和現在的信息補充,調整方向,繼續走未來的路。”許寧說。
(克里斯蒂娜摘自微信公眾號“真實故事計劃”)